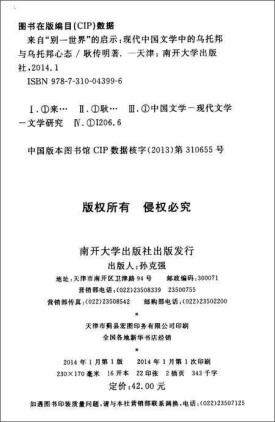命定論
命定論
中國倫理思想中一種人生貴賤禍福觀點。
先秦時期的儒家、道家都主張有"命",並把"命"看成人事的最後決定者。一些儒家的代表人物提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認為人生的一切都受冥冥之中一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決定,主張樂天知命、逆來順受。道家則從"天道自然"出發,否定人對自然的一切作為,其中莊子主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東漢思想家王充認為"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人生的貴賤禍福與神無關,也與個人品行無關,而是取決於命,即由處於母體時稟受自然元氣的厚薄所決定。王充站在唯物主義的無神論立場上反對福善禍淫的神學目的論,具有積極意義。
作為一種倫理觀的命定論,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和道德抉擇能力,也否認人們的道德責任,所以它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歷來就有兩種對人生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命定論(determinism),謂宇宙和人生都預先有一定的安排,不是人的意志力量所能支配的。這種情形,無論你怎樣形容——你說是“神”也好,說是“自然”也好,就說是“機械的自動”也好——人總是被決定了的,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種是“自由意志論”(free will)。如哲學家康德,就承認現象的世界(phenomenal world)里,沒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又捨不得他珍重的道德責任,不讓它無處安放,於是想出了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supernatural world),其中安居了絕對的自由意志。在這超越自然的世界里,人的自由意志,與上帝的合而為一,這就是道德的先天必然性。普通所謂命定論起源甚早。初民時代就有占星學(astrolAogy),主張人生是受神的主宰;神有絕對的權力,要人怎樣就得怎樣。這也可稱為“神定論”,或是“運定論”(fatalism)。我們在兒時常聽到老年人說,天上的星都是代表人的,每人有一顆星,星暗則人倒霉,星墜則人死。大星落於五丈原頭,於是諸葛亮歸天了。人像棋子,神就是下棋的人,只能聽他擺布。這種觀念在中國商周時代,頗為盛行。《列子》是表現這時代思想的一部書,其《力命》篇一段道:“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然則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無可奈何。”此處所謂天就是神,也就是命。在同一篇里,還有一段很有趣的文章,就是“力”和“命”兩位的對話:“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這位命陛下的權威真是大極了,力是一點沒有用處的。這種觀念,支配中國人的思想甚深。其實何只在中國,在希臘神話、印度哲學,以及許多宗教的經典里,哪處不能找到?西洋如此,東方亦然,天下思想皆相通也。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殷周時期已流行。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說明早在殷周時期,天命觀就已經在人們的頭腦里紮根了。
這用《易經》的話來說,叫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對於這裡的命,後人註釋道:“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天壽之屬也。
在古人的思想觀念中,人們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以及死生壽夭、窮通得失,乃至科場中舉、貨殖營利,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非人類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種力量,即命運是也。
命運的觀點,在古代源遠流長。由夏經商曆周,至春秋時,孔子弟子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可見孔門弟子是信奉命運的。孔子進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宋國的桓魑有一次想謀害他,孔子聲稱:“天生德於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總之,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生死存亡、富貴貧賤完全與高懸於天的命運有關,絕非塵世碌碌眾生的力量所能改變。故孔子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日》)。
儒家祖師爺孔子是位極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說,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大儒,對於人類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怎麼就會信起命來呢?原來,他早年風塵僕僕,奔走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很想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是到了後來,當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後,才深深地省悟到,命運之神竟是如此這般的厲害,然而這時他已是個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從不知命到知命這一思想轉化過程的最好說明。與此同時,他不僅“知命”,他和他弟子還不遺餘力大肆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屬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的思想。這裡他的說教是,一個人的生死貧富,都是命里早就註定了的,作為一個君子來說,非得知命不可,否則就夠不上做“君子修的資格。正因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從老天爺的安排,但是小人卻不這樣,他們不肯聽從天命,往往冒險強求,希望有幸,意得個好結果。
當然,看問題也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孔子袋語》記錄孔子的話說:“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我孔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這裡,他認為賢和不肖是根據才華來劃分的,乾和不幹是人們自己可以把握的,至於機遇好和不好,是時間的問題(既在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而是死還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這種天命思想,又在後來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萬章》上篇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沒有人叫他干,而他競幹了,這就是天意,沒有人叫他來,而他競來了,就是命運。同時他還舉例說明,堯、舜的兒子都不肖,是因為舜、禹為相的時間太長.所以堯、舜的兒子不有天下;禹的兒子啟賢能,而禹為相的時間義短,所以啟能得到天下。以上這些,都不是人力所為而自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從理來說,這屬於天意,對人來說,這屬於命運。天和命。實在是一致的。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還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年n會善不吉亞粵健'下尺甘;首而而芒.幣會十h.坯地環老.非幣等待天命,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後者是說,天底下人的吉凶禍福。無一不是命運,只要順理而行,接著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立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下面。因此,儘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這裡,孟子雖然認為天命的力量無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應該按照我的仁義而行,不能無緣無故地白白送死。無疑,這對孔子的天命觀來說,有著補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諸子信命的還很多,而以儒家的勢力為最大。
天命觀經過先秦學者的一陣鼓吹,其時從上到下。從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風氣一時很盛。早在殷商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們,就已習慣於在每做一件事之前,總要先佔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後來,又由於人與天地相應觀念的影響,更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整個天下的命運和每個個人的命運,都和天時星象有關。《周禮·春官》記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這是說馮相氏和保章氏,是專管歲時星象,並從而窺探命運從而推測人間吉凶禍禍福的一種職官。
命數,這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誠等對數有一段很好的論述:“人為自然界天與地作用的產物,人在天地間生存、運動;宇宙萬物都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人、天、地及宇宙萬物的運動無一不受著一種數的制約。古人認為,對這種數,人們可以通過卜筮等術數手段,得到神的指點和啟示,感知和認識它。”數是宇宙本質現象在度上的規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它是點和線,也是波和場。它是數字的學問,也是哲學的學問。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劉禹錫在《天論》中認為數是事物內部的聯繫,凡物必有數,由數可以得理,順乘其勢。他說:“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問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傾。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可見,數是考察事物的著眼點,通過數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發展趨勢。
在孔子的學說中,還保存有“天命”的觀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樂天知命,才被稱為君子。夫子到五十歲明白這個道理,一切通達了。
於是自由意志的學說,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如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就主張我們只有支配行動的意志(the will to act),卻沒有支配意志的意志(the willto will)。又如偏向泛神論的哲學家斯賓諾沙(Spinoza)則主張意志不過是精神的自動(spiritual automotion),也就是順其自然,不知所以的動作(spontaneous motion)。這都是離開自由意志的表現。
但是18世紀末葉和19世紀初葉有兩位思想界的重鎮,重行樹起自由意志的大纛,為人生道德問題求得適當的解答。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叔本華。叔本華以為意志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它是宇宙人生的原動力,它在一切宇宙人生動作之後,推動這一切的動作。它沒有原因,它本身就是原因。人的行為完全受制於這不可測度的意志,所以人生是盲目的,也是不能自主的。他要解脫命定論的悲觀,但是他自己卻踏入另外一條悲觀的路上。康德是接受牛頓力學的宇宙觀的,然而他只是接受和承認他在現象的世界里的權威。(因為當時支配科學的原理,只以牛頓力學為最高;設如康德知道20世紀的近代物理學,他的學說是一定會有改變的。)他另外想出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來,安放道德的範疇,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在這物質科學稱雄的世界里,他三部深刻的“批評”,使人類在無可如何之中,得到一種道德的援助;也使康德成為一百餘年來道德哲學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