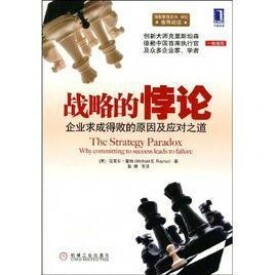戰略悖論
戰略悖論
戰略悖論源於戰略承諾和未來不確定性之間的衝突。如果公司為規避風險而不做出戰略承諾,那麼或許公司能夠生存,但很有可能無法蓬勃發展。如果公司進行戰略承諾,可能收穫豐厚的回報,卻要同時面臨徹底毀滅的高風險。面對兩難境遇,應該如何作出抉擇,是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一個難題。
在《戰略的悖論》一書中,雷納著重分析了索尼的Betamax卡帶式錄像機及其迷你光碟音樂播放器兩則失敗案例,旨在說明未來的不確定性給確定性的戰略所造成的衝擊和威脅。作為日本企業的代表,索尼在制定戰略方面極少出錯。它了解客戶的需求,善於發現新的細分市場,開發尖端產品,執行過程完美無缺,並密切關注競爭對手的舉動。然而,索尼還是嘗到失敗的滋味,當種種努力背後那些看似完全合理的設想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索尼將體會到一個好的戰略同樣需要一個好的運氣。對此,雷納評論道:“沒有好運氣,或者甚至是伴隨著厄運,再好的準備都是錯誤的準備。所以,在解決戰略悖論的問題上,預測甚至並不如適應性來得有力。”
對於如何解決這一悖論,雷納提出“其方法在於對承諾和戰略不確定性的分工管理,一些部門負責履行已做出的承諾,另一些則負責降低風險,捕捉機遇”。也就是說,在進行長遠規劃時,高層管理者應關注於對戰略不確定性的管理;而低層管理者,由於負責短期規劃,則應著眼於履行已做出的承諾。在書中,雷納稱這一新型組織原則為“必然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為組織中每個層級都由它與管理戰略不確定性的關係來決定。
雷納的建議意味著企業領導者要將管理不確定性視為管理的主要職責,並形成這樣的認知,即最合適的戰略制定與決策過程,依賴於環境波動的程度,戰略規劃的程序和結果應該和現實緊密相連,以適應市場上迅速發生的變化。一個好的戰略應該具有戰略柔性,能夠給企業多種選擇,既對這些選擇做出清晰的權衡,同時又配有相應的應急措施。
當然,雷納的方案更多是一種原則和綱領性的。他沒有對戰略不確定予以更為細緻、深入地探討。例如,是否可將不確定性分為幾種,在此基礎上,制訂相應的解決方案;或者將“戰略的悖論”議題擴展至更廣的範圍,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未來不確定對戰略承諾的衝突。即便如此,雷納還是對管理學做出了貢獻,他引導人們思考戰略的意義及其局限性。正如他與克萊頓·M·克里斯坦森教授在多年前合作出版的《困境與出路》所帶給工商界的意義一樣,此次他揭示了戰略管理困境,指明了方向。毫無疑問,他的新作《戰略的悖論》會成為企業發展之路上的一劑良方。
應對戰略不確定性的一種可能就是提高企業的適應能力:多數組織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適應性。然而,適應性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有用。具體而言,只有當組織變化的速度與環境變化的速度相一致時,適應性才能發揮作用。如果環境變化的速度相對於組織的變化速度過快或過慢,適應性就不再有效。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就是,每個組織都會在某一時期遇到一種或兩種環境與組織自身變化速度不一致的情況,而每種情況都能導致組織的毀滅性後果。
我們先來看當發生快速變化時的情形。以自然界6500萬年前白堊紀大滅絕的環境突變為例,由於慧星撞擊改變了全球環境,由此改變了地球上的每一個生態系統。在商業領域,也會有類似的“環境突變”。比如2001年由於“技術泡沫”破滅而引發的電信設備市場崩潰,導致朗訊、北電網路等大量的電信設備公司裁員或破產。而思科和德州儀器等較好地經受住了這次風暴,並不是由於它們更快地適應了變化,改變了戰略,而是由於他們恰好有某項業務滿足了新的市場環境。
正如克里斯坦森在其《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所指出的,當某個行業特有的技術進步能夠滿足另一個行業的客戶時,行業之間就會發生碰撞。如果一個行業的參與者為滿足環境所精通的技術對新興競爭對手形成了結構優勢,破壞就會發生。每一次破壞都會催生出一批新的市場既有企業,反過來後來者又以幾乎同樣的方式被破壞。並不能將破壞者的成功歸因於高超的靈活性適應性,每個行業的領先公司都具有高度的適應性,能夠應對快速激烈的變化。而一旦兩個行業發生碰撞,成敗不是由誰能更好地適應決定的,倖存者只是碰巧滿足了當前需求而已。
與產生破壞性創新的快速變化相比,緩慢變化促使組織適應周圍環境的漸進式變化,並且由於這些漸進的適應方式,公司常常無法察覺到更徹底變革的必要性。汽車行業應對當前石油危機的方式也許就受到這種異常緩慢變化的影響。隨著油價逐漸攀升,汽車製造商通過大幅度提高燃油使用效能、製造混合動力電動機等延長內燃機壽命的方式來加以應對。但是,由於環保原因需要限制碳的排放量,或者整體經濟增長未能抵消油價上漲的負面效應,內燃機總有一天必須被拋棄。如果那天一旦到來,一直在利用自身適應能力的公司將遠遠落後於那些已經開始積極主動探索替代型技術的公司,這些技術旨在替代而不僅僅是延展這種已有百年歷史的技術。
實際上,多數競爭環境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多種變化速率,產生組織無法完成的任務,該任務要求組織在同一時間以不同的速度變化,以同時應對快慢變化。結果,適應性無法解決甚至減輕戰略悖論問題。
悖論的前半部分是承諾:即使承諾被證明是錯誤的,公司也不能對其進行修改。反過來,我們能否對未來做出足夠準確的預測,事先做出準確連貫的承諾,從而避免悖論呢?
有人預測,通過對過去現在進行分析,他們能發現並說明最終決定未來的趨勢,因為總有人做出成功的預測。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原因有三:首先,誰都不能理直氣壯地宣稱對未來有非凡的預測能力,可以不斷做出正確的戰略承諾。既然我們無法知曉什麼人會做出正確預測,或者能正確預測出什麼事情,那麼事後證明預測是準確的也是徒勞的。
其次,從當前的角度來看,預測未來就是描述每一個可能發生的事件及其發生的概率。遺憾的是,我們將無法對未來基於概率的描述與當前真實的概率進行比較。例如,如果我說明天降雨的概率是10%,那麼明天降雨與否都不能說明我預測的準確性,不管是否降雨都符合10%的降雨概率。
難以進行準確預測的第三點原因是隨機性無處不在。這種隨機性首先是由於外在的衝擊,幾乎任何競爭系統都會受到外在衝擊,諸如那些能夠催生出新競爭對手或顛覆長期均衡態勢的新技術或新管理體制。商業系統是由人組成的,而人的行為是無法預測,有時我們因為理性的意願而選擇做出不可預測的行為,有時僅僅是因為我們情不自禁。
在豐田公司的成長歷史中,這種隨機性的作用清晰可見。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作為一場外部衝擊使得北美市場對小型節能汽車的需求猛增。而豐田生產的正是這種汽車,許多原本不會購買豐田汽車的顧客也因此第一次購買了豐田汽車。在某種意義上,石油危機正是豐田所需要的並使其得以進入美國主流汽車市場的幸運突破。
為何豐田比諸如福特、克萊斯勒等其他汽車企業的定位更準確,甚至搶在了通用前面?難道豐田具有極具天賦的預見力和適應性,使它比其他企業先知先覺嗎?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在豐田的故鄉日本,汽油一直以來就比美國的貴,減小汽車體積一直就是企業的首要目標。這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市場“初始條件”可以歸結為地理、政治、文化這些擁有幾百年積澱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豐田似乎並沒有模仿通用的戰略,在預見石油危機后也沒有改變策略,也沒有在遭到禁運時調整戰略。相反,迫於國內市場壓力,豐田自成立之日就一直致力於一個戰略(小型、節能、便宜的轎車),這一戰略使豐田由於難以預見的原因最終適應了北美市場。沒有好運氣,或者甚至是伴隨著厄運,再好的準備都是錯誤的準備。因此,在解決戰略悖論的問題上,預測甚至並不如適應性來得有力。
戰略悖論是在企業不可能知道哪些是正確承諾的情況下嘗試做出正確承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也就是承諾和戰略不確定性相互衝突的結果。解決方法在於對承諾和戰略不確定性的分工管理,一些部門負責履行已做出的承諾,另一些則負責降低風險,捕捉機遇。
這一分工的基礎是傳統的組織層級。運行良好的等級制度在不同層級之間有明確的分工,這一分工是根據檢驗當前決策正確與否所需的時間來劃分的。CEO思考長遠規劃,部門經理(特別是運營部門)考慮中期規劃,而最前線的執行部門則負責提供產品。
戰略不確定性隨著規劃的時間跨度增大而不斷增大。這一新型組織原則被稱為“必然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為組織中每個層級都由它與管理戰略不確定性的關係來決定。
對於不確定性和承諾的分開管理其意義深遠,遠非表面所見。首先,高層管理者不應該關注短期的結果,這條信念被廣泛認同卻又屢遭違背,而“必然存在的不確定性”正是為這條信念奠定了基礎。在戰略層面,很少能做些什麼來改善本季度的現金流,而且任何被迫經常干預當前財務狀況的CEO都不太可能有足夠的精力去關注戰略。
清晰界定戰略不確定性,並要求高層管理者參與其中,這完全不同於許多公司已有的自下而上的風險管理程序。許多既有的風險管理實踐都著眼於重要短期的不確定性,如供應鏈、公司聲譽等,卻忽視了公司對錯誤戰略做出承諾所帶來的風險及其應對措施。
更具爭議的是,運用“必然存在的不確定性”原則意味著CEO的角色定位不應是做出戰略選擇,也即承諾,而應該側重於建立戰略期權,也就是說依據如何解決重點不確定性來培養尋求有效替代戰略的能力。它也意味著,董事會既不應該過多關注公司戰略的制定或審核,也沒必要過分決定對戰略風險和機遇的最恰當控制。只有將企業高層的關注重點從制定、執行戰略轉到管理戰略不確定性,企業才有望降低戰略風險,同時創造戰略機會。
“必然存在的不確定性”將管理戰略風險和機遇的責任交付給總部,而由運營部門創造並獲取價值。應用該原則時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工具即戰略靈活性,戰略靈活性是通過創造戰略期權來管理戰略不確定性的一種公司層面上的框架,這個框架可以用來辨認不確定性並開發各種降低風險或利用機會所需的選擇。
作為最引人注目的中國企業之一,比亞迪正在給自己創造更多的戰略選擇權——一方面,它把自己標誌性的電動汽車和油混動力汽車的特色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仍牢牢抓住傳統汽車市場,它的汽車銷量連續數年保持100%的增長。
另一家值得提及的公司是GE,這家化石燃料時代最重要的企業在2005年開始推出一項名為“綠色創想”的商業戰略,產品包括海水淡化、風力發電等綠色能源技術。它的海水淡化平台每天可處理1.5億人每天所需的各種用途的水,風力渦輪機每年提供的電力相當於1 200萬戶中國家庭的年耗電量。據說這些技術已經實現了3倍於公司增長速度的快速增長。
且不論比亞迪或者GE的戰略新選擇最終是否對應著市場的滾滾財源,但不難想見的是,它們已不再把戰略的全部籌碼壓在某個技術或市場上,而是為自己設置了多種選擇權,以備未來之需。對於比亞迪來說,如果電動汽車未來流行起來,它無疑將永垂不朽,但如果電動車沒能成氣候,它還能依靠傳統汽車吃飽飯。而GE一面在化石燃料的此岸耕耘不輟,另一面已經在為明日的低碳時代搭架起通向彼岸的多座橋樑。它們的做法體現了一種“戰略靈活性”(strategic flexibility)。
在傳統觀念中,戰略常常是一種對某種新技術或新市場的承諾(commitment)。人們通常認為,一個公司要獲得高度的成功就必須專註於一個極端戰略,大膽投資,放手一搏。但實際上未來是很不確定、處於變化中的。極端戰略可能會帶來極端的高收益,但也可能造成極高的風險。用棒球界的術語,要麼是全壘打,要麼被打出局。這就是“戰略悖論”(strategy paradox)。
所有企業都面臨著“戰略悖論”。當年的索尼在開發消費電子產品新模式—Betamax盒式錄像機的時候,正是因為過於注重產品的高品質,而忽略了價格和網路效應,導致了該產品的徹底失敗(相關文章可見本期“求解”)。時至今日,我們有必要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出發,消弭極端戰略的迷思,破除風險和收益的必然關聯性。
戰略靈活性就是這樣一個新的視角。它不要求企業作出承諾,而是建立一種適應性(adapting)。這種適應性需要企業去建立一系列戰略期權(real option)或稱為戰略選擇權,對未來未雨綢繆。公司可以追求激進的增長戰略,但同時利用戰略期權來對沖激進戰略所帶來的風險。這樣,公司就不用在極端戰略和安全戰略兩個極端中作出痛苦的選擇。
戰略靈活性四步驟
那麼,企業應當如何建立戰略靈活性呢?
第一步,情景分析。根據不同的場景來分析不同結果。這是把不確定性融入戰略的第一步。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也不能就此兩手一攤說:“我放棄算了。”這兩種極端都不對。場景分析可以幫助企業確定不確定性的範圍。
第二步,制定戰略。考慮未來如何應變。以燃料電池和藥廠為例,電池公司的不確定性是未來技術的發展趨勢,而藥廠的不確定性則在於未來市場結構的變化和走向。它們都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第三步,積累。在這個步驟中,企業針對未來可能的變化採取行動,建立戰略選擇權。譬如有時候收購其他公司,有時候出售一些對戰略沒有價值的業務,有時候對其他公司少量投資,有時候建立合資企業或者白手起家建立全新企業。
第四步,執行。真正把你所選擇的、認為成功的戰略付諸實行,並需要根據情況變化作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