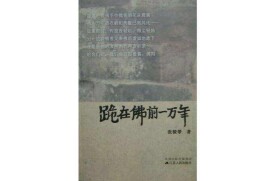跪在佛前一萬年
跪在佛前一萬年
《跪在佛前一萬年》是2009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駿翚。
《永夜漂泊的情聖(代序)》
想不到駿翚居然寫詩,居然寫的是純熟的現代詩,居然寫得如此之好,使我在成都東郊某個安靜的閣樓上,沉醉了三個下午。夕陽的餘輝,暖暖地洞穿窗戶,將我從酣夢中喚醒,我懷疑我的記憶和判斷。駿翚是治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的,寫起現代詩來,有志摩之情,望舒之味,還有適之先生之自由,而清新自然還在好多著名的現代詩人之上。
20世紀80年代初的某個春天,我被安排在省林干院學外事。少來多愁善感,青春無助。一日鬱悶不安,從沙河堡散步遛灣,不知行程。無意間到達獅子山,曲徑通幽,誤入一處桃林,正是夭夭灼灼。突然心有所動,此處必是藏龍卧虎之地,定有高人出沒。沒想到,不出廿年,這樣的人漸次闖入我的生活,年長者諸如萬師光治先生者輩就不提了,年輕者中前有何大草,這次又有了張駿翚。
長久以來,駿翚對我是個秘密。他似乎總是走動在我看不到、走不進的生活空間。冥想中,那裡陽光充足,荷葉田田,蓮花綻笑,有童子焚香沐浴,卻與外界隔著一重厚厚的門。裡面的人,聽不見外邊的敲門聲。無論這敲門進行了多少個春花秋月。不是這次讀到駿翚的詩,他也許永遠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儘管正是這樣的人構成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和世界的本相。
十年前,一個初春的下午。這是一個枯燥的下午。例會開得如火如荼。駿翚坐在教室的某個角落,一臉的絡腮鬍子特別扎眼。好一個鬚眉男子。而這鬚眉與頭髮青蔥得發亮,旺盛的生命力彷彿就是從這裡咯嚓喀嚓不斷外射。他的絡腮鬍子很不藝術,很不顯秀,順其自然中倒有些無賴:長就長吧。駿翚就這點開始吸引我。幾十年,行走在人生途中,遇到過不少長發美髯的男人,感覺不怎麼的不乏其人,駿翚在他們之中一定是個例外。
這個判斷在未來的日子裡不斷得到證實。
關於駿翚這就算認識了。之前的他我一無所知,甚至沒有聽說過一點有關他的故事。
以後,駿翚消失了一段時間。去了山東念博士。走之前,據說他為某寺院奉獻了多少多少公斤清油,還有多少多少什麼,我記不清了。這件事,在別人只是說說,給我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讓我對他肅然起敬。稚嫩的經驗告訴我:一個懂得敬畏的人,一個知道限度的人,往往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人。因為他身上有怕有愛。怕和愛,不是誰都懂得,尤其是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現代智識者,可偏偏駿翚他懂。
從山東回來,看不出這個戴了博士帽的男人有什麼變化。又是這次讀了他的詩,才知道長在黃河以北的白楊樹與永恆的愛情之間關係是如此的密切,以至於多年以後的日日夜夜,駿翚還在他的詩中,在一個又一個的不眠之夜,念想泉城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和飄渺不定的鬼魅精魂。
到歐洲作觀光客,我和駿翚的接觸多了些。無論是在塞納河畔看紅日弄波,還是在威力斯蕩舟、慕尼黑飲酒,抑或是維也納街頭聽樂,駿翚的行為都稍稍有些怪異。一次,我們走進巴黎香榭里榭大街的香水店,一個黑人姑娘迎上來,那細膩光滑的皮膚,纖細動人的身段,顧盼流輝的雙眸,不讓人走神才怪。遲疑之間,驀然看見一隻手扶住姑娘的腰身,有閃光燈一閃。當我回過神來,駿翚已完成和那位黑人姑娘的合影。即便在異國他鄉,真性情就還是真性情啊。面對此情此景,你無法不感嘆一二。機會難得,我也趕緊上去和那姑娘合影一張。我們的妻子就在身邊認真地目睹了這一幕。姑娘轉過身去,帶著職業的微笑招呼另外的客人時,我瞥見駿翚的眼中,有一種深刻的悵然若失。那種眼神中透露出的亘古的苦痛,像一朵黑色的火焰,是很容易灼傷人的。那個下午或者是上午,三年以後回想起來,還隱隱有痛莫名其妙穿越時空而來。
沒想到,寫著寫著,在這裡自爆出正人君子眼裡不太“方正”的“丑”來,駿翚不會怪我?
駿翚在公共場合話不太多,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這樣。一朝開口,聲音又總是不小,總是在你不經意間搶過話頭,說出你意想不到或者感覺有些文不對題的話。他似乎總在走神,似乎總是行走在世界的另一端,按照自己的方式,仗劍行吟走天涯。但他的外表卻不乏開朗,笑容甚至不乏天真。可是,我注意到了,為此我感到幾分不安,也有一些時候,駿翚皺著眉頭說話,眼睛紅紅的,濕濕的,好像剛剛經歷過一件值得憂傷的事情。
的確,從外表你很難說駿翚也是一個可以憂傷的人,他是有些名士氣的。駿翚是要大碗喝酒的,這遠遠超過了大碗吃肉。能喝總是要喝的。有一年院里在麻石橋團拜,還有一次在紫荊路為導師祝壽,一片觥籌交錯之後,我們都喝醉了,踉踉蹌蹌在夜深人靜的路燈下不知轉悠了多久才回到家裡。
在一起喝酒的次數多了,每次的時間長了,給別人名士的感覺就有了。而這種感覺常常是跟懶散結緣的。不知別人怎麼看,反正我認為我懶散駿翚也懶散,就象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一樣。那次駿翚說起,他在川大的博士后工作站要推遲一年出站,我暗自有些得意,這不印證了我的判斷嗎?可是,我終於錯了。
學生中不斷有關於“八道子”博客的傳聞,有說得神秘兮兮的,有說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點開一看,是駿翚的。內容豐富得令人咋舌。欄目10餘個,文章 1000餘篇,點擊幾近20萬。心靈碎片、拈花苦笑、欄桿拍遍、管窺天下、流風遺韻……涉及讀書、寫作、喝茶、旅行、學術、教子,可謂應有盡有,記錄下駿翚幾年來的心路歷程。每當想起經年累月,入夢時分,駿翚還在鍵盤上斟字酌句;每當想起萬籟俱寂睡夢聲中那個孤單的身影,就讓我羞愧,我哪有駿翚的這份執著和堅韌?懶散於我是真話,在他卻成了謊言。
駿翚的博客多有文學原創,其中不少美文和好詩。這本詩集中的絕大多數詩篇便是從博客上擷取的。可以說它們都是愛情詩,都是“我”為“我”和“你”歌唱。
我自視讀了不少一點兒新詩,也敢在課堂上講點兒現當代經典詩歌文本細讀之類混飯。但坦率地說,寫愛情,附庸風雅的多,真情實感的少,寫“通”的就更少了;有文學史意義的多,是經典作品的少;倫理性強的多,文學性強的少。
不要去說駿翚的作品有多好,我想說的是:駿翚是懂真情的,尤其是真懂愛情的。這樣的詩句道破古今愛情玄機:“愛情沒有歸宿:/在可以倚靠的樹下/愛情悄然地死去,如一枚落葉”。愛情是不能被婚姻樊籬,被家庭套牢,被一個人拴死的。愛情是沒有歸宿的,愛情是流動不居,永夜漂泊的。這樣的愛情與生活中你要成家,你要舉案齊眉,你要家庭幸福,你要百年偕老沒什麼關係;與倫理道德、安定團結沒什麼關係。這些東西都是次生的、派生的,而不是本然的、本根的。
愛情的發源地據說在伊甸園。當初亞當是雌雄同體的。當初亞當身上的一根肋骨被上帝變戲法而有了夏娃。這樣,就決定了沒有夏娃少了一根肋骨的亞當是殘缺的,沒有亞當只有一根肋骨的夏娃是不完整的。這樣,也就決定了,被逐出伊甸園的亞當、夏娃為了做為人的完整,會無盡的思念,永恆的尋找,尋找各自的對方,就像風中失去了聯結點的兩片剪刀。除非回到伊甸園,這尋找不會找到,也就永遠不會停止。除非在夢中,人類已經沒有了回到伊甸園的路。這樣,作為尋找的愛情就成為永恆,作為尋找的夢想就成為人類永恆的鄉愁。這樣,偷吃禁果不僅成了人類始祖永遠的恥辱,更成了人類永遠無法走出的悖謬。當然,卻成就了詩人的光榮。
有著敏感詩心的駿翚,還未蒙上厚厚塵垢的駿翚,浸潤過諸子百家、唐詩宋詞的駿翚,熟讀俠士隱士騎士和里爾克、阿古斯蒂尼的駿翚,就無法不懷抱永恆的鄉愁去作無望的尋找。在幽深的松林中,在雨後初霽的窗前,在荷塘的深處蓮花的背後,在遙遠的白楊樹下,在如花似玉的妹妹叢中,在月光如水的簾幔後面,在似黃金噴涌的陽光地帶,在每年第一場雨、第一場雪降臨的時候,在有槐花、梔子花、玫瑰花飄香的日子,在狼狽逃亡的途中,在紅燭點燃的時刻,在柔波蕩漾的湖面,在柔情似水的夢醒時分,在兩棵樹、兩枚青杏之間,在豐茂濕潤的青青草地,在一張發黃的老照片里,在三亞的情人橋,在彭州的修道院,在塔子山公園安靜的角落裡,在七夕,在中秋,在一枝山菊花的開放的時候,在一星螢火、一聲鳥鳴飄過的中間,在狂想、夢想、幻想、臆想的漫漶無邊之際,在人生走過的一行又一行歪歪扭扭的腳印窩裡……我們的可憐的駿翚,都自以為看見了“她”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的愛情,讓心慢慢靠近,讓情慢慢噴發,讓手狠狠抓牢,再抓牢。但哪知道,到頭來,打開手掌一看,抓到的只不過是一抹青煙和刻骨銘心的失望。可是,我們的可憐的駿翚又轉過身去、義無反顧,踏上新的尋找的征程。
找不到了,實在找不到了,駿翚向佛祖祈禱,對上蒼髮誓,向命運求情,直至六月飛雪、天崩地裂。他甚至為了神聖的愛情願意在上帝面前犯罪:“親愛的,等到有一天,/我們手拉著手/挺起兩顆驕傲無悔的頭顱/走到威嚴的上帝面前//如果,他要問:/‘你們可曾犯下什麼罪?’/親愛的,讓我們勇取又驕傲地回答:/‘愛情,呵,是愛情!’”為了愛情,駿翚願意接受末日審判。
可是,愛情依然隱匿。
駿翚的詩是那樣深深地打動我,我看見一個孤獨的、憂傷的孩子,在兩間絕望地尋覓,歌哭,在內心深處,在一個常人無法到達的地方。誰都不能伸出援手,除了文字,除了詩歌。
就這樣,一個也許並不打算做詩人的人,無意中成了詩人,成了優秀的詩人,成了詩界永夜漂泊的情聖。詩哪裡“做”得!詩是血淚凝成,詩是生命無路可走時的突圍,詩是一條不是道路的道路。
突然想到駿翚的飲酒,駿翚的言不由衷,想到香榭里榭大街的黑人姑娘和駿翚那雙偶然紅紅的、濕潤的眼睛……我好像若有所悟。
當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聽說駿翚獨自背上行囊去了貴州。他早已不是十年前的長發美髯,而是頂著一顆光頭,面頰修得精光,不過與十年前一樣,還是那個駿翚。
我的手就要停止敲打,可駿翚還在漂泊,而且是永夜的漂泊,作為一個情歌王子。
2008-7-8於蓉城
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藝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