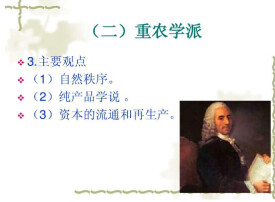重農學派
重農學派
重農學派是18世紀50—70年代法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弗朗斯瓦·魁奈(FransoisQuesnay,1694—1774)是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安·羅伯特·雅克·杜爾閣(Anne-Robert-Jacqnes-Turgot,1727—1781)進一步發展了重農學派的理論,並把重農學派的經濟綱領付諸實施,是其後期的主要代表。1765—1772年,杜邦·德·奈穆爾(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1739—1817)曾主編重農學派的雜誌。他編輯出版魁奈的著作,就以“重農主義”(Physiocratie)作書名。後來,這一經濟學派就稱為“重農學派”。17世紀末至18世紀中葉,法國處於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轉變時期,農業在經濟上佔有很大優勢。但是,法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先後實行犧牲農業發展工商業的重商主義政策,使農業遭到破壞而陷入困境,國家財政枯竭,經濟問題甚為嚴重。於是出現了反對重商主義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和重視農業的重農主義經濟學說,重農學說的理論基礎是“自然秩序”論。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存在的客觀規律是上帝制定的“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政策、法令等是“人為秩序”。只有適應自然秩序,社會才能健康地發展。
重農學派在鼎盛時期以“經濟學家”稱謂。其成員之一杜邦·德·奈穆爾於1767年編輯出版了一本題名為《菲西奧克拉特,或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的魁奈著作選集,首次提出了源於希臘文“自然”和“統治”兩字的合辭作為他們理論體系的名稱。但在當時,這個新名稱沒有得到通用。
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依據他們“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把他們稱為“農業體系”,漢語則意譯為“重農學派”。
魁奈是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和首領。有人曾認為古爾奈也是創始人之一,但古爾奈除了經濟自由放任的主張外,並沒有樹立任何重農學派的主要論點。魁奈無疑地首創了重農主義所有的理論。他的代表作《經濟表》,就是這一理論體系的全面總結。
18世紀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圍逐漸出現了一批門徒和追隨者,形成了一個有較完整理論體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別,而且是一個有明確的綱領和組織的政治和學術團體。他們有定期討論學術問題的集會,有作為學派喉舌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誌》和《公民日誌》。
杜爾哥是繼魁奈之後的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響但不是魁奈的門徒,也幾乎沒有參加所謂“經濟學家”們的派系活動。
他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農主義的重要文獻。他發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黨的論點,使重農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特徵有更加鮮明的表現。在他那裡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
重農主義體繫上是第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卻又是封建制度、土地產權統治的資產階級的翻版。封建主義是以資產階級生產的角度來加以說明,而資本主義則以大農業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來發展。這樣,封建主義就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資產階級社會獲得了封建主義的外觀。這個實質和外觀的矛盾出現於重農主義幾乎所有的理論中。
在當時法國的宮廷、貴族、達官中獲得聲譽,甚至在巴黎所謂社會顯貴名流的社交場合中,以稱道農業改革和穿著帶有農家色彩的裝束為時尚。在法國以外的當時歐洲若干國家的統治者,如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納的利奧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對他們的學說和主張抱有一定的興趣。但也因此他們的學說引起了革命的或進步的啟蒙思想家們的反感。伏爾泰在《有四十個埃居的人》中,對於他們學說的臆想進行了無情的諷刺與嘲弄。
另一方面重農學派也欺騙了他們自己。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達官貴人,他們的利益和法國當時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絕沒有認識到,他們所鼓吹的是一個與現存的社會相對立,並且只有消滅現存社會才能建立起來的新資本主義制度;而總以為他們所企求的只是對舊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鞏固現存的制度。
自然秩序是重農主義體系的哲學基礎,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啟蒙學派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爾在為重農主義體系下定義時,明確地稱之為“自然秩序的科學”。
重農主義者指出,和物質世界一樣,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恆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會的自然秩序不同於物質世界的規律,它沒有絕對的約束力,人們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來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會的人為秩序。後者表現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和法令規章等等。
重農主義者指出如果人們認識自然秩序並按其準則來制定人為秩序,這個社會就處於健康狀態;反之,如果人為秩序違背了自然秩序,社會就處於疾病狀態。他們認為當時的法國社會就由於人為的社會秩序違反了自然的社會秩序而處於疾病狀態,而他們的任務就是為醫治這種疾病提出處方。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學說第一次確認在人類社會存在著客觀規律,從而為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客觀規律的任務。這一認識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創立了把社會經濟看作是一個可以測定的制度的概念。這概念意味著社會經濟受著一定客觀規律的制約;經濟範疇間存在著相互的內在聯繫;事物的發展具有理論上的可預測性。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和政策就是建立在這一概念上的。但由於他們的局限性,重農主義者既把人類社會客觀規律看做永恆的規律,又把社會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實質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主要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是個人的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統一又只能在自由體系之下得到實現。於是重農主義者就從自然秩序引伸出經濟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的準則,可能最早溯源於與柯爾貝爾同時代的法國商人勒讓德而由魁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農學派才真正地成了標識著新時代的戰鬥口號。
純產品學說是重農主義理論的核心。他們的全部體系都圍繞著這一學說而展開;一切政策也以之為基礎。重農主義者認為財富是物質產品,財富的來源不是流通而是生產。所以財富的生產意味著物質的創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經濟部門中,他們認為只有農業是生產的,因為只有農業既生產物質產品又能在投入和產出的使用價值中,表現為物質財富的量的增加。工業不創造物質而只變更或組合已存在的物質財富的形態,商業也不創造任何物質財富,而只變更其市場的時、地,二者都是不生產的。農業中投入和產出的使用價值的差額構成了“純產品”。
重視農業是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布阿吉爾貝爾自稱為農業的辯護人,指出農業是一個國家富強的基礎。重農主義者繼承了這一傳統,並以“純產品”學說論證了農業是一個國家財富的來源和一切社會收入的基礎,為這一傳統觀點提供了理論基礎。
純產品學說是重農學派的剩餘價值學說。重農學派實際上是以農業資本來概括一般資本,以農業資本主義經營來概括資本主義生產。租地農場主,作為產業資本的實際代表指導著全部經濟運動。農業按資本主義大規模經營方式經營,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傭工人。生產不僅創造使用價值,而且也創造價值,而生產的動機則為獲得“純產品”即剩餘價值,而地租則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在“純產品”的基礎上,重農學派提出了廢除其它賦稅只徵收一種單一地租稅的主張。他們認為“純產品”是賦稅唯一可能的來源。“純產品”歸結為地租,於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負稅的收入。在複合稅制下,賦稅的負擔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會通過轉嫁間接地歸於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當地取消一切雜稅,改而徵收單一地租稅。由於簡化租制會減少徵收費用,這種改革實際上減輕了地主的負擔。
在分析社會財富、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的嘗試上,重農學派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既分析了資本在勞動過程中藉以組成的物質要素,研究了資本在流通中所採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會總產品的生產,通過貨幣的中介,在社會三個階級間的流通過程,表現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同時,在再生產過程中,包括了對各社會階級收入來源,資本和所得的交換,再生產消費和最終消費的關係,農業和工業兩大部門之間的流通等等的分析。這些都在魁奈的《經濟表》中得到了全面表達。
大量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通過傳教士進入歐洲。
到了17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和對中國商品的消費成為時尚,形成遍及歐洲的“中國熱”。“中國熱”對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國文化,將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等視為他們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來源。
霍爾巴赫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爾泰則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伏爾泰甚至感慨,在歐洲各國還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時候,中國人已經能夠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國那樣的國度為憾。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和杜爾哥在建立重農學派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影響。

重農學派
魁奈以御醫身份進入凡爾賽宮后,通過龐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於1756年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了顯示重視農業的儀式“籍田大禮”。在宣揚重農學派思想觀念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誌》和《公民日誌》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歐洲的文獻而是中國的典籍。在杜幫編輯的魁奈及其門徒的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或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中(該書第一次提出“重農主義”概念),為了顯示其神聖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
作為重農學派理論基礎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國古代哲學的深刻影響。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該書的第八章標題即為《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法則相比較》。魁奈將中國作為一個實行自然法則的理想國度,通過對中國的制度實踐的考察,闡述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精神。魁奈的自然法則觀念,同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天行健”觀念一樣,都體現了對自然的敬畏。可以確定,中國古代文化對魁奈自然秩序觀念的起了重大作用。
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的理論體系使“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經濟學說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閣的理論骨架,即使不談它比《國富論》在時間上領先,也顯然比《國富論》的理論骨架更勝一籌。”而杜爾哥此書的寫作,與中國和中國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
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高類思和楊德望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策源地;人們都希望這兩位中國青年能夠讓他們的歐洲東道國不斷地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於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擬讓他們回國后在研究本國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予以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系統而真實地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為了使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義,我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於社會的各種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
杜爾哥所提出的問題及作出的分析都與他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或者是希望從中國的實踐中得到解釋,或者是受中國的情況的啟發而予以發揮,或者是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有研究者說,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蒙受中國的影響最深。”
魁奈的去世和杜爾哥免職后對他所推動的改革的反動,標誌著這個學派的迅速崩潰。
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給重農學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和政策主張上,斯密的經濟思想成為以後的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思想。而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制憲會議從杜爾哥改革方案得到啟發的財政政策,只能是這一體系的“迴光返照”而已。
在一定意義上,重農學派是中國古代文化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樑。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遊歷法國期間,與魁奈和杜爾哥有過多次接觸。斯密正是在這些接觸中產生對經濟學的研究興趣並著手制定《國富論》的寫作計劃的。與魁奈和杜爾哥的討論對斯密構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寫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幫助,而重農學派對中國文化的傾慕也對斯密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對中國資料和文獻的大量引用可以作為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