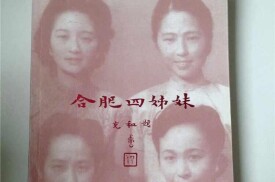合肥四姐妹
金安平創作的小說
《合肥四姐妹》金安平著 凌雲嵐、楊早譯的一本書,作者描繪了一幅和睦美滿的畫面,充分展示了舊式大家庭溫情脈脈的一面,足以讓習慣於批鬥地主劉文彩、貧下中農的血淚控訴的人們驚詫錯愕。

合肥四姐妹
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能在這讓人感動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種無形的殘酷。除了這無形的殘酷,還有無形的悲涼。
解啟揚:老實說,要不是看到“保姆”一章,我不太可能看《合肥四姊妹》這樣的書。
雖然這書有很多賣點:很多人對名門望族、侯門深院、大家閨秀懷著窺探性的興趣,書做得漂亮,很多圖片,張充和秀雅的題籤,作者金安平又是史景遷的妻子,有折射的名人效應。但畢竟已有《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等一堆書出版在前,十姐弟兩度出版家庭刊物《水》,四夫婿(顧傳玠、周有光、沈從文和傅漢思)比四閨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還有名,元和大齡下嫁崑曲戲子轟動一時,沈從文的愛情驚動了胡適,這個“鄉下人”終於“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電報“允”,充和與德裔美籍漢學家的異國戀情……張家的這些逸聞也耳熟能詳,我需要一個特別的翻開這本書的理由。
全書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姊妹都單獨一章,但對我來說,唯有乾乾們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內容。原來,張家背後還有很多家,四姊妹後面也有很多別的女子,她們怎麼生活?怎麼理解世界?沒有人關注,但他們都曾認真地生過、愛過、活過,然後死去,無聲無息。
其實這一章命名為“保姆”非常不準確,張家的“乾乾”和現代的“保姆”完全是兩回事,她們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群體,低賤為奴,但事實上承擔了部分母親的角色,每個孩子從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個專職乾乾負責照顧,她們與孩子同床睡覺,形影不離,甚至負責教育,汪乾乾對她分管的宇和就“管頭管腳”,吃飯不準咂嘴、撒飯粒,不準吹口哨。
乾乾們各有特色,女主人陸英(四姊妹的母親)在僕人中發動識字運動,兆和的朱乾乾最勤奮,學習意志最堅強,堅持練慣用九宮格寫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頭,見了不認識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問。兆和每每胡亂應對了以便繼續睡覺,碰到不認識的字也要胡謅,免得丟臉。朱乾乾不久便能自己寫信給孩子,督促他們好好讀書。兆和結婚時,很在乎這個倔強清高的乾乾對夫婿的評價。
有的乾乾等於是《紅樓夢》里所謂的“家生子”,她們跟隨做乾乾的母親,在張家大院、和張家孩子一起長大、一起讀書,她們被稱為“大姐”,而不是乾乾。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夫死後並不以回張家為辱,或因此難過,她文化程度高,擅長彈詞,樂於當大家的活寶。高幹干頗有才華,記憶力超人,是陸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兒金大姐也是夫死後回來幫傭,金大姐幫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陰影,整個戰爭期間無償為張家幹活,戰爭后張家姐妹回到蘇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來日用家居用品。
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能在這讓人感動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種無形的殘酷。張家孩子和乾乾的男孩女孩們一起玩、冒險、讀書,甚至吵架。可是,長到十四五歲,主僕間鮮明的鴻溝就出現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僕人的孩子就是僕人的孩子。從姊妹的角度,這讓她們“失望”,覺得不該長大,以至於友誼結束。但在“奴隸的女兒”眼裡,這“友誼”未必那麼純粹,她們除了跟小姐們一起讀新書,接受新思想以外,還受到了別的什麼樣的教育,這是小姐們不知道的。我所看到的乾乾們的故事,是張家小姐們講出來的,難以想象,如果由乾乾們講述張家故事,和張家背後各家的故事,會是什麼樣子?那個和小姐們一起接受新思想的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滿意家長定親,離家出走後再無消息,應該不久便窘困而死了。娜拉出走後能怎麼樣呢?整個社會結構的組成都沒有給她預留下任何出路和空間。
悲涼之二,是所有的保姆都“對新事物非常抵觸”,“對摩登事物心存懷疑”。汪乾乾用詞粗野,不敬佩讀書人,一身毛病總花很多錢用偏方治療,宇和在校演戲回家晚了,即遭諷刺:“表演,‘裱’什麼‘眼’,還糊鼻子呢。”。男主人對西方藝術的愛好讓她們難堪,她們從雕塑面前過時總掩著眼不去看那些裸體,認為太丑、“不知羞”。她們對文學有自己的欣賞,不喜歡揭露社會不公的現代話劇,而偏愛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傳統戲曲。朱乾乾對於兆和嫁給沈從文非常不滿意,因為看不起沈從文是寫白話小說,而且小學都沒畢業。兆和生孩子讓朱乾乾去北京家裡幫忙,事先把沈從文寫的書都藏起來,免得朱乾乾看了沒好評。結果朱乾乾看了書架上巴金和老舍的書,評價說“稀鬆平常”、“比舊小說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乾乾都不喜歡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親自挑選丈夫。她們認為婚姻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這個前提本身就有問題,因為自由戀愛不能持久。可惜,張家的小姐都是先戀愛再結婚,她們很遺憾不能阻攔。
最後我要說,我很喜歡全書講真話的態度,比如說,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假裝說元和或兆和的婚姻很幸福,也沒有美好和渲染她們的“高貴”。這是一個學者。

合肥四姐妹

充和
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不同。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紮實,也更有自信,就連充和寫的詩歌也更新穎且富於原創性。
充和童年時遠離自己的兄弟姐妹,幾乎總是獨處,只有在特殊時期才有幾個同伴,這些情形必然會影響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和她寧靜的氣質。
三歲前,她就學會了背唐詩,然後又讀了幾種啟蒙書,為繼續攻讀“四書”打下基礎。七八歲時,充和開始學作對子,然後就學習寫詩。充和每天要學習相當長時間,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這些讓她養成了學者的習氣,也讓她有時間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參加姐姐兆和的婚禮,之後她決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勸她參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學入學考試,她自己也覺得不妨一試。
充和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來準備入學考試。考試內容包括四個領域——國文,歷史,數學和英語,其中的前兩門,從她六歲開始,合肥的家庭老師們就已經為她打好了基礎。她在父親的學校中學了一年英語,然後在上海中學里又學了一年,她覺得這門語言並不難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數學。十六歲以前,她從來沒接觸過數學,突然之間,她就要面對證明題和代數方程式。她看不出學數學意義何在,也不明白該從何入手。
那一年,有數千名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爭奪全國最好的五所學校那幾百個錄取名額。考試的當天,家人為充和準備了圓規和曲尺。“我沒用,”她說,“因為我簡直連題目都看不懂。”她的數學考了個無可爭議的零分,但她的國文卻得了個滿分,結果考試委員會破格錄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當年只錄取了一個女生。
充和在北大這所名校就讀的收穫,並不如想象中的大,雖然這裡不乏名師:胡適和錢穆教思想史,馮友蘭教哲學,聞一多教古代文學,劉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詩。但充和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夠理想。當時很多學生參加了激進的政治活動,無法靜心向學,而充和寧願將時間花在學習戲曲上。
清華大學就在北大旁邊,有位專業崑曲老師每周一次在那裡開設非正式的崑曲課,充和與在清華讀書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課。
抗戰期間,充和與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鎮呈貢,小鎮上住著好幾位文藝界的傑出人物,但是來訪客人更喜歡在充和、兆和的住處逗留。充和會吹笛子,所以彈琵琶、彈古箏的人都喜歡上她那兒去。詩人和書法家們也喜歡聚在充和的房間里,他們喜歡這裡的氛圍,也喜歡充和的筆、墨和硯台。充和說,即使手頭再緊,有些東西她還是很講究:“我不愛金銀珠寶,可是筆、硯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來,是因為沈從文幫她在這裡找了份工作。沈從文沒有進入聯大之前,在一個三個人組成的教科書編選委員會裡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編選文學部分之後,他推薦了妻妹充和編選其中的散曲章節。教育部給充和下了聘書,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標準很難衡量充和的學歷,她上過北大,但是沒有拿到學位:1936年她生了病,醫生診斷為肺結核,所以她被迫退學。康復后,她在南京《中央日報》當了一段時期的副刊編輯。隨後戰爭開始了。在充和回到蘇州直至戰爭開始前的短暫歲月中,她的才學顯然已經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書編選委員會的工作時間不太長,一年後,教育部就取消了這個項目。充和並沒有太失望,當然,她需要工作,因為和姐姐們不同,她是單身,必須自食其力,但她決不願意倉皇求職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這時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個是卞之琳,他一生都愛戀著充和,這件事盡人皆知。他寫了很多信給充和,即使他已經知道充和不會選擇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後,他仍然堅持寫那些信。他還收集充和的詩歌、小說,並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還有一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專家。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學問大如充和者也沒法明白:“他一寫就是好幾張信紙,我相信一定寫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歡保持單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間,重慶政府又給了她一份工作,這次是為教育部新建立的禮樂館服務,幫助政府重新訂正禮樂。充和的職責是從五世紀的《樂志》中挑選出適合公共大典使用的樂章來,請作曲家配曲。這份工作很對充和的胃口,她過去就很難忍受各種典禮,現在可以對它們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編選出二十四篇適合的樂章,用最好的書法精心謄寫了兩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編選的篇目后,充和與同事們立即舉辦活動,徵求當代作曲家來為這篇章譜曲。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
充和在這段時間結交的人中,有兩個名人:章士釗和沈尹默。文人之間的這種結交固然源於雙方共同擁有的文學氣質,不過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他們在學識上水平相當,少有分心旁騖之舉。當他們苦學有成之後,就連娛樂也成為文人雅趣。
學者兼書法家沈尹默後來成為了充和的老師。充和第一次來訪時,沈尹默讓她寫了幾個字,然後他給出了“明人學晉人書”的評語。到今天,充和還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褒是貶。
在沈尹默與充和相識相交的過程中,他寫了很多詩給充和,充和也將自己的許多詩給他看,聽取他對這些詩作該如何修訂的建議。
一開始,沈尹默客氣地稱呼充和“充和女史”,後來又改口稱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響下,充和將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擴而大之:早上早起,臨帖練字至少三個小時,如果有時間還要練更長時間。直到八十八歲,她依然保持這一習慣。她運筆寫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樣強壯。
充和在重慶期間,寫出了她最好的詩詞作品。其中有兩首是以桃花魚為題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魚有多重意義:它是“凌空”的隱喻,由於它出現在桃花盛開的時候,所以它也隱喻著春天;此外,桃花魚也暗喻著戰爭期間,許多犧牲在重慶沙洲上的跳傘者。
充和喜歡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和“懸”有關。書法家寫字時手腕要輕懸在書桌上方,掌虛指實,運筆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滯。掌握了運筆的緩急輕重,捕捉到“鸞舞”之姿和“龍騰”之態以後,書法家方可以到達“懸”的境界——“心忘於筆,手忘於書”。
但是戰爭讓她憂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難。美學要轉換成現實並非易事,有時,一點小事也會讓她心情不寧。有一次,章士釗贈她一首詩,將她比作東漢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詩中有兩句讓她很不開心:“文姬流落於誰事,十八胡笳只自憐。”前輩學者的詩中有惋惜她流落他鄉的意思,卻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說,文姬是被擄掠到北方,不得不在異鄉過著異族的生活,她自己卻是因為戰爭才離開家鄉,而且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她也能自食其力,盡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憂傷源於認識到自己離開了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和崑曲,當時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過姐夫沈從文她與傅漢思相識,次年結婚。
傅漢思出身於德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家庭,戰時成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離開德國,當時他十八歲。他們在英國待了一陣子,然後在美國加州定居。漢思獲得了西班牙文學的學位,同時也精通德、法、英、義大利文學。他到中國來,是為著尋求一番奇遇,也是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到中國後幾個月,他就認識了沈從文,他常常與沈從文大談中國的藝術和建築,那時他的中文已經說得比較流利了。
從中國回到美國后,漢思就攻讀中國文學,後來應聘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
一位文化曲人獨特的世紀回憶,穿越抗戰與內戰的烽火,浸潤她六十年來海外移居的生涯,記錄眾多曲人以曲會友的盛事,薈萃他們丹青墨韻的精華,這就是曲壇名家、書苑才女張充和珍藏至今的紀念冊《曲人鴻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戰前後吳梅、杜岑、路朝鑾、龔聖俞、陶光、羅常培、楊蔭瀏、唐蘭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間,身在美國的李方桂、胡適、呂振原、王季遷、項馨吾及身在台灣的蔣復璁、鄭騫、焦承允、汪經昌、夏煥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後姚莘農、林燾、趙榮琛、余英時、吳曉鈴、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聞等作品。
今依據近百歲高齡的張充和本人口述,孫康宜筆錄曲人本事,鉤沉演藝傳承,再現當年沙龍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並對《曲人鴻爪》各家題詞和畫幅做出畫龍點睛的詮釋和導讀。此外,附錄張家舊影、張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題字存目。全書文字書畫,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張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滅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以及許許多多的誰家庭院。

合肥四姐妹

合肥四姐妹
九如巷張家,不僅在蘇州教育史上有重要位置,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也赫赫有名。葉聖陶曾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這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子便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四姐妹。她們的詩意人生牽動人們對那個時代的想象,她們的文集和傳記——《最後的閨秀》、《張家舊事》、《合肥四姊妹》都曾暢銷一時。
20世紀20年代,張家兄弟姐妹們在蘇州九如巷家中合辦家庭刊物《水》,發表自己的作品,後來在離散中停刊。 1996年,《水》又在九十多歲的張允和倡議下復刊,先後在北京、蘇州編輯,隨張家後人流向大江南北,直至大洋彼岸、世界各地。這本家庭刊物被出版家范用先生譽為“本世紀一大奇迹”。 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水》的文選《浪花集》;今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又推出 《水——張家十姐弟的故事》。這本家庭刊物以及他們的家族故事,由此被更多的讀者熟知。
如今,九如巷老家還住著九弟張寰和。九十歲的寰和老人滿頭華髮,交流雖然需要助聽器,但記憶驚人,思路清晰。他繼承父親成為樂益女中校長,終身在蘇州從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