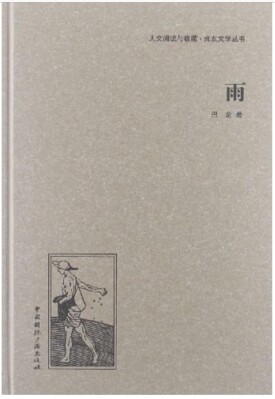共找到38條詞條名為雨的結果 展開
雨
巴金創作小說
《徠雨》,巴金《愛情三部曲》第二部,長篇小說,出版於1933年,出版社為:良友圖書公司。主要講述了《霧》中主人公周如雲的朋友吳仁明的經歷,描寫了舊社會時期各種不同人的思想動態。
《雨》——《愛情的三部曲》之二(巴金)
兩年後的上海,吳仁民的妻子已經病死,陳真被汽車撞死。
此時張若蘭已經嫁給一個大學教授,周如水又愛上了另一個被稱為小資產階級女性的李佩珠。吳仁民對周冷嘲熱諷,但自己很快也墜入情網。戀上他從前幫助過的女學生熊智君。但吳仁民很快發現熊智君的好友就是自己從前的戀人玉雯,她因為愛慕榮華富貴而拋棄過他,現在又因為孤獨想與他重續舊好,吳仁民痛苦地拒絕了她。
李佩珠決心做一個革命女性,拒絕愛情,周如水在絕望中投水自殺。吳仁民也得到玉雯自殺的消息,熊智君為了保護他抱病嫁給了玉雯的丈夫——一個軍閥,並留信鼓勵他追求事業。吳仁民在悲憤中終於振作了起來。
《雨》可以說是《霧》的續篇,雖然在量上它比《霧》多一倍。寫完《雨》,我的《愛情的三部曲》已經完成了兩部。
最後的一部現在還沒有動筆。在《雪》裡面李佩珠將以一個新的女性的姿態出現。
從周如水(《霧》的主人公)到吳仁民(《雨》的主人公),再到李佩珠(《雪》的主人公),這中間有一條發展的路,而且在《雪》裡面吳仁民又會以另一個面目出現,更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這個人。實際上《雨》和《霧》一樣,而且也和將來的《雪》一樣,並不是一部普通的戀愛小說。
徠《雨》的前三章發表以後,一個朋友寫信給我,說:"前幾天讀了你的小說的前三章……陰鬱氣太重,我很為你不安。
你為什麼總是想著那個可怕的黑影呢?……照你的這種傾向發展,雖然文章會寫得更有力,但對於你的文學生命的繼續或將有不好的影響。自然,你在夜深人靜時黯淡燈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了解的。但是我總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他要我"多向光明方面追求"。
朋友說得對。但是他對我多少有點誤解。我似乎生下來就帶了陰鬱性,這陰鬱性幾乎毀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並沒有一刻停止過。我過去短短的歲月就是一部掙扎的記錄。我的文學生命的開始,也是在我掙扎得最厲害的時期。在《滅亡》里杜大心和張為群的頭腐爛了,但是李靜淑並沒有死去。在《家》中高覺慧脫離了那個就要崩潰的舊家庭。在《復仇集》里我哭出了人類的痛苦,在《光明集》里我詛咒摧殘愛的勢力,但是在這兩個集子里我始終沒有停止過"光明就要到來"的呼喊。在《霧》里,絕望的雲霧也並不曾淹沒了希望。最後在《新生》里我更明顯地說:"把個人的生命連在群體的生命上,那麼在人類向上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廣延,哪裡還有個人的滅亡?"總之,即使我的小說的陰鬱氣過重,這陰鬱氣也不曾掩蔽了貫串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的對人類的愛鼓舞著我,使我有勇氣、有力量掙扎。所以在夜深人靜時黯淡燈光下鼓舞我寫作的並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對人類的愛。我的對人類的愛是不會死的。事實上只要人類不滅亡,則對人類的愛也不會消滅,那麼我的文學生命也是不會斷絕的吧。
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斷地掙扎,同樣我在創作里也不斷地掙扎。掙扎的結果一定會給我自己打開一條路。這條路是否會把我引到光明,我還不能說。但是我相信我終於會得到光明的。
現在《雨》放在讀者們的面前了,請你們照你們的意思批評它吧。
周如水:日本海歸學子,認為建設鄉村比城市重要,性格優柔寡斷,家中有父母為其所娶文盲妻子,妻子死去,因為愛情被拒,絕望自殺。
吳仁明:該愛該恨,墜入新的情網,最後在悲憤中振作起來。
李佩珠:拒絕了周如水的追求,決心做一個革命女性。
熊智君:吳仁明曾經的學生,最後為了保護吳仁明嫁給了好朋友玉雯的丈夫。
鄭玉雯:吳仁明曾經的戀人,熊智君的好朋友,愛慕虛榮嫁給了一個軍閥。
“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我要拿痛苦來征服一切,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我在不能夠這樣地生活下去。我不能零碎地殺死自己,,,,”吳仁民是三部曲中我最喜歡的人物,無法避免地被他熱情而浮躁的心情而帶動。這是一顆躁動的靈魂,清晰地看到處於變革浪潮中的社會命運——黑暗未知,定會到來的光明朦朧而遙遠。愛情和事業,永恆的兩個主題,這裡幻化成為了他日日喝醉時內心痛苦的煎熬。巴金先生妙在把握住了人性深處本能的慾望,吳仁民不滿於知識分子築以精神上的空中樓閣,來拯救水深火熱的社會,卻也不能信服革命能夠帶來光明,於是,他在高志元、方亞舟般地革命熱情前退縮了,放大了對情感的依賴,放縱自己沉溺於敏感到神經末梢的愛情之中,用情感來填補內心對於前途未知的恐懼和空虛。前幾天去重慶看了國民黨官邸,南山幽幽的竹林和低調雅緻的小樓,讓我思緒回到國共年代。良知,教養,自傲,風度,種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念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個年代滾滾的時代潮流。 “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我要拿痛苦來征服一切,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我在不能夠這樣地生活下去。我不能零碎地殺死自己,,,,”吳仁民是三部曲中我最喜歡的人物,無法避免地被他熱情而浮躁的心情而帶動。這是一顆躁動的靈魂,清晰地看到處於變革浪潮中的社會命運——黑暗未知,定會到來的光明朦朧而遙遠。
愛情和事業,永恆的兩個主題,這裡幻化成為了他日日喝醉時內心痛苦的煎熬。巴金先生妙在把握住了人性深處本能的慾望,吳仁民不滿於知識分子築以精神上的空中樓閣,來拯救水深火熱的社會,卻也不能信服革命能夠帶來光明,於是,他在高志元、方亞舟般地革命熱情前退縮了,放大了對情感的依賴,放縱自己沉溺於敏感到神經末梢的愛情之中,用情感來填補內心對於前途未知的恐懼和空虛。前幾天去重慶看了國民黨官邸,南山幽幽的竹林和低調雅緻的小樓,讓我思緒回到國共年代。良知,教養,自傲,風度,種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念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個年代滾滾的時代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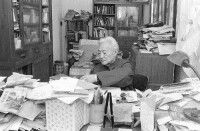
巴金
“巴金”這一筆名源自他在法國留學時認識的一位姓巴的同學“巴恩波”。巴金正在翻譯的著作的作者“彼得·阿歷克塞維奇·克魯泡特金”。他把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為了他的筆名。
巴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914年母親去世。1917年父親也去世。自幼在家延師讀書。五四運動中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反封建的宣傳活動。1922年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發表《被虐者的哭聲》等新詩。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1925年夏畢業后,經常發表論文和譯文,宣傳無政府主義。1927年赴法國,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1929年在《小說月報》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1928年冬回國,居上海,數年之間,著作頗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愛情的三部曲”(《霧》《雨》《電》)。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天東渡日本。次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學叢刊”、“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季月刊》,同年與魯迅等人先後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和《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