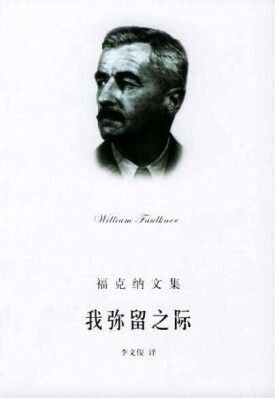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我彌留之際的結果 展開
- 威廉·福克納創作長篇小說
- 美國2013年詹姆斯·弗蘭科執導電影
- 2013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圖書
我彌留之際
威廉·福克納創作長篇小說
《我彌留之際》是美國作家福克納於193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以及“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重要小說之一。
該作講述美國南方農民本德倫為遵守對妻子的承諾,率全家將妻子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的“苦難歷程”。小說完全由本德倫一家、眾鄰居及相關人員五十九節內心獨白構成,多角度講述了這個故事,是作者運用多視角敘述方法及意識流法的又一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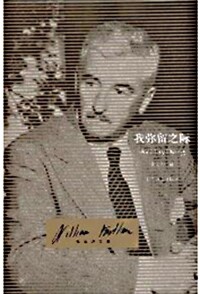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我彌留之際》
| 達爾 | 皮保迪 | 達爾 | 塔爾 | 惠特菲爾德 | 瓦達曼 |
| 科拉 | 達爾 | 卡什 | 達爾 | 達爾 | 達爾 |
| 達爾 | 瓦達曼 | 達爾 | 塔爾 | 阿姆斯蒂 | 卡什 |
| 朱厄樂 | 杜威·德樂 | 瓦達曼 | 達爾 | 瓦達曼 | 皮迪保 |
| 達爾 | 瓦達曼 | 達爾 | 瓦達曼 | 莫斯利 | 麥高恩 |
| 科拉 | 塔爾 | 安斯 | 塔爾 | 達爾 | 瓦達曼 |
| 杜威·德樂 | 達爾 | 達爾 | 達爾 | 瓦達曼 | 達爾 |
| 塔爾 | 卡什 | 安斯 | 卡什 | 達爾 | 杜威·德樂 |
| 安斯 | 瓦達曼 | 薩姆森 | 科拉 | 瓦達曼 | 卡什 |
| 達爾 | 塔爾 | 杜威·德樂 | 艾迪 | 達爾 |

我彌留之際
從字面上說,《我彌留之際》講的是小說中本德倫一家的女主人艾迪臨死以及死後發生在這一家人身上的故事;但從比喻意義上說,《我彌留之際》之中的“我”可以暗指剛剛過去的“繁榮的20年代”,它雖已成過去,但是其影響還深深地留在美國人們的腦海里,20年代還在“彌留”著。毋庸置疑,福克納在小說中觸及到了存在於當時美國社會中的許多社會現實問題。鑒於該小說的重要性以及它創作和發表的時間來說,可以說,《我彌留之際》是20年代創作的最後一本重要的美國小說,也是在30年代發表的第一本重要的美國小說。
在20年代,美國南方地區仍然在努力從1860年代的內戰以及戰後北方對南方的經濟殖民中恢復過來。南方的農民已經處於長期的蕭條時期了。在30年代,各種各樣的合作行為幾乎在整個美國都得到了鼓勵。全國範圍內,“集體主義”成了一種口號。在南方,平民黨黨員(Populist)和各種激進運動人士都在為提高弱勢群體,尤其是貧窮白人農民們的經濟和政治條件而鬥爭,即把他們聚集在一起去反對富有的種植園主和銀行聯盟者。雖然當時平民黨主義(populism)的影響在不斷擴大,但對南方而言,“集體主義”的故事卻有著特別保守的涵義。從傳統意義上說,南方的集體主義理想意味著一種對長期存在的集體關係和風俗的尊重。它意味著要講究禮節形式。福克納把南方這種集體主義理想寫進了小說中。
1930年1月12日,福克納打完了《我彌留之際》,之後他便籌劃投稿給一些有知名度的雜誌,這些籌劃中的小說有30篇於將來的3年中發表。這時他的短篇小說稿酬已超過過去寫四部長篇的酬勞。4月30日,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發表於《論壇》雜誌,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還有《榮譽》、《節儉》和《殉葬》。10月6日,《我彌留之際》在紐約由凱普與史密斯公司出版。12月,同一公司出版了修訂版的《聖殿》。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克萊·劉易斯在其演說中提到了福克納,稱他“把南方從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淚中解放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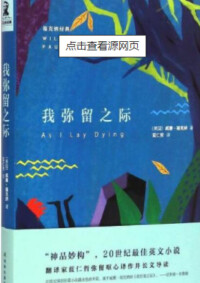
我彌留之際
安斯可以說是整個南方窮苦農民的代表,他身上體現了農民的典型品質。儘管眾多評論家認為“他集懶惰、自私、虛偽、甚至冷酷於一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但從實際上看,這種評價過於主觀,忽略了生存環境對他的影響和他身上的其他特質。作為一家之主,他曾辛苦勞作,以至於“腳八字的厲害,”“腳趾痙攣、扭歪、變形,兩隻小腳趾根本長不出指甲來”;他儉樸持家,為了一家人不挨餓而事事節省,甚至十五年來不捨得裝一副假牙;他為家庭瑣事煩心,卡什的瘸腿、達爾和朱厄爾的叛逆、艾迪的病,全都使他焦頭爛額、心力憔悴。儘管科拉認為他自私自利到無藥可救,完全不值得信任;儘管他在卡什摔斷腿時,首先痛心的是“他(卡什)整整六個月幹不了活” ,在艾迪將死之際仍不捨得請醫生,僅僅是因為心疼診費。但客觀上說,這些言行舉止是生活貧苦的他的本能反應,對一個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生存都有困難的農民來說,他不得不從現狀出發考慮問題,而他的現狀就是缺錢、缺勞動力。他的自私、冷酷很大程度上是被生活所迫,對他來說,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但在運送艾迪的屍體回傑弗生這件事上,他充分展示了一個農民的固執、忍耐和對自己道德信念的堅守。在整個過程中,他只有一個信念,“我親口答應過她,我和孩子們一起用騾子能跑得最快的速度送她去那兒,好讓她靜靜安息”。為了實現這個諾言,他帶著一家人開始了這段艱難旅程。即使在途中遭遇洪水沖橋,人傷馬亡,但他從未退縮。他甚至不惜拿出自己攢了許久的買假牙的錢、典當農具,就為了能將艾迪送到傑弗生安葬。他自始至終堅守著自己的道德觀念,堅定不移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由此可見,他並非人們印象中那樣自私、冷酷。
卡什
卡什無疑是全書中最為正常的人物,他身上具備很多優秀品質。作為兄長,他包容、疼愛弟妹,知道朱厄爾徹夜打工買馬,他就默默的替朱厄爾完成家裡的活;作為兒子,他孝敬父母,母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他都會放在心上。當聽到艾迪說如果有肥料的話她就試著種花時,他馬上“就拿了只烤麵包的平底鍋到馬棚去裝了滿滿一鍋馬糞回來”,讓母親種花;在艾迪彌留之際,他一絲不苟、不分晝夜的趕製棺材以給母親“帶來自信,帶來安逸”。在眾多兒女中,他是最關心父親的一個,在大雨中,他自己淋雨卻讓父親穿上雨衣到一旁休息。卡什的身上體現了福克納一直宣揚的勇敢、忍耐、同情等精神。在整部小說中,卡什話語不多,但他卻用行動證明自己對家人的愛。在送葬這件事上,他像往常一樣沒有過多的發表意見。但從小說中可以看出,卡什雖木訥卻並不愚蠢,他不可能不知道這趟旅程的艱辛,但是他義無反顧的踏上這條送葬路。哪怕半路為救棺材摔斷腿,他也要堅持下去,忍著劇痛將母親安葬到傑弗生。卡什正是魯迅先生說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他明確的認識到了現實的不幸,但勇於面對並反抗這種不幸,從而獲得新生。
艾迪
艾迪可以說是全書的軸心,一家人的苦難歷程都是為了實現她的遺願而展開的。作為“人”,她沒有直接參與這段歷程。可她的整個人生卻是一段更為坎坷的“苦難歷程”。艾迪是一個悲觀的人,在她看來,“活著就是為長久的安眠做準備”,所以生活對她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她也是一個一直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她嫁給安斯,期望婚姻可以改變她厭惡的教師生活,卻適得其反,因為她無法使自己真正融入到瑣碎婚姻生活中,以至於科拉反覆告訴她“她不是一個真正的母親”,“她對孩子們、對安斯、對上帝欠了債”;她與牧師惠特菲爾德偷情,幻想從他身上獲得慰藉,但卻碰上了一個敢做不敢當的懦夫,使她的願望再一次落空。一次次的失敗使她的內心世界與生活現狀越來越格格不入——她的內心渴望愛卻不相信愛的存在,她期盼為人理解卻從未真正的敞開心扉。在她悲劇的一生中,她從未用正確的生活態度去正視現實。在她看來,活著就是為了等待死亡,所以她從未努力爭取過,甚至從未真正的融入到現實的生活中去感受丈夫、兒女的愛。她的人生中只有失去,沒有未來、沒有希望,所以她只有在孤獨、絕望中耗盡一生。
達爾
達爾也是本書的焦點人物之一。許多評論家認為他是一個“先知”,“敏感、孤獨、偏執,具有神經不正常的人才特有的那種超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能看到不在場的事情和看透別人心裡的想法”。的確,作為小說最主要的敘述者,許多不為人所知的秘密,如:杜威·德爾的懷孕,朱厄爾是私生子的事實等,都是通過他的話語顯現出來的。但他更“是一個固執的喪失理智的男孩子”,他會一遍又一遍地問朱厄爾:“你是誰的兒子?”“你爹是誰,朱厄爾?”很顯然,他知道答案卻不敢向眾人揭穿這個秘密,只能通過傷害別人來掩飾自己的懦弱。他對送葬一事的態度正是他性格的最好體現。他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現實的殘酷性和這件事情本身的荒誕性,但他沒有像卡什那樣坦然面對,卻試圖用更加荒誕的行為阻止這件事。為達到目的,他不惜放火燒馬棚,以期將母親的棺材葬於火海。然而,他的過激行為是毫無意義的,並改變不了什麼,那只是對現實的逃避。這種逃避現實的行為註定他最終會被現實擊敗,不能與其他人一起享受生活。因為“這個世界不是他的,這種生活也不是他該過的”。
杜威·德爾
一直以來評論家們對杜威·德爾的評價都以否定為主。他們認為她有“原始人的氣質,既懦弱卻又兇殘”。事實上講,杜威·德爾並不是一無是處的。在母親艾迪生病期間,是她寸步不離的照顧母親,大熱天里站在母親的身邊“用一把扇子給她扇風”。母親死後,她“俯下身去,把被子從艾迪手中輕輕的抽出來,拉直蓋到下巴底下,又把它撫平、抻挺”。從這些細微的動作可以看出她對母親是充滿關愛的。與母親一樣,她也與人偷情,但被情人拋棄后,她沒有像母親那樣自怨自艾,為死做準備,而是接受了現實,到城裡打胎。即使打胎失敗,即使明明知道了那些葯“不會起作用的”,她還是選擇了接受命運的安排,勇敢的活下去。可能以後的生活會更加艱難,但畢竟,活著就有希望。在反抗不幸的過程中她輸了,但雖敗猶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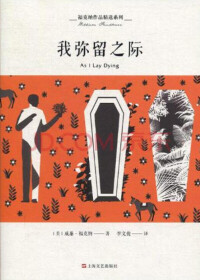
我彌留之際
這部小說有著一切偉大小說的基本元素:如何面對生存和死亡、大自然和人的關係、人性的善和惡、人如何面對上帝、人的家庭內部和外部的關係等等。
在總體上,福克納還是把這次出殯作為一個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行為來歌頌的。儘管有種種愚蠢、自私、野蠻的表現,這一家人還是為了信守諾言,尊重親人感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難與阻礙,完成了他們的一項使命。福克納自己說:“《我彌留之際》一書中的本德侖一家,也是和自己的命運極力搏鬥的”。可以認為,《我彌留之際》是寫一群人的一次“奧德賽”,一群有著各種精神創傷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滿痛苦與磨難的“奧德賽”。從人類總的狀況來看,人類仍然是在盲目、無知的狀態之中摸索著走向進步與光明。每走一步,他們都要犯下一些錯誤,付出沉重的代價。就這個意義說,本德侖一家不失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縮影。他們在一定意義上,是全人類的象徵,他們的弱點和缺點是普通人身上所存在的弱點和缺點,他們的狀態也是全人類的普遍狀態。加繆對福克納作品的主題所作的概括也許是絕對化了一些,但是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說:“福克納給予我們一個古老然而也永遠是現代的主題。這也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悲劇:盲人在他的命運與他的責任之間摸索著前進”。福克納有他自己的概括方式。他說:“到處都同樣是一場不知道通往何處的越野賽跑”。在三十年代福克納所在的世界里,這樣的描述不失為準確與真實。福克納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這樣的現象,應該說是忠實地反映了他周圍的現實。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福克納是一位關注人類的苦難命運,竭誠希望與熱情鼓勵人類戰勝苦難,走向美好未來、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儘管他總是將受苦的人寫得那麼醜陋,在寫成《我彌留之際》前的另一本小說《聖殿》里,福克納寫出了社會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及人心的醜惡,道出了惡的普遍存在,而《我彌留之際》寫出了一群活生生的“醜陋的美國人”。而在《我彌留之際》,福克納依然寫出了人類的勇敢、自我犧牲與理性的一面,譬如朱厄爾、卡什與達爾的那些表現。而且在總體上,福克納是把這次出殯作為一個吉坷德式的理想主義來歌頌的,儘管有愚蠢、自私、野蠻的表現,這一家人還是為了信守諾言,尊重親人感情,克服了巨大困難與阻礙,完成了他們的一項使命。自我凈化是人類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正是基於這個目的福克納才在他的作品中突出了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南方人性格中醜陋的一面。
在福克納那裡,因為他發現了人裡面那種恆久忍耐、正義、為承擔諾言而忍耐、責任感以及人的不可摧毀等崇高品質,人與現實的關係趨於緩解,福克納堅信:人類通過與自身命運的極力搏鬥,可以獲得終極幸福,譬如本德侖太太在彌留之際達到的澄明境界,福克納用自己終身的行動捍衛了自己所監守的信念是真實的、可信的。而《我彌留之際》寫的正是一群人的一次“奧德賽”,一群有著各種精神創傷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滿痛苦與苦難的“奧德賽”。從人類的總體狀況來看,人類仍然是在盲目無知的狀態中摸索著走向光明與進步。每走一步,他們都要犯下一些錯誤,付出沉重的代價。他使我們認識到——人類雖然渺小,卻有著無堅不摧的勇氣,通過自身堅苦卓絕的努力,一定會戰勝所有苦難。
手法
對福克納而言,寫作《我彌留之際》是一次冒險的“技術壯舉”。他使出了所有的招數,譬如內心獨白、多角度敘述和意識流手法等等,正是這些創作方法奠定了福克納作為一個現代派小說家的地位。
荒誕劇
國外的批評家說這是一出悲喜劇。其實最確切的說法應該是荒誕劇,因為它具有五十年代荒誕劇的一切特色,雖然在它出版的1930年,世界文壇上還沒有荒誕劇這個名稱。《我彌留之際》如果與福克納同時期創作的另一本小說《聖殿》並讀,主旨就顯得更清楚了。(《聖殿》的出版在《我彌留之際》之後,其實寫成卻在《我彌留之際》之前。)在《聖殿》里,福克納寫出了社會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及人心的醜惡,寫出了“惡”的普遍存在。而在《我彌留之際》里,福克納寫出了一群活生生的“醜陋的美國人”。
神話模式
《我彌留之際》中敘述的歷險,與《奧德賽》和《出埃及記》就有著內在的聯繫。安斯的妻子與人通姦,與阿伽門農類似;它的神話原型是《奧德賽》,但是它完全沒有《奧得賽》的英雄色彩。在框架上又有點像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和《舊約·出埃及記》中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也曾經歷長途跋涉。只不過,在《我彌留之際》中,已沒有了那種英雄氣概。
意識流
福克納拋棄了傳統的現實主義表現手法,而是借鑒了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1922)的意識流技巧,以及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精華,以意識流蒙太奇的表現手法追求人物的心理真實。因此這是一部比較難讀的小說,如同喬伊斯那本被稱為“天書”的《尤利西斯》一樣,它打破了讀者長期以來被慣壞了的閱讀習慣。對那些只希望在作品中讀到偉大人物和波瀾壯闊的社會畫面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顛覆。然而《我彌留之際》的意義無法抹殺,他在難度和有趣上仍然無愧於世界名著的稱謂。正是從喬伊斯,馬塞爾·普魯斯特,以及福克納等同時代作家的努力,小說才恢復了微小事物、日常事物,甚至是無意義的生活細節在寫作中的地位。通過他們的努力,寫作才成功地從集體記憶力解放出來,真正進入個人內心生活的真實。
非現實主義
三十年代時,美國的一些批評家曾把《我彌留之際》作為一本現實主義小說來分析,把它看成是關於美國南方窮苦白人農民的一部風俗志,一篇社會調查。用那樣的眼光來看《我彌留之際》更是沒有對準焦距。這非但無助於領會作品的主旨,反而會導致得出“歪曲貧農形象”這樣的結論。
因此不應那麼實、那麼死把本德侖一家當成美國南方窮苦農民的“現實主義形象”,他們在一定意義上是全人類的象徵,他們的弱點是普通人身上存在的弱點,他們的狀態也是人類的普遍狀態。在福克納大部分作品中都在表達著同樣的主題,“他們在苦熬。”(They endured)。在故事的開頭,艾迪·本德侖太太躺在卧榻上,她曾得到丈夫的口頭保證,在她死後,遺體一定要運往她娘家人的墓地去安葬。本德侖太太死後,家人遵照她的遺願將屍體送去40英裡外的墓地埋葬而經歷的一次長達十天的苦難歷程。儘管每個人懷著各自的目的踏上送葬之路,儘管一路上有許多自私、愚昧、荒誕的行為發生,但這次出殯仍然具有理想主義的光輝,在與水災、火災的鬥爭中,顯示了人的力量。

我彌留之際
《我彌留之際》在當時是一部具有實驗性的小說,是對西方流行的探求文學模式的諷刺性模擬。是了解福克納其他更具有挑戰性小說的入口。這本小說已經為作者以後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系列作品做好了鋪墊,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本小說中,福克納描寫的不僅僅是南方人,評論家們集中關注其中人類忍受苦難的能力以及最終取勝的人道主義思想。並且他還觸及到了整個現代世界和人類的生存狀況,而這正是福克納整個“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作品系列的主題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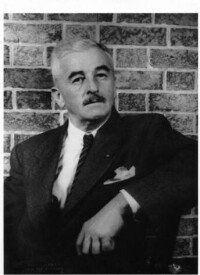
威廉·福克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