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
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
伍修權(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男,祖籍湖北大冶,出生於湖北武漢武昌。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伍修權同志於1997年11月9日零時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伍修權,曾用名吳壽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於湖北武昌。著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

伍修權
到中央蘇區后,伍修權先後擔任閩粵贛軍區司令部參謀,瑞金紅軍學校第一期連指導員、第二期政治營教導員、第三期軍事團教育主任,軍委模範團政委,軍委直屬第三師政委,福建軍區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務。其間,參與編寫了我軍早期的軍事教材,編譯了蘇軍戰鬥條令,參加了第三、四次反“圍剿”。在蘆豐戰鬥中,英勇作戰,身負重傷。1933年秋,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翻譯,參加了第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列席遵義會議。在與“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始終旗幟鮮明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遵義會議后,伍修權任紅三軍團副參謀長,參與組織搶渡金沙江、吳起鎮、直羅鎮等戰役戰鬥。過草地時,提出了戰勝敵人騎兵的有效戰術。在紅軍陝甘支隊期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發布全軍的政治訓令。1936年4月,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參謀長,參加了東征戰鬥。1937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負責邊區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2月,伍修權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他利用其公開合法的身份,幫助指導黨的地下組織,培訓幹部,發展黨員,擴大組織;作為溝通延安和蘇聯聯繫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轉運了蘇聯援助的及西北地區支援的大量抗戰物資;接送了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黨的主要領導和大批革命家,使辦事處成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一處“戰鬥指揮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權返回延安,擔任中央軍委一局局長。其間,在葉劍英的領導下,參加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敵人軍事進攻的方案。1945年參與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軍事工作報告。同年8月,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

伍修權
新中國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權先後擔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副部長、中國駐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職。1950年1月,伍修權隨周恩來總理赴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談,並參與起草中蘇友好條約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審議中國提出的“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案”,伍修權作為中國政府特派代表赴會,在聯合國講台上慷慨陳詞,嚴厲駁斥美國及其同夥對我國的種種誣衊和誹謗,痛斥了美國對我國領土台灣的入侵和戰爭威脅,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尊嚴。在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期間,他積極開展工作,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提出建議,為建立和發展中南友好合作關係、傳播兩國人民的友誼,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權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並曾兼任機關黨委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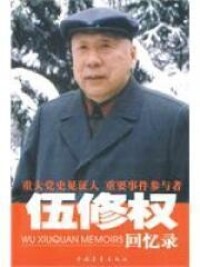
伍修權
1975年4月,伍修權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分管情報和外事工作。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認真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決議,擬制了新時期情報、外事工作方針和規劃,主持修改了軍隊外事工作的有關規定,加強了國際戰略形勢的調查和綜合研究,為黨中央、中央軍委若干重大決策提供了依據。
1980年6月,黨中央決定伍修權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和特別法庭副庭長、第二審判庭審判長,領導參加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勝利完成了這一令世人注目的歷史性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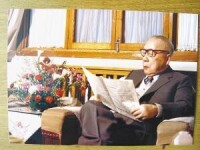
晚年伍修權
在擔任中顧委常委期間,伍修權經常深入基層,聯繫群眾,調查研究,積極向黨中央提出建議。他擔任中顧委在京委員臨時黨委書記時,組織學習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領導完成了中顧委在京委員的整黨。他還擔任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兼檢查組組長,主持查處了若干大案要案。參加了黨的十三大籌備工作。擔任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安全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他還擔任了中蘇、中俄友好協會會長,北京國際戰略學會會長,老區建設促進會名譽會長,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顧問。在祖國統一、香港回歸、維護國內安定團結、倡導兩個文明建設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晚年撰寫了大量回憶文章——《我的歷程》、《往事滄桑》、《回憶與懷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歲。
參與審判反革命

伍修權
領導建設遼瀋戰役紀念館
伍修權同志十分關心位於錦州的遼瀋戰役紀念館,積極籌劃和推動新建遼瀋戰役紀念館。

伍修權同志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奠基

伍修權與部分建館委員會委員視察工地

伍修權在《攻克錦州》全景畫創作現場
主持編輯《遼瀋決戰》

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合影

伍修權
1983年8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陳雲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遼瀋決戰》一書編輯出版會議。會上經陳雲同志提議,成立了《遼瀋決戰》編審小組。並決定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遼瀋戰役紀念館共同負責這個項目。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成立后,伍修權同志作為編審小組成員,實際主持《遼瀋決戰》編輯工作。在伍修權同志及《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其他成員和《遼瀋決戰》編輯部組成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和《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合編的《遼瀋決戰》(上、下)一書,於1988年10月遼瀋戰役勝利四十周年之際由人民出版社順利出版,並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時28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上首發。
《遼瀋決戰》(上、下)出版后,許多老同志反映還應增加和補充資料,才能全面展現遼瀋戰役全過程。於是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決定編輯《遼瀋決戰》(續)。伍修權同志繼續擔任編審小組成員,並親自擔任編輯部主編,全面負責編輯工作。遼瀋戰役紀念館管理委員會和《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合編的《遼瀋決戰》(續)於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侵略朝鮮、中國台灣和干涉亞洲事務的罪行,並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的提案,嚴正要求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召開有關討論美國侵略中國、侵略朝鮮的會議,必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參加。時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年僅42歲的伍修權作為特別代表率團出席了這次會議,參加了“美國侵略台灣案”的辯論,在紐約掀起了一場“紅色風暴”。

伍修權左一喬冠華左二龔普生在聯合國
經過鄭重研究,毛澤東、周恩來最後決定派出伍修權作為特使率團前往,並確定了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伍修權是一位久經革命鬥爭風浪考驗的具有文韜武略的將才,是當時出任中國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選。
1950年10月23日,周恩來以外長名義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任命伍修權為大使銜特派代表,喬冠華為顧問,其他人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員,共9人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訴武裝侵略台灣案的會議。”1950年11月14日,中國政府代表團離開北京,肩負著崇高使命向聯合國所在地---美國紐約成功湖出發。
1950年11月24日早上6點13分,代表團乘坐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班機在紐約機場降落。這天也正是麥克阿瑟宣布要在聖誕節前結束朝鮮戰事回家過節的日子。中國代表團為人關注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二天,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的消息成了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
第一次來到美國的心臟地帶,代表團每個人都保持著高度警惕。伍修權曾回憶說,當時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靜電擦起的火花,都會想一想,這是不是什麼特殊的特務裝置。為了防止被竊聽,大家不在房間里談論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時候,就到飯店旁邊的一個公園裡,邊散步邊商量。
1950年11月27日上午11點20分,聯合國安理會秘書處才通知,正式邀請中國代表團出席安理會會議。中國代表團趕到成功湖聯合國總部已經12點。
中國代表團進入會場的時候,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正在發言。他看到伍修權等進來,立即停下原來的講話,說:“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會議,預祝他們工作成功。”
代表團被工作人員引導到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標籤的席位上。伍修權的旁邊是英國代表楊格,再過去就是美國的杜勒斯。按議程,當天中國代表不發言,只是亮個相,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已經來到聯合國。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聯合國安理會開始討論我國提出的“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案”。在這次會上,伍修僅代表我國政府發表了長篇演說。他首先莊嚴宣告:“我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國人民,來這裡控訴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包括澎湖列島)非法的和犯罪的行為。”接著,伍修權列舉大量歷史和當時的一系列事實后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的武裝力量侵佔了台灣,這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公開直接的武裝侵略行為。”伍修權著重批駁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特別是“台灣地位的確定須待對日和約簽訂”的謬論。他說:“美國政府侵佔台灣,本來是沒有絲毫理由的,然而為了要侵略,它需要找出‘理由’來,說是‘台灣地位還沒有確定’啊,因此美國武裝侵略台灣,不能算是美國侵佔了中國的領土。”“這樣說行不行呢,不行的。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魯門反對1950年6月27日的杜魯門。1950年1月5日,杜魯門說:‘美國及其盟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當時杜魯門先生並沒有以為對日和約已經簽訂了。其次,羅斯福總統反對杜魯門。1943年12月1日,羅斯福總統莊嚴地宣布了‘日本所竊取於中國的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的《開羅宣言》,當時羅斯福總統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為在對日和約簽訂以前《開羅宣言》是無效的,以為滿洲、台灣、澎湖列島在那時以前仍然應當歸日本所有。”“台灣的地位早就決定了,台灣根本不存在什麼地位的問題。台灣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政府武裝侵略我國領土台灣的問題。因此說是由於對日和約尚未訂立,台灣的地位不能決定,應該由聯合國審議的一切說法是同歷史開玩笑,同現實開玩笑,同人類的常識開玩笑,同國際協定開玩笑,同聯合國憲章開玩笑,是杜魯門總統同杜魯門總統自己開玩笑的荒謬絕倫的不值一駁的笑話。”這一席邏輯嚴密、言詞鋒利、對美國政府極盡冷嘲熱諷的話,使美國代表奧斯汀氣得臉紅脖子粗,狼狽不堪。
伍修權進而揭露:“美國的實際企圖是如麥克阿瑟所說的為使台灣成為美國太平洋前線的總樞紐,用以控制自海參崴到新加坡的每一個亞洲海港。”把台灣當成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針對“美國未曾侵略中國領土”之說,伍修權質問道:“好得很,那麼,美國的第七艦隊和第十三航空隊跑到哪裡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們在台灣。任何詭辯、撒謊和捏造都不能改變這樣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武裝力量侵佔了我國領土台灣。”
伍修權又說:“美帝國主義者現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畢竟不是1895年,時代不同了,情況變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國人民,一定能驅逐一切侵略者,恢復屬於中國的領土。”最後,伍修權代表中國政府向安理會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譴責和制裁美國侵略台灣及干涉朝鮮的罪行;第二,使美國軍隊撤出台灣;第三,使美國和其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
奧斯汀對伍修權的發言進行答辯,辯解美國沒有侵略中國,也沒有干涉中國內政。由於根本違背事實,他的發言連西方國家的代表聽了也不時搖頭。伍修權對此質問奧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鮮的美國武裝力量侵犯中國領空,據初步統計,已達200次,毀壞中國財產,殺傷我中國人民。我質問奧斯汀先生這是不是侵略?自從6月27日以來,美國第七艦隊侵入我國台灣領海,以阻止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台灣行使主權。我質問奧斯汀先生,這是不是侵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花費60多億美元幫助中國國民黨集團發動內戰,美國武器殺傷了數百萬中國人民,我質問奧斯汀先生,這是不是干涉內政?”鐵證如山,事實俱在,全場鴉雀無聲,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對奧斯汀。奧斯汀緊張窘迫,再不敢張口。
伍修權的演說2萬多字,講了近2個小時,各國代表通過同聲翻譯收聽了發言內容。這篇大義凜然的發言,轟動了美國和西方世界。事後有人對伍修權說,他演說時嗓門很高,勁頭特足,不論是發言的內容,還是演說的聲音,都把會場給震動了,就像把中國人民憋了多年的氣,一下子吐了出來。
演說結束后,許多人上前同他熱烈握手,向他表示歡迎和祝賀。
伍修權的發言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連一般的美國老百姓也感到非常驚訝,因為畢竟還沒有哪個國家在聯合國這樣譴責過美國人。當時有一個美國黑人對代表團說:“你們這次發言,是有色人種第一次指著美國人的鼻子譴責他們,告訴他們地球上不僅只有美國人存在,而且還有其他的人居住著,你們的控訴使黑人更有希望了。”
1950年11月29日,安理會繼續開會。這次會議開始是討論美國誣衊我國的所謂“侵略朝鮮案”,安排了南朝鮮(今韓國)的代表第一個發言。中國代表團為了表示抗議,拒絕參加這種討論,入場後有意不到會議席就座,而坐在大會的貴賓席上,只參加旁聽。南朝鮮代表發言后,蔣介石的“代表”蔣廷黻接著發言。為了便於同他進行鬥爭,中國代表團又坐回到會議席上,準備伺機予以反擊。蔣廷黻的發言除了照例對中國新政府進行攻擊辱罵外,又為其美國主子的侵略罪行辯解開脫,還引用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證據”。蔣廷黻口口聲聲“代表”中國,發言時使用的語言卻又不是中國話,從頭到尾用的都是英語。待他發言完畢,伍修權馬上要求臨時發言:他首先指出蔣廷黻只是國民黨殘餘集團的所謂“代表”,根本無權代表中國人民,接著伍修權抓住蔣廷黻發言不講中國話的“小辮子”嘲笑挖苦說:“我懷疑這個發言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偉大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語言他都不會講。”這下弄得蔣廷黻十分狼狽,也給了與會者深刻的印象。中國代表團在會上理直氣壯地使用著祖國的語言,並為此“敲”了蔣廷黻一下。這是一段即席講話,事先沒有稿子,只由大會的同聲翻譯臨時譯成外語並廣播出去。當時翻譯這段話的是位中國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經在英國受過教育,英語很出色。伍修權這段即席發言,她翻譯得順暢準確,帶有相當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場聽眾再次感受到中國代表的智慧與風采。
1950年11月30日,安理會繼續就我國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和美國的所謂“中國侵略朝鮮案”進行討論。奧斯汀極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鮮問題上,企圖通過對他們有利的提案,最後又操縱表決器,否決中國關於譴責和制裁美國侵略者、美軍自台灣和朝鮮撤退的提議。對這一無理決定,伍修權強烈聲明:“只准帝國主義侵略,不準人民反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要告訴奧斯汀先生,美國的這種威脅是嚇不倒人的!”
1950年12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多數通過決議,將誹謗我國“侵略朝鮮”的提案列入聯合國議程。中國代表團在這一顛倒黑白的提案通過後,憤怒地離開會場。接著,聯合國又在美國操縱下,宣布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均無限期休會。聯大的這些決定,實際上取消了中國代表團利用聯合國講壇同美帝國主義者進行鬥爭的機會。中國代表團便適時地採取了別的鬥爭方式,把在聯合國會場內的鬥爭,轉移到會場以外來。
1950年12月16日下午,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所在地成功湖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伍修權根據我國政府指示,對各國記者發表談話說,中國代表團是為爭取和平來的,我們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種種合理建議,“但是不幸地、雖然並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集團的操縱下,拒絕了我國政府這個合理的和平的建議,對此,我們表示堅決的反對和抗議”。由於美國政府的操縱,聯合國未能繼續討論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但是,我們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音是應該被全世界聽到的,因此,我把準備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的發言,在這裡分發給大家。同時,我們對於美國政府如此操縱聯合國,不讓我們有繼續發言的機會,表示憤慨。最後,他又通過記者向用各種方式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歡迎和友好的美國人民表示衷心感謝,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戰勝美國統治集團的侵略政策,使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發展下去。
面對美國操縱聯合國無限期休會的情況,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伍修權將軍及其隨員已無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權將軍等於12月19日啟程回國。”
1950年12月19日,代表團完成了此行的任務,離開美國回國。就在代表團準備起程回國的前夕,1950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凍結中國在美資產,包括全部存款。當時代表團帶到美國的經費也存在當地的銀行里。因為即將回國,代表團大部分的錢已經取出來了,最後只有680美元被凍結在那裡,損失不大。
至此,伍修權歷時37天的聯合國之行,勝利結束。這是新中國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聯合國控訴美國對中國的侵略,顯示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氣概,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美帝國主義的威風。美國有的報刊評論說:“紅色中國的外交強硬,這是蔣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伍修權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影
伍修權( 1 9 0 8 — 1 9 9 7年),曾用名吳壽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於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倫奎和父親伍理釗都在清庭駐武昌的湖廣總督衙門下面做事,專做抄抄寫寫文書一類的工作,雖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糧”,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達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長,就在伍修權三歲時,他的故鄉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間湖廣總督衙門不復存在,伍家的兩位書吏也自然丟了差使,全家人賴以生存的唯一經濟來源被切斷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帝制,這對於社會發展和國家民族來說,當然是一件幸事,但對伍家這樣依附於舊體制維持生計的家庭而言,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使他們一下子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伍修權的祖父在貧病之中黯然去世,父親到處求職卻四處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來謀生。伍修權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從小他就跟著幾個哥哥在長江邊揀菜葉薯根,在蛇山上揀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鄰居,大都是工人、手工業者和小販等下層勞動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權的童年夥伴。正是這一切,才為伍修權此後成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環境,從而打下了最初的“階級基礎”。正如他自己在回憶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卻從另一個方面,給我帶來了一些意外的好處,可以說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這裡得到的現實教育,大大有助於自己後來的投身革命。”
由於家境貧寒,孩子又多,伍修權吃飯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難重重。直到1920年他12歲時,還只能在家中幫忙做些雜活補貼家用。不過他也不能算毫無文化,畢竟父輩是書吏出身,也算是讀書人,雖然不能教給伍修權現代知識,卻也讓他基本識字,能背上幾段“子曰詩云”。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第二年,一些熱心人士為了普及教育和喚起民眾,開始面向廣大勞動群眾的子弟辦學,武昌城裡也開辦了一個不收學費的“單級學校”。伍修權從鄰居家的小夥伴那裡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去參加了報名,老師見他已經基本識字,又見他的年齡個頭遠在其他兒童之上,就讓他直接插進小學二年級,伍修權也總算正式開始了他的求學之路。這個武昌重鎮的小學校和今天許多偏遠地區的小學校相比,恐怕都要遜色許多。所謂學校,不過是一間教室,一個老師給四個年級一共四十多名學生輪留講課而已。條件雖然簡陋,伍修權卻依然學得十分起勁,由於這種特殊的教學模式,他可以在那兒同時同地聽到幾個不同年級的課,學習效率倍增,當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級。正當伍修權發奮讀書之時,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這所掛靠在武昌高等師範小學名下的“單級學校”,在辦了一年半之後,因為經費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辦學,伍修權又面臨著失學的命運。所謂天助自助者,由於他入學后一直勤奮學習併名列前茅,老師對他格外器重,在單級學校停辦之時,幫他疏通了有關方面,讓他進入了同樣免費的武昌高等師範附屬小學,並且插入初小四年級繼續讀書,伍修權才得以繼續求學。
由於是一所正規的學校,校方規定每個學生必須穿統一的校服。這一件小小的校服卻難壞了伍家,連吃飯都時常斷頓,哪有餘錢為他添置校服呢?經過再三的請求和老師的同情諒解,學校在免收學費之後,又破例允許他不穿校服上學。於是,伍修權每天穿著家常的舊布衫,背著自製的小書包,走在了整齊劃一的學生隊伍里。由於衣服的關係,聽課時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後的角落裡,列隊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兒都是一個突出的目標,不斷地承受不時襲來的譏諷和嘲笑。這時的伍修權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圍的社會環境已經使他懂得,一個人要自立並受到他人尊重,並不在於他的衣著外表,而是在於他的品行和學識。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裡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強的上進心,穿著上不如別人,學業上卻要高於別人。由於伍修權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謙虛誠懇,使他很快贏得了周圍老師和同學們的尊重和好感,最終順利地完成了在高師附小的三年學習。
二、十四歲少年幸遇恩師,中共一大代表成為他的入團介紹人
1922年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權在高師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級。就在這一年,伍修權的班裡來了一位新老師。這位老師二十五六的年紀,生得方方正正,濃眉大眼,對人滿面春風,又透出一股正氣,一見面就讓伍修權覺得可敬可親。這位老師到班裡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從個頭到學業都高出別人一頭的伍修權,經常和他交談,相互間很快熟悉起來,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這位老師,就是伍修權思想上的啟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區最早的共產黨人陳潭秋。當時,陳潭秋以學校教師為職業掩護,一面領導湖北地區黨的工作,一面傳播革命思想,發現並培養革命青年。他不僅為學生講授語文和歷史等重要課程,還是與學生關係密切的級任老師,相當於今天學校的班主任。在課堂上,陳潭秋不斷地將許多的革命道理和社會知識,點點滴滴地灌輸到孩子們的頭腦中。在講解革命理論的時候,他善於聯繫實際,又不超出講課的範圍,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滲透到他要講的課題中,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他講的道理既新鮮又深刻,語言又很生動和淺顯,對於伍修權這樣求知慾旺盛的青年來說,無異是在革命知識的荒漠上,澆灑下一陣陣甘霖,在正待開發的處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種子。伍修權由於自己所處的家庭地位和環境,正對社會上的許多不公現象感到不可理解,聽了陳老師的講課和言談,思想上的重重迷霧漸漸被撥開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潭秋又組織伍修權等年齡較大又積極上進的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為失學的工人子弟掃盲識字,同時對學生家長和工人家庭進行社會調查,使伍修權比較深入地接觸和了解了勞動人民和無產者的生活狀況,從而啟發和提高了他的階級意識和鬥爭觀念。在此基礎上,陳潭秋又讓伍修權等開始參加一些黨的外圍活動,使他們由普通的學生,漸漸變為一個個初具革命思想的進步青年。
1923年底,經過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黨組織決定將15歲的伍修權和另外二名同學吸收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陳潭秋和當時武漢團組織的負責人何恐作為他們的介紹人。入團的儀式不比今天,既沒有激昂的大會宣誓,也沒有洪亮的集體歌唱,只是下課以後,在一間小屋子裡,由陳潭秋莊嚴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權等三名學生,組織上批准了他們的要求,同意他們成為黨所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隨後,他和何恐同志為伍修權等講解了青年團的任務,對團員的要求和今後的工作等等,同時決定由伍修權和另兩名一起入團的同學,組成高師附小的第一個團小組,並指定伍修權為第一任小組長。儀式雖然簡單,意義卻非比尋常,它可以說是伍修權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正是從這一天起,伍修權正式成為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員。當時,共產黨被簡寫為“CP”,共青團則簡寫為“CY”。
伍修權無疑成了當時武漢地區第一批,同時也是中國第一代的“CY”成員。
三、中秋之夜離鄉北上,初一學生躋身蘇俄大學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權剛剛完成了高師附中第一年的學習。開學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權路過當地黨組織負責人錢介磐老師家門口,錢老師遠遠地就迎上來叫住他,告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談。原來,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中國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一所以孫中山命名的學校,專門為中國培訓革命人才和黨的幹部,以進一步幫助和支援中國革命,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已經籌建就緒,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黨組織,選派一批年輕的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在指定地點集中,然後集體赴蘇學習。湖北的黨組織遵照中央的通知,對所屬的黨、團員和青年骨幹一一作了研究,確定了伍修權和其他一批同志作為赴蘇學習的人選。聽到這個消息后,伍修權欣喜若狂,紅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聖地,是十月革命的發祥地,能夠到那裡學習,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錢老師表達了願意赴蘇留學的意向。
按照中央規定,各地赴蘇人員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於當時黨的經費有限,去上海的路費及個人行裝只能各人自籌解決,這又成了伍家的大難題。雖然全家人對伍修權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異常高興,可是家無餘糧,生活尚且困難,更別說為伍修權整置長途旅行的路費和行裝了。正當伍修權無計可施近於絕望之時,恩師和同窗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權的小學老師張朗軒先生為他送來了多年的積蓄四十元大洋,解決了他的路費和行裝問題,同學何立人將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給了他,幫他抵禦了橫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亞的一路風寒,其他師友也都用各種方式對他表示了支持和幫助,使得伍修權得以順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舉行了一個多年來最豐富的家宴為伍修權餞行,父親破天荒地割回了一點肉,打了二兩酒,母親還為他做了一盤炒雞蛋。吃完團圓飯,父親和三個哥哥將他送上了東去的輪船。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實際上是他們最後的訣別,不等伍修權重回故鄉,他的父親和三位兄長就在貧病之中相繼辭世了。伍修權重回故鄉與母親團聚,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了。
當年10月28日,伍修權和同志們乘上一艘駛往蘇聯的煤船,到達遠東的海參崴后,換乘火車用兩周的時間到達了革命聖地莫斯科,在那裡蘇聯政府為這些中國革命者提供了相當良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當時的中山大學面臨大街,附近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達數層的寬大樓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辦公用房,還有專門的俱樂部,校內設有面積寬闊的大廣場,有專門從瑞典請來的體育教員帶領學生做早操,學校南端還建有一個小花園,供教師和學生們課餘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請來了裁縫為每個中國學員量身製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著裝,然後分編班級,發放了學生證,每人每個月還能領到十個盧布的零用錢。於是,伍修權這個在國內衣著寒酸坐在教室角落裡餓著肚子聽課的窮小子,一下子變成了西裝革履享受當時一流教育和訓練的大學生。
中山大學根據中國學員的文化程度編成幾個班,每班約二十多人。從法、德等國來的同志外語水平較高,編為法語、德語班,從中國去的英語較好的則編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語上課。學習的課程有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聯共黨史、西方革命運動史、東方革命運動史和俄語。在班上伍修權的年齡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別的同學多是大學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剛剛上完初一。由於伍修權的勤奮好學,他這個小小的初中生進步很快,整體成績在這個精英群體中居於中等,超過了許多基礎比他紮實的同志,俄語和政治經濟學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學習,要聽懂教授的講課,學好俄語是一個先決條件,伍修權在俄語學習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當時同學中只有一本劉澤榮先生編寫的俄語語法,伍修權一回宿舍就爭著看,把那些名詞、代詞、形容詞的變格和動詞的變化規律等等,都背得爛熟。為了學習單詞,伍修權專門準備了一個小本子,把所接觸到的新單詞都抄到小本子上,將它們反覆記熟,背熟后再把這一批去掉,換上新的不熟的單詞,再反覆背,如此不斷反覆,辭彙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權還利用各種機會去練習俄語的聽說,通過實際使用來提高自己的俄語水平。如此一來,伍修權的俄語水平在短期內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過翻譯也能大致聽明白教員的授課了。在政治經濟學這門課上,由於伍修權平時對這一學科很感興趣,閱讀了許多教材和輔導材料,加上他的俄語水平不凡,同學們一致推薦由他來擔任翻譯。在課堂上,伍修權流利而準確地翻譯和講解了教員的論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
四、反革命政變陰雲起,文秀才變武將軍
1927年,伍修權來到中大學習已經快兩年了,正當他要結束在中大的學業之時,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為國民黨右翼勢力的叛變而失敗了。中國共產黨人奮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裝起義來回應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在激烈的鬥爭中,黨深感軍事人才的不足,於是通過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從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結業並準備回國的學員中,抽選一批轉入蘇聯各個軍事學校,為新生的人民軍隊培養經過正規教育和訓練的軍事人才。正當伍修權為不能回國參加鬥爭而焦慮不安時,校方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的這一指示,伍修權當即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按照伍修權的條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任意選擇不同的軍兵種及其學科,步兵、炮兵、工兵、騎兵和海、空軍等等,都可以自由報名應試。他考慮到國內的作戰形式主要將是游擊戰爭,其他兵種雖然都比步兵瀟灑和輕鬆,但只有靠兩條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適合國內鬥爭的需要,於是決定學習步兵。
伍修權來蘇聯之前只是一個閱歷不深的青年學生,這兩年雖然學了不少馬列理論,但對當兵打仗還根本摸不著頭腦,於是他決心從頭學起,報考專門訓練初級軍事指揮員的莫斯科步兵學校。校方將伍修權等十一名應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學學生編成一個單獨的中國班,他們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國學員。步校位於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時代就存在的軍校舊址,這裡的環境和中山大學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營式的建築,設有各種訓練器械和室內運動場。學員宿舍也完全是基層連隊的風格,每間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時居住,正好是一個排的建制,每人一張木床一個小櫃,還設有集體的槍架。到了步校,伍修權就換下了他那一身西裝革履的學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頭式的士兵單衣,冬季是拖到腳面的粗呢軍大衣和高達膝蓋的氈靴,完全成了一個蘇軍普通戰士的模樣。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隊完全一樣,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過早餐就上課,一上就是五個小時,上午的操課全部結束后才吃午飯,午休后又是三小時的操課,晚上是自習時間,除了各自溫習功課、整理筆記和閱讀有關書籍,有時還得去聽教員輔導。對伍修權來說,這種生活雖然緊張刻板,卻有十分豐富、充實的內容,讓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穫與長進,因此學習的勁頭始終不減。步校有許多課程不在室內而是在室外進行,比如隊列訓練、射擊投彈、地形學等等,對學員的體能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過,這可難不倒伍修權,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文弱的書生。身為窮人的子弟,長期的勞動鍛鍊出了他強健的體魄,在國內上學時他就是學校運動會上從不缺陣的運動員,曾經在一次運動會上幾乎包攬同一年齡組的全部冠軍,被同學稱為“台炮”,野外的風雨對於伍修權而言已經習以為常了。蘇聯軍隊那時依然重視騎兵,步校的學生也要學習騎術。俗話說“北人善馬,南人善舟”,伍修權這個長江邊上長大的青年連馬都見得不多,要想學會騎馬,難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權就是有股不服輸的勁頭,在不知摔了多少個跟頭之後,他不但能夠用雙手駕御戰馬,還能用兩腿夾住馬肚,在馬上自如地射擊和劈刺,成了技藝精湛的騎手。
冬夏兩季,伍修權要和其他戰友一起到郊外參加野營訓練和攻防演習。夏天,他們要自己搭帳篷,住在戶外;冬天,更是要經受俄羅斯零下幾十度嚴寒的考驗。伍修權常常頭戴只露出面部的氈帽,穿著又長又厚的軍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達一兩尺的積雪中摸爬滾打,前進時一步一個深坑,每一步都邁得十分艱難。在劇烈的運動中,一方面外面寒風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體內又熱得如同火燒。這種異乎尋常的鍛煉,幫助伍修權適應了各種氣候和環境,培養了他克服困難的毅力和勇氣,為以後幾十年的軍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異國佳人留不住中國青年,從伯力到江西萬里赴戎機
到了1929年,伍修權在莫斯科步校已經渡過了兩年的學習時光,這年10月,東北的張學良和蘇聯軍隊發生了邊界衝突,即“中東路事件”,蘇軍急需一批中文翻譯隨軍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選了十名中國同志,伍修權也在其中。戰事結束后,伍修權又被分配到蘇聯遠東保衛局,成了一名專職的翻譯。在那裡,伍修權成了蘇聯軍官,加入了聯共(布)黨,獲得了相當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當時遠東地區有不少華僑,大多是農民,俄語水平不高,蘇聯政府十分需要漢語翻譯協助進行管理,而伍修權受過專業的教育和翻譯實踐的鍛煉,是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又積極肯干,因此深受保衛局領導的器重。為了做好當地華僑的工作,當地辦了一份中文報紙,經常請伍修權將蘇聯報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軍政機關的文件公告譯成中文在報紙上發表,有的還彙編成小冊子出版並分發給華僑閱讀。伍修權筆譯技能嫻熟,下筆速度很快,有時一個周末就能譯出一萬多字,一經發表,就能拿到相應的稿費。當時伍修權手頭可是相當的寬裕,加上開支不大,很快就積攢了一筆不小的存款,還經常拿出稿費請周圍的同志下館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時蘇聯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生活還很艱難,一天只有午餐時才能在白菜湯里見一點肉丁,下館子大塊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蘇聯的那段時間,伍修權不但經濟上非常“小康”,愛情女神對他也十分眷顧。在不少蘇聯姑娘的眼裡,來自中國的青年是理想的戀愛對象,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年輕瀟灑又頗有修養,當時也確實有一些在蘇聯留學的中國青年娶了當地的姑娘安居樂業以致樂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學習期間,步校醫務室一名叫“卡佳”的護士姑娘對他頗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於伍修權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們就開玩笑地將兩人的名字合起來,叫他們“彼契卡佳”。護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權卻沒有表態,後來他奉命調到遠東,這份感情也就沒了下文。到遠東保衛局后,單位的一位女共青團員又相中了他,幾次對他進行暗示,伍修權卻總是裝作沒有理解對方的好意,沒有進行回應。後來,保衛局的領導為了讓他在當地紮下根來,安心工作,也一再動員他找個蘇聯姑娘結婚,主動為他當起了紅娘。
安逸的生活並不能讓伍修權平靜下來,在蘇聯生活得越久,他對祖國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國參加鬥爭的意願日夜縈繞在他心頭。他正是血氣方剛,精力旺盛的時候,成天坐辦公室,啃黃油麵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國的土地上去,和同志們並肩戰鬥。他把自己的想法試探性地向保衛局的領導提了幾次,保衛局的領導哪裡肯放走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才,對他說共產黨員都是國際主義者,在哪兒工作都是為共產主義奮鬥,他在局裡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國不可。幾次碰壁之後,伍修權決心繞過遠東保衛局,向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求助。但是,怎麼才能獲得領導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權使了個“金蟬脫殼”之計。他對遠東保衛局的領導撒了個小謊,說他在莫斯科有個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順便動員她來遠東,在這裡定居下來。領導一聽,大為滿意,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還幫他解決了從遠東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車票,開出了招待所的介紹信,並特批了一筆路費。伍修權心中暗喜,為了不使人產生懷疑,他幾乎沒有帶走任何個人物品,連自己那筆不菲的存款也沒動,隻身趕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權馬上和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取得了聯繫,在代表團負責同志的協助下,伍修權回國的要求終於被蘇方接受,準備在組織的安排下秘密回國。
當時從蘇聯秘密回國的路線有三條,一是繞道歐洲,搭乘遠洋客輪迴國,二是在海參崴搭蘇聯貨輪從海路直達上海或者大連等中國港口。這兩條線路雖然相對安全,卻路費昂貴,耗時費力。第三條是通過中蘇邊境秘密越境,這條路最為便捷,卻也最為危險,伍修權回國心切,就選擇了這一方式。一個黃昏,伍修權換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褲,將作為路費的美鈔和中國紙幣用一條圍腰布捲起纏在腰間,登上一輛馬車,在秘密交通員的掩護下,向邊境駛去。快過國境線時,一個土崗子上的碉堡里傳來了一聲吼:“什麼人?”那是中國軍閥部隊的哨兵在問話。趕車的交通員非常輕鬆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時,邊界兩側的居民常在兩國間來回做工或者倒騰買賣,哨兵見得多了,往往懶得一一盤問,伍修權只聽得碉堡里傳來了幾聲懶洋洋的咕嚕聲,卻沒有人露面,馬車毫不減速,轉眼就把邊境哨所甩在了後面。充滿危險的國境線,由於白軍哨兵的馬虎鬆懈,讓伍修權順利通過了。伍修權趕到了滿洲里的火車站,乘火車到達營口,又從營口搭上了開往上海的客輪,準備在指定的地點等待組織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達上海后,伍修權在預先指定的旅館內,等了接近一個月也沒有同志來接頭。原來,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剛剛遭遇了一場可怕的災難,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供出了我黨的大量機密,許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犧牲,上海的地下黨組織一時間難以恢復正常工作,伍修權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他從萬里之外奔波回國,卻一下子和黨失去了聯繫,剛剛回國的歡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權想來想去,只能咬著牙上街走走。這種做法一方面極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卻也有遇見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權一邊裝作閑逛的遊人,一邊警惕地掃視著過往的人群,突然,一張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發現了和他在遠東地區共同工作過的老同志張振亞!在通常的情況下,和街頭碰見的熟人直接對接組織聯繫是十分危險的,在尖銳複雜的鬥爭環境下,有些人昨天還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變成叛徒和敵人。但伍修權此時別無選擇,憑藉對張振亞的了解,他相信張振亞是可以信賴的,於是他悄悄地走了過去,向張振亞說明了自己的情況。伍修權是幸運的,張振亞同志並沒有暴露,而且還和組織保持著聯繫,他把伍修權的情況向上級組織作了彙報,在上級的安排下,伍修權離開上海坐船來到香港,一路輾轉,穿越了閩西山區,最終到達了他萬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蘇區。
一到蘇區,他這個經過蘇聯正規軍校教育的軍事人才,馬上就發揮了作用。紅軍剛剛從白軍手中繳獲了一些馬克沁重機槍,都是蔣介石花了大價錢從德國的兵工廠里買來的,這對連步槍數量都不夠的紅軍而言可是火力強大的重武器。可是當時戰士們對於這種新裝備的使用和維修,還一無所知,只能看著這四個人才能扛動的大傢伙乾瞪眼。伍修權到了以後,稍稍擺弄了幾下,馬上讓這些重機槍噴射出了密集的彈雨,在戰場上大顯神威,讓戰士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很快,擔任紅軍學校校長的葉劍英就發現了這個人才,親自點將,挑選伍修權做教員,為紅軍學校的學員們講解射擊學原理。就這樣,經歷了千錘百鍊的伍修權回到了國內革命鬥爭的大舞台,為他傳奇的革命人生揭開了新的一頁。
伍修權是一員儒將,戎馬生涯幾十年,幾度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參與機樞,籌劃大局,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建立了卓著的功勛。葉劍英元帥曾經稱讚伍修權同志“文武雙全”。
伍修權是我軍陸、海、空三軍院校建設的開拓者之一。留蘇回國后,他就在中央蘇區新創建的紅軍學校執教,為培養我軍早期指揮人才和建軍骨幹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他兼任過東北軍區軍政學校校長,著力培養軍事人才。抗戰勝利之初,一批日本空軍人員向我軍投降,伍修權根據彭真同志指示,親自出面做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們為我軍工作,使我軍能夠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起義,輾轉到達東北葫蘆島,伍修權代表毛主席、朱德總司令歡迎和慰問起義官兵,並以他們為基本力量,在丹東參與籌建了我軍第一所海軍學校。他以極大的熱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設與發展,為我軍空軍、海軍的創建做了人才準備。
伍修權還是我軍情報工作的卓越領導者,他非常重視對情報的搜集和研究。戰爭年代,他善於把隱蔽鬥爭手段與公開合法鬥爭方式結合起來,通過各種渠道捕捉有價值的情報,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務,為黨中央、毛主席決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資料和對策建議。他到總參謀部工作后,大力加強情報戰線的思想、組織、作風和手段建設,開拓了我軍情報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視對世界形勢的分析與研究,經常組織有關人員研討國際戰略格局的發展趨勢,親自掌握國際重大事件的動向,及時向中央提出報告和建議,為黨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提供依據。
新中國成立后,伍修權轉入外交戰線,成為周總理處理外交事務的得力助手。他作為新中國的代表,作為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來於世界各國,頻繁出現於國際政治舞台,在尖銳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身負重任,不辱使命,表現了新中國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風采。
伍修權是我軍軍事外交的開拓者和領導者。1938年2月,他擔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根據中央指示與蘇聯接觸。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蘭州成為我黨我軍對蘇軍事交往的重要樞紐,接轉了蘇聯為支援我國抗戰派出的自願航空隊,接收了由蘇聯運來的軍援物資。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權擔任軍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我方負責人,工作中既要和國民黨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國人打交道。他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在戰場上奪到的東西,絕不能在談判桌上失掉,為此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圓滿完成了黨賦予的任務。1975年4月,伍修權在任副總參謀長期間,主管軍隊外事工作。他按照鄧小平同志確定的大政方針,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團影響,頂住“四人幫”干擾,主動配合國家外交,積極開展軍事外交,邀請外國軍事代表團來華訪問,同時派出軍事技術考察小組學習外軍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增進了我軍與友好國家軍隊的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