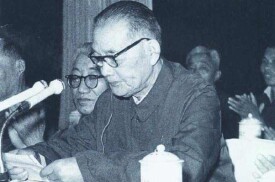李汝祺
中國遺傳學家
李汝祺(1895—1991)中國遺傳學家。 1895年出生於天津市的一個小商人家庭,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由於經濟原因他10歲才開始入小學。因聰穎勤奮,連續跳了三次班,5年中完成了7年的小學學業。離小學畢業還差1年時考入了當時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18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農學系學習畜牧學。1923年畢業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動物學系研究院,從師於世界著名遺傳學家摩爾根教授,在他領導的實驗室進行果蠅發生遺傳學研究工作,1926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學位論文,成為該實驗室第一位獲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

李汝祺
在大學的活動
1926年李汝祺回國后在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任副教授。翌年,轉而應聘為北京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1935年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進修,從事細胞遺傳學研究,1936年回國繼續在燕京大學任教至1942年。1942—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李汝祺任中國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45年秋季,在北京醫學院解剖科任教,兩年後轉北京大學理學院動物系任教授兼醫預科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1989年退休。
在學術組織的活動
1950年中國動物學會恢復活動,在北京大學動物系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李汝祺被推舉為該會的理事長,任職至1956年。197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國遺傳學會,會上李汝祺教授被推選為理事長兼《遺傳學報》主編,任職至1983年。在他任職的四年中,中國遺傳學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分會,大力推動遺傳學的學術交流和普及工作,並舉辦了若干次講習班,提高了大、中學遺傳學和生物學的教學質量。學報由季刊發展為雙月刊。中國遺傳學會於1982年加入了國際遺傳學會的組織。
歷任職務
李汝祺曾任北京博物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遺傳學編委、主編等職務。李汝祺於1953年加入民盟,1958年被推選為北京市民盟常委,1979年任民盟中央委員,1983年為民盟中央顧問委員會顧問。他還是北京市政協的常務委員。
相關貢獻
李汝祺熱愛祖國,忠誠於教育事業。1948年他在英國倫敦大學生物系進修時,完全了解當時在蘇聯所發生的對摩爾根學派不公正的待遇,但當他獲悉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時,出於對國民黨政府腐敗的憎恨,他懷著慶幸國家得到新生的喜悅心情,於1949年夏返回祖國任教。當李森科的不正學風波及到中國后,李汝祺不苟同於當時國內對摩爾根學派所進行的錯誤做法,憤然中斷了遺傳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潛心學習馬列主義著作,並改而從事動物生態學的研究和講授畜牧學課程。1956年李汝祺應邀參加了在青島召開的遺傳學談會,會上他坦誠而有說服力地闡述了自己的學術觀點,批判和澄清了許多混亂的思想,並讚揚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他所寫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的文章,毛主席看后非常讚賞,建議《人民日報》轉載,並把標題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將原來的標題作為副標題,還親自為之寫了按語,於當年5月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此文發表后對推動我國遺傳學的健康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對科學地闡明百家爭鳴方針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人民日報》轉發了李汝祺的文章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於5月1日轉發了這篇文章,在轉發時,不僅加了一個新的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在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辦的,新標題是毛澤東擬定的,編者按語也是毛澤東撰寫的。
李汝祺的這篇文章有一個複雜的歷史背景。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不同的觀點、流派,是很自然的事。但利用行政力量強行推行自己的觀點,壓制別的觀點,在蘇聯有過深刻的教訓。遺傳學領域李森科學派對摩爾根學派的壓制就是典型的例子。1948年,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權力發起了對摩爾根學派的粗暴批判,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蘇聯的做法很快傳入了中國,在當時學習蘇聯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也採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壓制摩爾根學派,著名的科學家談家楨就因為信奉摩爾根學派而不被允許開設遺傳學課程。
這種做法在1950年就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注意,當年夏天,毛澤東就對某大學粗暴對待摩爾根學派學者的材料作了批示,認為這樣的作風是不健全的,對這所大學的領導要作適當的處理。經過調查,解除了這位領導在大學的職務,並且批評了他對待知識分子和對待科學問題的簡單粗暴的做法。但在當時的總的背景下,這個糾正還是一個開端,範圍和程度都是有限的。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雙百方針”,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四天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向黨內外宣布了這個方針,他說: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講話推動下,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聯合在山東青島召開了一次遺傳學座談會。這次會議認真貫徹了百家爭鳴的方針,各種不同的學派和觀點都得到了充分的發表意見的機會,可謂各抒己見,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盛會。這也是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們國家為了貫徹落實這個方針而召開的一次影響巨大、效果很好的會議。
毛澤東對這次會議也很看重。會後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竺可楨,向他了解青島會議的情況。在竺可楨介紹時,還不停地插話,表示對會議的肯定,並且鼓勵竺可楨:“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不要怕。”
遺傳學領域的糾錯顯示了“百家爭鳴”方針對推動科學健康發展的巨大威力。但在黨內,對於“雙百方針”還有不理解甚至抵觸的情緒,在知識分子中間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顧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繼續思考如何通過爭鳴和交鋒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通過爭鳴和交鋒發展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1957年2月,他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雙百方針在這個講話里佔有重要的位置。
李汝祺的文章在這種背景下發表出來,引起毛澤東的重視是很自然的事。毛澤東把遺傳學領域發生的事件上升到我國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這個簡潔明快的提法,不僅是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高度概括,也體現了毛澤東對百家爭鳴方針的極力推動。
後來,毛澤東又幾次約見竺可楨,一直到1974年冬天,在長沙養病的毛澤東還特地囑託王震路過上海時給竺可楨帶了口信,問為什麼這幾年沒有見到竺可楨發表的文章。遺傳學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似乎有著特殊重要的分量,也許,這與1956年遺傳學領域開了百家爭鳴的先河,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繫吧。
早期成就
在研究工作方面李汝祺教授亦甚重視。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胚胎學,細胞學和遺傳學方面。他是第一個把早期細胞遺傳學介紹給中國的學者。1927年第一期出版的《美國遺傳學報》(Genetics)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是李汝祺教授關於黑腹果蠅發生遺傳學的研究結果。在他的論文發表八年後,美國學者才開始進行對黑腹果蠅發育致死胚胎學的研究。隨後在1929年李先生與畢瑞吉斯共同發表了《果蠅翅端缺刻的缺失區域》論文。論文證明了不同發育時期所發現的同一缺刻基因,在其染色體缺失的同一區域缺失的長短不同,會導致果蠅的生殖力和生活力的差異。以上的研究成果也為後來研究一些染色體的缺失畸變(Poulson(1940))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1930在《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上發表了《巨大蟈蟈的精子發生和其染色體的研究》,這是我國首篇研究昆蟲染色體的論文。1932年至1933年與談家楨教授共同發表《瓢蟲鞘翅色斑的變異》和《瓢蟲鞘翅色斑的遺傳》,首次指出色斑的遺傳都是由獨立孟德爾因子負責傳遞的,為後來研究瓢蟲色斑遺傳打下了基礎。1934年發表了《發現在中國鳥中一種六條染色體的馬蛔蟲》。20世紀30—60年代他開展刺腹蛙、黑斑蛙及北方狹口蛙個體發育及其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研究,共發表了11篇論文。
“發生遺傳學”的開拓者
1936年在《Genetics》發表了《果蠅殘翅種在高溫下的發育》,實驗結果證明在蛹期用高溫31℃處理對殘翅的增長不起任何作用。但對剛剛由受精卵孵出的幼蟲卻表明高溫對殘翅發育影響很大,其中有些殘翅發育趨向正常翅的大小。對翅毛數目的檢查發現翅面增大是由細胞數目的增多,而不是個別細胞面積增大造成。這表明高溫促進中胸芽的發育,增加了細胞分裂的速度,進一步影響了翅芽細胞分裂速度。該項研究證明果蠅的器官發育既有其階段性,又有其延續性。這一研究成果對錶型模擬(Phenocopy)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例證。1955年,瑞士胚胎學家哈同(E. Hadorn)的德文版《發生遺傳學與致死因子》一書才出現。1961年馬克爾特(C. L. Markert)和烏爾斯普龍(W. Ursp-run)二人把散見於各方面的材料匯總起來,合寫了《發生遺傳學》,創立了這門學科的體系。由此可見,應該說李汝祺教授是“發生遺傳學”的開拓者之一。
後期研究
1955—1966年,李汝祺教授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用X-射線及60Co的低劑量照射雌鼠不同發育階段,研究其對卵巢發育的影響;搖蚊唾腺染色體在個體發育中的結構可逆性變化及其超微結構、組織化學的研究;馬蛔蟲(六條染色體)的減數分裂的研究以及黑斑蛙、金線蛙和北方大蟾蜍的染色體組型及其帶紋等研究。遺憾的是有關輻射遺傳及搖蚊多線染色體超微結構等方面的研究結果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只保存了一些搖蚊科研資料,經整理后,於1985年與吳鶴齡共同在《遺傳學報》上發表了《搖蚊唾腺染色體的研究。I,第四染色體的組織化學分析》和《搖蚊唾腺多線染色體的研究。II,第一和第二染色體在幼蟲到成蟲期間的可逆變化》二篇論文。
解放后的研究
李汝祺教授的專著《發生遺傳學》將於1985年初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在細胞學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李教授作的中國馬蛔蟲染色體研究,他第一次發現具有三對染色體的馬蛔蟲,有別於歐洲二對染色體的馬蛔蟲。解放后的數年中,李汝祺教授指導研究生詳細地研究了中國馬蛔蟲的減數分裂,並寫成論文。可惜論文未能發表就毀於文化大革命中。六十年代初期李教授從事放射遺傳學及用電鏡觀察果蠅和搖蚊唾腺多線染色體的發泡of現象的工作,遺憾的是文革一場浩劫毀掉了遺傳。(HEREDITAS (Beijing) 7 (1)" 2-3 1985)
所有的研究課題,全部正常活動都停止了。直到1977年教學秩序逐漸恢復后,為了追趕現代發生遺傳學的國際水平,李汝祺教授不顧八旬高齡。領導科研小組在停止了十年的研究基礎上,又增加了四項研究項目:
(1)原核生物的遺傳;
(2)細胞超微結構的研究;
(3)細胞的離體培養及脊椎動物性染色體的研究;
(4)脊稚動物的系統發育與其同工酶演變。
合作研究
李汝祺教授在性格上是一個內向的人,他不善於也不喜歡錶現自己,他珍惜時間講究效率,他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貢獻給了遺傳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李汝祺教授從事多年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著作甚多。除了在美國發表的五六篇文章外,李教授在三十年代即編寫了《人類生物學》一書,在該書遺傳學部分介紹了當時國際上對“優生學”的看法。四十年代他編寫了《生物學綱要》,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五十年代他還和李競雄教授合譯了《普通細胞學》,與張宗炳教授等合譯《卵子發生》,與江先群教授合譯了《受精》。另外李教授根據講授"細胞遺傳學刀課程整理的十三篇文章在《生物學通報》上連載,做為大學課本在教學中使用。
影響
1981年由科學出版社彙集成冊為《細胞遺傳學基本原理》。李教授對科普文章亦很重視,早在五十年代就曾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寫了《消滅老鼠》的通俗小冊子。1982年他不再執教后,很快又寫出了“談談遺傳學中若干基本問題”在《遺傳》雜誌連載並即將出版單行本。李汝祺教授熱心學術活動,早在三十年代末他就與生物界同仁組織成立了“北京博物學會”。該學會出版了《北京博物雜誌》,其中發表了數十篇論文。並曾擔任1940-1941年度的會長。1950年,中國動物學會召開解放后的第一次會議,李教授被推舉為理事長直到1956年這一職務由秉志教授接任為止。1978年中國遺傳學會成立,李教授被選為第一任理事長兼任《遺傳學報》主編。在他任職的四年期間對遺傳學及遺傳學會的發展均給予了大量的指導,貢獻了力量。他的品德,他的學問以及他對遺傳學事業的獻身精神應成為廣大遺傳學工作者的楷模。
果蠅發生遺傳研究的先驅
李汝祺1923年在摩爾根的指導下進行染色體畸變對果蠅發育的影響的研究,經過3年的艱辛工作,通過了博士論文,並在1927年以題為《染色體畸變在黑腹果蠅發育的效應》的論文發表在第一期“Genetics”雜誌上。這是最早的有關黑腹果蠅發生遺傳的研究。他利用具有各種染色體畸變(如缺失、重複、異位等)的品系進行雜交,造成其子代中純合子的死亡,然後仔細檢查其致死效應在果蠅發育早、晚期不同階段中的出現時間。結果證明缺失多在卵子期死亡,純合的重複只是拖延了整個發育時間,不一定死亡,雜合的缺失卻與純合的重複相似。實驗還證明Y染色體的存在與否並不影響當代的胚胎髮育。在這篇論文發表8年後,美國的D.F.普魯遜(Poulson),才開始進行對黑腹果蠅發育致死胚胎學的研究。又經過6年C.L.馬克爾特(Markert)和W.烏爾斯普龍(Ursprun)二人合寫的《發生遺傳學》出版后,才創立了這門學科體系,由此可見,李汝祺可以說是這一學術領域的先驅。從國外回來后,他還以帶回的黑腹果蠅和國內的瓢蟲為材料,進行許多遺傳學的研究工作,先後發表了10幾篇學術論文。
動物染色體和胚胎髮育的開拓性研究
李汝祺一貫認為細胞學、胚胎學和遺傳學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細胞學是架在胚胎學和遺傳學之間的橋樑。在這方面他通過研究北京西山櫻桃溝的最大直翅目昆蟲“山老虎”(Callimenusm Onos Pllas)的精子形成及瓢蟲(Harmoniaaxyridis Pallas)的精子和卵子形成,以決定它們的性染色體。發現雌性有兩個X,雄性則為X和Y,這是中國研究昆蟲染色體的最早的論文。1933年他又首先報導了中國馬蛔蟲有3對染色體,不同於國外的兩對或一對的物種。他還發現了三倍體蛔蟲(9個染色體)的胚胎,並研究了形成三倍體的機理。發現三倍體是由於畸形的紡錘體所促成的,三倍體卵子是不能完成發育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和助手們又開展了脊椎動物性染色體的研究。
在胚胎學方面,李汝祺研究了四川峨眉山的刺腹蛙、黑斑蛙和狹口蛙的胚胎髮育和變態,並著重研究器官發育與環境的關係,把生態學和胚胎學結合起來,先後發表了10餘篇論文。這些論文論證了刺腹蛙早期胚胎髮育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性;卵子大而且附著力大,神經系統與運動器官(尾芽)的早熟性、無吸盤等都是刺腹蛙適應峨眉山上瀑布下的水流急湍、浮游生物少、溫度較低的環境條件而產生的。北方狹口蛙胚胎的系統研究證明了它的消化道、鰓和肺、血管系統及味覺器官的發育特徵都是適應其生存在不流動而又易乾的雨水積存水窪中形成的。通過這些研究工作,李汝祺建立起以下的概念,即“如果從形態、生理和生態三位一體的角度去研究個體發育,任何器官的發生與變化都具有其適應的意義”。
在遺傳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工作
60年代初期,李汝祺領導一個小組開展放射遺傳學研究,對象是純系小鼠,目的是測量X射線的不同劑量對其卵巢破壞的程度。實驗結果與國外的發現一致,證實了小鼠出生后若干時間內具有高度抗輻射能力,還發現用母體胎盤提取液注射到初生幼鼠體腔內具有抗輻射的功能。同時,他領導另一個小組進行果蠅和搖蚊唾腺染色體亞微結構的研究,特別描述了核仁及鬆散區的亞微結構,這些工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可惜這部分工作由於“文革”未能繼續下去,也未能發表。
1977年後,李汝祺教授重建了北京大學遺傳教研室,並領導了教研室年輕教師們的科研和教學工作。開展了果蠅及小鼠有關群體和發育遺傳學的研究。如他經常從北大燕東園家裡步行到實驗室指導青年教師開展果蠅遺傳學研究,還親自指導他們如何採集和飼養果蠅等工作。對其他科研工作也以同樣的熱情關懷和指導。在教學方面幫助和鼓勵年輕教師開設了細胞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及微生物遺傳學等專門化課程。年邁的李先生不辭辛勞親自為文革后第一批遺傳專業的學生講授了發生遺傳學課程。李先生這種對遺傳學孜孜不倦的追求熱情和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激勵著青年教師奮發圖強努力工作。
李汝祺對教學是有深厚感情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深知一生最幸運的一點是我從1905年開始上學起,一生未脫離過學校”。在教學方面,他是第一位把細胞遺傳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1926—1948年他講授生物學和遺傳學,編寫了遺傳學教材並創建了細胞遺傳學實驗室。通過教學和科研工作,他培養了一大批後來成為我國遺傳學界和生物學界的骨幹人才,如談家禎、劉承釗等著名科學家。在60年的教學生涯中,李汝祺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他主張用“教而不包”的教學方式,他告誡年輕教師和學生們不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遇到問題一定要通過參閱文獻中的間接經驗,並根據自己的實驗工作進行思考和分析再得出結論,萬不可人云亦云,隨風漂流。在工作中他著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還經常對年輕教師講在大學工作比在科研機關有其優越之處,因每年都有新生入學,代謝速度極高,這對教師永遠是一種衝擊力量,如不加緊學習,必將落在新鮮事物之後。他一貫認為師生關係好比一個戰壕中的戰友,同呼吸、共命運,相互間可以志同道合地建立起終生難忘、牢不可破的友誼。他常說當我們想到“教學相長”時,多少會偏重“教”,但若沒有不斷學習的熱誠,是教不好書的。“學”與“教”是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在任何時期,任何事物上“學”比“教”更為重要。所以做為一個教師,首先要向老師學習,其次向同輩學習,而更加重要的是向他所教的對象學習。他在學生面前從不以師長自尊。他認真收集學生的意見,將其中合理的意見融匯到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中去,不斷充實和改進教學。他曾說:“我從學生身上所學到的東西要比我教給他們的東西多得多”。這是他出自肺腑之言。
李汝祺備課十分認真,儘管許多內容已講過十幾遍,但在講課之前至少要備三次課,第一次是寫講稿,他從不滿足於現用的教材,每次都要加點新的實驗和見解;第二次是默記講稿內容和檢查語言的表達;第三次是講課前一小時再打一次腹稿。課後都要做小結。所以他講的每節課都是嚴謹而風趣的,博得學生的好評。他累積了幾十年的教學卡片足有一大箱,看到使人肅然起敬。他認為給學生講課是教師生活中的一項中心任務,如果對講課不重視,說到底,是對教育事業的不尊重。他的教學原則是“忠於人”和“勤於事”,即對同事和學生要誠懇互助,在教學上要勤勤懇懇,自強不息。他雖已年逾古稀,仍不斷搜集新材料,新進展。他說:“寧願一生默默無聞地工作,但事無巨細永遠要兢兢業業,做一名永不知足的小學生。”
李汝祺在幾十年的教學和科研生涯中,出版過多種著作,並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論文50餘篇,后經科學出版社彙集於1985年出版了《實驗動物學論文選集》。出版的專著有《人類生物學》、《普通細胞學》、《卵子發生》、《受精》以及曾作為大學教材的《細胞遺傳學基本原理》等。1982年以後又出版了《細胞遺傳學若干問題的探討》和《發生遺傳學》,後者是他幾十年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總結,這部著作集細胞學、胚胎學及遺傳學知識為一體,體現了他一貫認為的細胞學、胚胎學和遺傳學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的思想原則。出版后得到廣大讀者很高的評價,並受到國家教委的獎勵。他在晚年曾致力於從歷史和哲理角度編寫一部批判在生物學研究中形而上學的著作,可惜因久病卧床而未能如願,不幸於90年代初在北京逝世。
李汝祺治學嚴謹,誨人不倦,生活儉樸,為人正直豁達,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勤勤懇懇,默默耕耘,把畢生精力完全獻給了祖國的遺傳學事業。1983年全國第二屆遺傳學會代表大會後,為了推動我國遺傳學的發展和鼓勵青年科學工作者,以其多年的積蓄設立了“李汝祺動物遺傳學優秀論文獎金”。李汝祺教的治學和為人風範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1895年3月2日 出生於天津市。

李汝祺合影
1923—1926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動物學研究院學習,獲博士學位。
1926年 任復旦大學生物系副教授。
1927—1935年 任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
1935—1936年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進修。
1936—1942年 任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2—1945年 任中國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5—1947年 任北京大學醫學院解剖科教授。
1947—1948年 任北京大學動物系教授兼醫預科主任。
1948—1949年 英國倫敦大學生物系進修。
1949—1952年 任北京大學動物系教授兼醫預科主任。
1952—1989年 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遺傳學教研室主任。
1989年 退休。
1991年4月4日 在北京逝世。
1955-1959中文
《刺腹蛙早期胚胎髮育的適應性》北京大學學報,1955,(1):111-112,(與李秀貞合作)
《中國動物生態學家的當前任務》科學通報,1956,(1):7,(與林昌善合作)
《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光明日報,1957年4月29日。
《北京狹口蛙個體發育的研究I鰓和肺的發生、發展和變化》,1958,10(1):35-52,動物學報,(與江先群合作)
《無尾兩棲類蝌蚪味覺器的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58,(2):235-249(與江先群合作)
《北方狹口蛙個體發育的研究Ⅱ食物對消化系統發育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1959,(1):75-98,(與林志春合作)
1962-1964中文
《細胞遺傳學發展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生物學通報,1962,(2):32—37.
《細胞遺傳學的現況與展望.細胞學進展》,1962,261—274.
《北方狹口蛙個體發育的研究Ⅲ幾種重要血管的發生與變化》.動物學報,1964,16(4):520—531,(與吳鶴齡合作)
《生物科學動態》,1964,2: 2-170
1981-1985中文
《細胞遺傳學的基本原理》,1981.
《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遺傳學卷》,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3, 128―131.(李汝祺主編, 談家楨等副主編. )
《搖蚊唾腺多線染色體的研究I第Ⅳ染色體的組織化學分析》.遺傳學報,1985,12(1):61—66,(與吳鶴齡合作)
《搖蚊唾腺多線染色體的研究Ⅱ第I和第Ⅱ染色體在幼蟲到成蟲期間的可逆性變化》.遺傳學報,1985,(與吳鶴齡合作)
《發生遺傳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實驗生物學論文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生物學綱要》 ,北京大學出版部, 2006年9月4日
1927-1929英文
Ju-chi Li, The effect of chromosome aberrations on development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Genetics, 1927,12:1-58.
Ju-chi Li, Calvin B. Bridges. Deficient regions of Notche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Publication No. 399 of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9, p.91-99.
1930-1967英文
Ju-chi Li, Ph.D. Spermatogenesis and chromosomes of Callimenus onos Pallas.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 1930-1931, 5(2): 1.
Chia-chen Tan, M.S. Ju-chi Li, Ph.D. Variations in the color Patterns in the Lady Beetles (Ptychanatis axysidis Pall. ) .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 1932-1933, 7:175.
Chia-chen Tan, Ju-chi Li. 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ttle (Harmonia axysidis Allas).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34, 68.
Ju-chi Li, Yu-lin Tsui. The development of Vestigial Wi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Genetics, 1936,21:248-259.
Ju-chi Li. A six-chromosome Ascris in Chinese horses. Science 1937, 86 (2):222.
2001英文
Poulson, D.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x-chromosome deficiencies on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Journal Exp. 2001. 83 (2):271.
“我父親是數蒼蠅的。”李汝祺的孩子曾經這樣回答別人關於父親職業的問題。因為李汝祺自己就自謙地說:“其實我就是數蒼蠅的。”
就是這位“數蒼蠅的”,遠渡重洋,成為遺傳學創始人摩爾根的第一位中國博士生。同樣,就是這位“數蒼蠅的”,培養了一批中國遺傳學界的研究骨幹,奠定了中國遺傳學事業的堅實基礎。
在不久前北京大學檔案館校史館推出的一次展覽上,李汝祺先生的部分手稿、學術專著等文物展現了他刻苦求學、追求真理、獻身教育的人生經歷。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學者楷模
1919年,李汝祺懷著科學救國的信念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普渡大學讀書。在普渡大學,他全力以赴投入學習,發奮攻讀,成績名列前茅。據北京大學生物系原副主任林錦湖教授記載,曾有這麼一段故事:
生物化學是一門主要必修課,有幾百名學生上課。第一學期的總評結果,第一名是美國學生,李汝祺屈居第二,彼此心中不服氣。於是在第二學期,他們暗自鼓足勁頭拚命學習。最後期末總評,教授在課堂上宣布,李汝祺名列第一。當時全班二百多名學生統統站立鼓掌祝賀,許多中國留學生更是歡呼雀躍。
李汝祺說:“這不只是我的光榮,也是中國留學生的光榮,祖國的光榮。我強烈地意識到個人的學習知識和祖國的榮辱興衰的密切關係。”
1923年大學畢業,李汝祺獲得碩士學位,以及各種榮譽證書,被校方推薦加入美國大學榮譽學會(“金鑰匙”學會)。
在摩爾根的實驗室里,李汝祺從事果蠅發生遺傳學的研究。為了觀察果蠅發育過程的變化和及時取得實驗材料,他經常不分晝夜連續工作。1926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論文,成為摩爾根實驗室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1927年美國《遺傳》學報創刊號的首篇文章,就是李汝祺關於黑腹果蠅發生遺傳學研究的博士論文--《果蠅染色體結構畸變在其發育上的效應》。此論文至今被國際遺傳學界公認是發生遺傳學的開拓性的經典著作。
林錦湖在追憶恩師時感言:“人們談論科學家的成功,更多看到的是他們的天才和機遇。但是,早慧未必成大器,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書生本色
李汝祺是我國遺傳學的奠基者。他第一個把細胞遺傳學介紹到中國,並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培養了一批後來成為我國遺傳學界研究骨幹的人才。
其中知名的兩棲類脊椎動物分類學家劉承釗院士和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院士,都曾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碩士學位論文。此外,著名生物學家張作軒、金蔭昌、林子明和李肇特都是他的學生。
李汝祺一生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教學和科研經驗,著作甚多。
1981年,凝結李汝祺講授細胞遺傳學多年心血和經驗的著作《細胞遺傳學基本原理》出版,該書被當時的國家教委定為大學通用教材。1982年李汝祺不再執教后,又出版了《談談遺傳學中的若干問題》等著作,他對生物學和遺傳學的思考已升華到歷史與哲學的高度。
1984年,在近90歲高齡時,李汝祺的著作《發生遺傳學》(上、下冊)出版。在著手這部近90萬字的巨著時,他已是85歲的耄耋之年,並正值他終生相依相伴的夫人江先群先生病故。在這部著作中,他把遺傳學、胚胎學和細胞學的基本規律融為一體,既精闢闡述了遺傳學的基本原理,又介紹了分子遺傳學的成就,反映了遺傳學的發展趨勢。這部著作被譽為我國的遺傳學經典巨著,是他留給我國遺傳學界的寶貴財富。
1985年,科學出版社從李汝祺1927~1966年在國內外雜誌上發表的上百篇論文中精選出40篇彙集成《實驗生物學論文選集》出版。此外還出版了《細胞學原理》、《卵子發生》、《受精》等多種專著。
教而不包,虛懷若谷——良師益友
李汝祺在大學講台和實驗室度過了60多個春秋。中國遺傳學界的另一顆巨星,李汝祺的學生談家楨評價他的恩師稱:“李先生虛懷若谷,一生追求真理,他的做人標準是忠於人,勤於事。”
李汝祺認為,辦好學校關鍵是教員。忠、誠、嚴是一個好教員的標準,也是他一生身體力行的教學原則。
忠,是忠誠於教育事業。“青出於藍勝於藍是客觀規律,否則,這個教師在教學上就是一個失職和失敗者。”在李汝祺看來,給學生講課,是一個教師工作的中心任務。
誠,是對同事和學生要誠懇。李汝祺從不以師長自居,善於聽取意見,改進教學。他說,自己永遠是一個“教然後知不足的小學生,從未放鬆對自己的要求”。
嚴,是學風嚴謹,為人師表,勤奮工作,自強不息。李汝祺備課極為認真,在登上講台之前,他至少要備三次課,儘管這些內容他已經講過幾十遍。
60多年的豐富教學生涯,使李汝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在教學上嚴肅、嚴格、嚴謹而生動,又十分風趣。他主張並形成“教而不包”的教學方式,放手發動學生儘早地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是指導,不是引導。
1977年,為了追趕現代發生遺傳學的國際水平,82歲高齡的李汝祺又上講台,為青年教師上課。他滿懷信心,老當益壯,為我國遺傳學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發出最後的衝刺。
李汝祺特別寄希望於年輕一代,為栽培青年遺傳學工作者,默默付出了艱辛勞動。1984年,近90歲高齡的他把自己多年積蓄的1萬元捐贈給中國遺傳學會,設立“李汝祺動物遺傳學優秀論文”獎金,以鼓勵遺傳學界的後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