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姚鍾華的結果 展開
- 雲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
-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姚鍾華
雲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
姚鍾華,雲南昆明人。1959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1964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現任雲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曾先後在北京、巴黎、台北、洛杉磯、費城、昆明舉辦個人畫展。1972年以來多次參加全國美展及國家主辦的前往東歐、巴黎、紐約等地的重要畫展。
姚鍾華,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雲南油畫學會名譽主席。
文/姚鍾華
人類生活在大自然中,人類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熱愛大自然,觀察大自然,崇拜大自然,讚美並表現大自然是人類的天性。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了以自然景物為表現對象的文學、音樂、繪畫。就繪畫而言,在中國叫山水畫,西方稱之為風景畫。二者有很多共同點,又因地域、種族、文化傳統的相異,又有很多不同。近現代以來,隨著相互的交流與互鑒,從互不理解、互相貶低,到互相認可、互相欣賞,以致互相交融,創造了人類共同的藝術成果。
自然崇拜在人類的童年是普遍地存在的。幾乎所有族群都把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湖、海神化了。它們都有了生命,都有相應的神靈。但在中國古代,又賦予了山川人格的力量和哲學的意味。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山水與人格精神相通,這“天人合一”的思想,二千多年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自然觀、山水觀。
繪畫是以感性認識——視覺感受為基礎的,客體的山水與主體人的感受及其表達的合一,正是“天人合一”觀念在山水畫中的體現。石濤說“山川使余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余也,余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余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石濤·《畫語錄》)這裡的“奇峰”當然不僅僅是奇異的山峰;而“打草稿”意味著重組與構建。也即是從“無我之境”走入“有我之境”。也正是“神遇而跡化”。
我是學油畫的,油畫風景寫生是在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光線下,畫固定的對象,是焦點透視的。畫好了,能將景物的空間、色調、質感表現得真切自然,生動強烈。而中國畫家觀察與體驗的方式有自己的特點。郭熙說“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游者,有可望者,有可居者。”(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這裡既是指山川自然,又是指畫中山水。我特別感興趣的是“行”和“游”。這是中國畫家觀察和體驗自然的特有方式。它是立體的、動態的、放鬆的、有趣味的。這與固定位置固定對象固定光線的方法大異其趣。
藝術家的創作風格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他的觀察方式與體驗感受的。我在北京從美院附中到美院讀書九年,暑假回昆,鐵路尚沒貫通,最早連武漢長江大橋都還沒有。汽車換火車,一趟要走八、九天,有時要在中途停下來,甚至住兩天,畫畫寫生再走。汽車在雲貴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緩緩而行,一時到了高山之巔,目極千里群山,有時又到了谷底幽深之處……。1972年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作《黃河》巨幅,我在陝北高原黃水之濱,隻身背著畫夾,頂著酷暑,在觀察著,在一筆一劃的記錄描繪著。在雲南的迪慶高原,我隨馬幫靠兩條腿,翻越過東彩、色紐、格宗等四千米以上多座雪山埡口。渡金川,過溜索,走過多少大江大河,激流險灘……一次我乘火車從北京回昆,到了湘江之濱,紛紛揚揚地下起了大雪,一直到貴州水城。我在列車上飽覽了千里雪山長卷的勝景……。我悟到,這就是“行”,這就是“游”。我悟到,中國山水畫中為什麼會有《千里江山圖》那樣的長卷,為什麼會有黃公望、王蒙那樣的條幅。是中國畫家“行”與“游”的對自然觀察與體驗的方式決定的。“行”與“游”的觀察體驗,對我來說是從被動的,不自覺的逐漸成為了主動的自覺的行為。
1972年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結尾廳創作象徵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幅油畫《黃河》。將去收集創作素材。行前,我去恩師董希文先生處辭行並請教。先生對我說“你要畫的不是一時一地的黃河,不是黃河上的一個景點。你要畫的是千古之黃河,是我們民族生長的地方;是光輝燦爛的歷史,光輝燦爛的民族……”。這是他最後的一課。不僅是對這幅畫的指導,它蘊含的深意讓我銘記終生。
我想到五代北宋那些表現雄山巨野的山水畫,想到荊浩、關同、范寬、李唐、董源……,那是西方風景畫中沒有的。我想能否用油畫的語言,那種色彩的表現力,那種對陽光、空間、體積、質感、機理的表現。畫出一幅雄闊而輝煌的,具有中國作風與氣派的巨幅《黃河》來呢?這成了我作畫的期望與追求。
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堪稱紀念碑式的巨障,“大中堂”,為中國山水畫所獨有。受其感染,我先後創作了《峽谷新顏》、《金沙天塹》、《雨林深谷》、《深谷夕照》、《岡曲河谷》等一系列作品。這類作品與中國山水畫是不同的。它是油畫,要充分發揮油畫的性能,雖然是重構,但景物都處於同樣的空間與光源之下。自然景物的色彩關係,山川結構是有其自然規律及自身的邏輯關係的。
這些創作是以長期的、大量的油畫及水粉寫生為基礎的。這些寫生基本上是遵循著西方的傳統。當然,有的作品在面對實景時,也用了中國畫“三遠”及“以大觀小”之法。在一些作品中,特別是在一些水粉寫生中,由於工具的接近,融入了中國畫的“筆情墨趣”。大量的寫生使我深入地觀察並把握了自然景物造型、色彩、質感、節奏、虛實的規律。所以,我在畫那些大型“油畫山水”時,少有參考。基本上是憑記憶感覺與想象的“默寫”。如中國古人說的“寫胸中之雲煙丘壑”也。
我自幼受到中國山水畫的熏染。那是我的伯父,中醫姚仲逵,能畫一手清雅的山水畫。我的外公王楨是位舊式文人,擅長詩文與書法。他篤信佛教,在他不大的客堂與佛堂里掛著山水畫,讓我看得出神。到了美院附中,有了國畫課,能見到大量李可染、宗其香等先生的原作。而故宮則是我常去的課堂,在那裡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畫——山水畫的魅力。
1962年看到林風眠先生的大展,十分陶醉,想也那麼畫。七十年代初期,常看黃永玉先生用高麗紙,濃墨重彩,橫塗縱抹。既保持了水墨的韻味,又有強烈厚重的色彩。於是買了高麗紙來,畫了不少這類水墨重彩畫,題材多是雲南鄉間的生活與景物。1980年,吳作人、肖淑芳先生來滇,我全程陪同,吳先生作畫時,我在旁埋墨理紙。肖先生說:“你那麼喜歡中國畫,又有那麼好的基礎,為什麼不畫起來呢?一腳就跨過來了。”我很受鼓舞,之後就大量的畫起水墨畫來。我的題材是廣泛的,人物、山水及牛都畫。後來還畫了不少水墨漫畫。當然,山水畫是不少的,也曾臨摹過,但主要還是畫我的生活感受。我長期作水粉油畫寫生。本能的注意大的黑、白、灰關係與色彩關係——雖然以水墨為主,但也要有個調子和色彩的微妙變化的。有次我問吳作人先生:近來在討論“墨分五色”,您怎麼看?他說:無非是水墨畫要有個“調子”。李可染先生為山水畫大師,有次我拿了自己的一批水粉油畫風景寫生去登門求教。他耐心的一一點評。講得有趣極了,他講出了風景畫與山水畫靈犀相通的深刻畫理。我的水墨山水畫不很“傳統”。我也很少稱之為“國畫”,免得有些人又來挑剔。就稱之為“水墨畫”。但在這個實踐過程中,使我更接近了傳統的核心和本質。
無論是西方的風景畫或是中國的山水畫,都源遠流長,有著偉大的傳統,有著眾多的大師及豐富多彩的無數傑作。人生苦短,我們所能學所能做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021年3月8日
 3張
3張郵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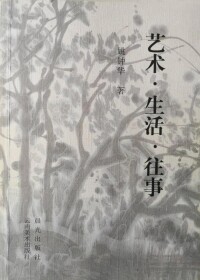 12張
12張出版著作
 11張
11張油畫作品一
 11張
11張油畫作品二
 14張
14張水墨作品
 6張
6張水墨重彩
 8張
8張水粉作品
 4張
4張北京大都美術館收藏
 2張
2張國家博物館收藏作品
 16張
16張中國美術館收藏
 3張
3張雲南片馬抗英紀念館收藏

中央美術學院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