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傅惟慈
傅惟慈,滿族。曾用名傅韋。1923年生於哈爾濱。近代文學翻譯家。
傅惟慈先後在輔仁大學、徠浙江大學(戰時內遷貴州遵義)、北京大學攻讀西方語言、文學。1950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后在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從事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工作。2014年3月16日去世,享年91歲。

傅惟慈(左)
年輕時候,我對文學有夢想。做翻譯是為了忘記當時殘酷的現實,也不排除是為了想表現自己是一個人,而不是“螺絲釘”。可是在“文革”中,我差點兒戴上了一頂詩人的桂冠。
“文革”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比較受寵,因為我善於“鑽空子”: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時候,國內德語文學名著譯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當時周揚找各個專業的專家一起來編“世界文學名著”,共100多本,其中我挑選了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來翻譯,從此開始有些名氣。因為中國人學德語的相對比較少,會德語的人當中又很少是學文學的,所以不到30歲我就“上來了”。
“文革”前兩年,我突然被安排到資料室去打雜,沒有了登講台的資格。學校里貼的大字報有些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紅叉。我想我不寫文章只搞翻譯,最大的罪名無非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吧?
有一天上午,革命群眾都到兄弟院校看大字報去了,我一個人坐在資料室里翻資料。一個年輕的法語老師突然走進來,對我說:“沒想到你還寫詩。”我說:“我是個俗人,從不寫詩。”他告訴我說學校有張大字報說我寫反動詩。幾天之後,看到他給我送來的一張紙條,我才恍然大悟。紙條上面寫的是:“筆記本,遺失后歸還。詩歌殘句,含沙射影。”在那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計劃出一本紀念德國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詩集,約我幫他們翻譯一些德文詩,都是指責統治者奴役人民的內容。我常常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詩,第二天偶然想到該怎麼翻譯就隨手記在本子上。後來這個本子不知怎麼回事丟了,過了幾天才從系裡的秘書那兒領了回來,沒想到就在這幾天里他們把我的筆記本當中的幾頁拍了照片存到檔案中。
假如沒有那個年輕老師的通風報信,我還不知道我“反動詩人”的黑鍋還要背多久。幸虧我還保留有出版社的約稿信。我提交了申訴后很久,系裡的領導小組找我去談話,說我寫反動詩的事情已經解決,但還是要繼續勞動,其中一個人說:“詩雖然不是你寫的,但你翻譯的時候是怎麼想的?就沒有共鳴嗎?”
在翻譯界,傅惟慈的名字和格林連在一起。或許沒有什麼人注意到,今年是格林誕辰100周年,但十多年來格林的宗教小說和驚險小說對中文閱讀與寫作的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可以說這樣一句話,沒有傅惟慈,我們就不會這麼深入格林的世界。
在資料室工作的時候,我每天被困在一間屋子裡面,整理資料、分發報紙,不知道將來會怎樣。幸好,這個時候學校從英國請來了一位名叫威爾遜的外教,他帶來了上百本的英文書,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國的現當代文學。這些書存在資料室由我來登記上架以供老師們借閱,當然我還要負責看看書裡面有沒有什麼“不妥”的內容。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聽說過或者連名字都沒聽過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包括《問題的核心》和《一支出賣的槍》。格林的書很多都是以悲劇結尾,其實我不喜歡看悲劇,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鴕鳥一樣,寧願把頭埋在沙子裡面,但人生路上到處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謹慎,還是有走到絕路的時候。
《問題徠的核心》講的是一個身處絕境的人的心路歷程,我自己當時在資料室里工作,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內心很苦澀、很灰暗,讀到這本書當然感觸很深。
雖然說我寫反動詩的罪名澄清了,革命領導不能把我打成反革命,但又不願意讓我回到人民隊伍中去。1968年的時候,他們把我安排到一個木工廠去做木工,那些木工們幹完活就釣魚、打撲克牌,沒人管我。跟我住一間屋子的木工每天都回到幾里以外的家裡去住,所以對我來說這兒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
就是在木工班的宿舍裡面,我又把《問題的核心》專心讀了很多遍。1979年的時候,我把這本書翻譯了出來,除了是對我自己的紀念之外,我還抱有一個小小的希望: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話,他看到這本書了會知道這個世界上正在遭受折磨的人不止他一個。
在格雷厄姆.格林的書裡面,邪惡的勢力總是戰勝美好的事物。有時我想,格林看到的社會陰暗面是不是太多了?也許是吧,但是我們社會裡面的危機還少嗎?
就翻譯來說,譯者和作者的交流永遠是重要的,這種交流有可能帶來原著的真正精神。
從這個意義出發,傅惟慈和格林的交往絕對不是一次會面那麼簡單,其實更多的是兩人之間的精神契合。只是不知道,《格林文集》何時能夠面世。
格林本人不像他的作品那樣低沉,他看起來是很活潑的一個人。
我同格林通信是在1979年的春天。1978年底的時候我已經把《問題的核心》基本譯完了,有幾個公司名稱的縮寫我不知道怎麼翻譯———我翻譯的時候最怕碰到一個國家有特色的東西,就向國外的朋友寫信請教,這個朋友替我給格林寫了封信,不久,他就回信了。1980年這本書出版后,我給格林寄去了一本。
1981年年初我到德國,又跟格林通了信,他表示他願意跟我在歐洲某個地方相會。
當年的9月左右,我有1個月的假期去英國。格林的家在地中海的某個避暑勝地,不過一年有兩三個星期會回到英國處理一些出版的事情。
恰好當時我們都在倫敦,他就約我到他住的旅館去見了一面。那一年我55歲,他78歲。他精神狀態很好,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而且很熱情、愛開玩笑。
他問我中國人對他的作品了不了解,可惜我回答不出來。我只能告訴他,《一個沉靜的美國人》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但是這以後20年,只有一個短篇在《世界文學》上發表。直到80年代,中國的讀者才逐漸知道英國有個格林。
當時格林還對我說,他並不太喜歡《問題的核心》,雖然這本書一直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我沒有問他為什麼,據我猜測,他可能是覺得這本書不夠深刻,小說里的悲劇感很能打動一般人,但是對人性的挖掘不夠。他說他更喜歡《榮譽領事》(《權利與榮耀》)和《隨姨母旅行》。
到1987年的時候,我又見過格林兩面,談我想在國內出一部20卷的《格林文集》,他很高興,答應給它寫序,還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入選篇目。
可惜因為種種原因,至今為止我沒有實現對格林的承諾。
我是個生性喜歡東奔西跑的人,小時候讀到艾蕪的《南行記》和高爾基的《俄羅斯漫行記》,讓我特別嚮往。
我20歲的時候也一個人離開了家,說是想到前線去抗日,實際上最吸引我的還是自由,我喜歡那種離開現在的感覺。可惜我生不逢時,一輩子有太多時間被耽擱在政治運動中。
1987年4月,我在從希臘的薩洛尼卡去貝爾格萊德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奧地利朋友,我們談到中國、奧地利,也談到文學。他是一個寫作迷,我說一個人對演奏或者寫作著迷,可能是出於自我表現的需要,他說他從沒想過要表現自己,開始是怕忘記一些事情,後來寫作就成了癖好,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而寫了。
他讓我想起我翻譯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裡面的畫家思特里克蘭德,小說裡面的“我”看到思特里克蘭德的怪行后問自己:“如果我置身於一個荒島上,確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沒有別人能看到我寫的東西,我很懷疑我能不能寫下去。”我的奧地利朋友就是一輩子一本書都沒出過,還是堅持寫作。我想,如果我翻譯了一本書,但是知道永遠不會有人給我出版的話,我不會做這個工作,因為如果單純為了自娛,我不會去做翻譯,我會去玩、去旅遊和收集錢幣。
先生的家在西直門附近的一個衚衕里,獨門獨戶的小院,院里栽種著些植物。家裡是不通暖氣的,要取暖全靠空調。這是先生家祖傳的院子,他從1951年住到現在有53年了,免不了擔憂可能哪一天會突然接到搬遷的命令,這是他最感憤恨的。
先生起先不苟言笑,談到他搜集的錢幣的時候才面色柔和,把收藏錢幣的冊子一本本拿出來給我看,說常常有同好者來欣賞,還有商家想要收購他的一些錢幣,而他是斷然不會出售的。
即將離開他家的時候,他突然說你等等,你來看看我的這間屋子。
他帶我去看的是那間屋子裡牆上掛著的照片,都是他在國外旅遊時候拍下來的,放大了鑲在鏡框里。說起在外遊玩的經歷,他顯出非常高興的樣子來。
格林的書裡面,他最喜歡的是《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原因之一就是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黑非洲,他說他從童年開始就喜歡神秘的蠻荒之地,喜歡探險,喜歡驚險小說。
50年代從俄語及德語譯介了匈牙利、波蘭等國當代文學作品,從50年代後期起從事德國文學翻譯。"文革"后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英國語言及翻譯課,主要翻譯英國現當代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成立后,任理事。主要譯作有:〔德〕羅莎·盧森堡《獄中書簡》、《席勒評傳》,〔德〕托瑪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僕》,〔德〕畢希納《丹東之死》,〔德〕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學評論集》,〔英〕格雷厄姆·格林《問題的核心》、《尋找一個角色》,〔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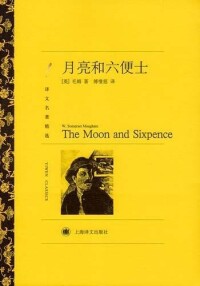
傅惟慈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