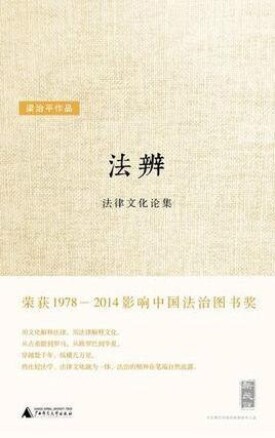法辨
2015年梁治平所著的書籍
本書書名取自作者27歲發表的代表作《法辨》,在收入本書的18篇文章里,13篇刊於《讀書》雜誌,這些文章曾經以其銳利之思想、清新之文風而引人矚目,不但令眾多外行一窺法理堂奧,得以親近法律,同時也使法律學子領略了法律寫作的另一種樣式,耳目為一新。
《法辨:法律文化論集》是梁治平先生的代表性文集,追隨法儒孟德斯,而力圖推陳出新,以“用法律去闡明文化,用文化去闡明法律”的原則,開創了比較法律文化研究的先河,奠定了比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礎,是為法學理論的一部經典之作。這次再版,是2002年版后的第一次修訂版,除了對文字有少量訂正,還刪去了舊版中的一篇文章,並對書名作了相應調整。
梁治平,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法辨:法律文化論集》、《法律史的視界》、《法律何為》、《法律的文化解釋》(編)、《法律與宗教》(譯)、《新波斯人信札》(主筆)、《在邊緣處思考》、《禮教與法律:法律移植時代的文化衝突》等。
榮獲1978-2014影響中國法治圖書獎,排名第一
用文化解釋法律,用法律解釋文化。
穿越數千年,縱橫幾萬里,
將比較法學、法律文化融為一體,法治的精神在筆端自然流露。
——1978—2014影響中國法治圖書評委會

法辨
比較法與比較文化
比較法律文化的名與實
身份社會與倫理法律
“禮法”還是“法律”
“從身份到契約”:社會關係的革命
——讀梅因:《古代法》隨想
古代法:文化差異與傳統
“法”辨
說“治”
從蘇格拉底之死看希臘法的悲劇
中古神學的理性之光與西方法律傳統
——《阿奎那政治著作選》讀後
自然法今昔:法律中的價值追求
文明、法律與社會控制
——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讀後
從權力支配法律到法律支配權力
法,法律,法治
法制傳統及其現代化
情理,道德,自然法
海瑞與柯克
死亡與再生:新世紀的曙光
後記
重印後記
再版後記
這個集子收錄了我自1985年至1988年這幾年中間寫就和發表的大部分文章,共計18篇。其中,13篇發表於北京三聯書店的《讀書》雜誌,它們是全書的主幹。
從內容上看,這組文章涉及領域眾多,時間和空間的跨度也很大,但是在方法和主題方面,它們卻又是非常單一的。這種情形與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方法有很大關係。
我取的基本立場,簡單說就是“用法律去闡明文化,用文化去闡明法律。”這是一個很寬泛的原則,因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極有彈性。就更具體一層的方法來說,或如一位學界前輩所言,我的研究主要是“社會學”的。這裡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我的研究也是“歷史的”和“比較的”,唯獨不是思辨的。我無意建構體系,也不願被“理論”束縛了手腳。我需要一項原則作理論的支點,於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對象。更確切地說,我不是在研究“法律文化學”,而是研究法律文化的個案,研究可以歸在這個大題目下面的種種具體問題。這是我興趣所在。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不可避免要給人以內容上龐雜的印象。
不過,內容的龐雜未必就是主題的散亂。事實上,就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來講,主題是相當集中的。編排此書目錄所以大費躊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按時間順序編排文章的辦法最簡單,但顯然不合適。最後以(1)概說;(2)中國法;(3)西方法;(4)比較中、西法四目作大致的分類,實在也是勉強為之。實際上,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種方法討論著同一個大問題,而且是透著同一種關切的。在我來說,所以要寫下這樣一組文字,不純是為了滿足學術上的好奇心,也是為了對今天嚴峻的現實作出一種回應。
中國古代法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終於在最近的一百年裡消沉歇絕,為所謂“泰西”法製取而代之。但是另一方面,淵源久遠的文化傳習,尤其是其中關乎民族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種種因素,又作為與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頑強地延續下來。由此造成的社會脫節與文化斷裂,轉而成為民族振興的障礙。這一點,經常成為熱衷於“觀念現代化”的人們的話題。
中國的進入現代社會,固然是以學習西方開始,但是中國現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傳統結束。任何一種外來文化,都只有植根於傳統才能夠成活,而一種在吸收、融合外來文化過程中創新傳統的能力,恰又是一種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現。在這意義上說,上面談到的社會脫節、文化斷裂等現象,已經是一種“文化整體性危機”的徵兆了。這樣講並不過分。
辛亥革命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的文化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缺乏說服力。在一班先進青年的眼中,傳統不但是舊的,而且是惡的。揭露與批判傳統,竟成為“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一種“傳統”,這種情形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憂慮。因為事實上,這種對於傳統的批判態度,首先是來自於他們的敏感:他們痛切地感受到這樣一種事實的存在,即在這百餘年的社會動蕩與文化變遷中間,健康而富有活力的傳統已然失落,泛起的只是數千年文化積澱中的沉渣。至少,這一點在今天尤為顯明。
當然,問題也不像人們通常以為的那樣簡單。對於傳統,無論我們所採取的態度是批判的還是創新的,弄清楚傳統及其由來總是必要的前提,而這需要我們以冷靜的做學問的態度去看待歷史和現實。這裡,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比如,就中國古代法律傳統這個大題目來說,我們要弄清的,就不但是中國古時的傳統,而且也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臘、羅馬傳來的遺產。我們不但要問過去的和現在的法律實際上是怎樣的,而且要問它們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羅馬何以能借法律而征服世界?西方的法制憑什麼能夠取中國法而代之?反過來問,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的中國傳統法制因為什麼竟遭消沉歇絕的命運?它不能夠傳世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些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因為歸根結蒂,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環境是以往全部歷史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說,欲知今日,不能不先知過去。未來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識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帶有歷史的印記。在我來說,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總是相對的。—切都是歷史,一切都是當代史。傳統之於我,“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過去,同時還是個歷史地存在的現在。因此,我們不但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追尋傳統,而且可以在當下生活的折射里發現傳統。”(“古代法:文化差異與傳統”)我談西方的法律傳統,講它過去的和現在的理論與實踐,既是要廓清其本來面目,也是想探尋中國現代法律制度後面原本應有的精神;關於希臘法終於隱而不彰的悲劇命運的討論,實際是包含了對中國古代法歷史命運的反省;而就自然法乃至西方中古法律學說所作的討論,同時又未嘗不是對於中國法律傳統以及法學衰敗現狀的觀照與批判。在關於“中國法”的一組文章裡面,即便是最最單純的只講中國古代法律的文章(只有一篇),實際也隱含了與西方文明相比照的背景,透露出我對於過去與現代中國法與中國社會的基本思考。促使我這樣做的,自然不是借古諷今的衝動,而是我對於中國近代歷史演變以及文化發展規律的特定認識。這些文章確實表明了某種現實的關切,但是引領著我深入歷史文化中去的,同時也可說是學術上的好奇心。也許可以說,嚴肅而平正的歷史研究是我關注現實的另一種方式。在我身上,這兩個方面並不矛盾。我從不曾為了現實的緣故去“修正”歷史。相反,在探究所有具體歷史問題的時候,我都為問題本身所吸引,幾乎是為學問而學問的。如果說這裡面依然隱含了重大的現實問題,那只是因為傳統不滅的緣故。
毋庸諱言,在這三年中間,我對於問題的看法也經歷了一個深化的過程。這一點,細心的讀者當不難發現。為H. J. Berman《法律與宗教》所寫的譯序“死亡與再生”一文,在時間上最為晚出,其中所表達的思想自然也比較成熟,只是囿於篇幅和文章的形式,意見的表述末盡系統。這種情況,在那些借“書評”之名寫下的文章裡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或者是一種缺憾。此外,這本集子里關於中國法的討論,基本上只集中於“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而於中國古代法“不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卻沒有正面展開,當然更不可能在此基礎上就中國古代法作全面而系統的總結和評判。完成這項工作需要寫成一本專著,而這正是我現在在做並且已接近於完成的一件事情。這是可以順便加以說明的。
關於這本集子,“自序”里作了必要的說明,只是,這篇序言寫在差不多四年以前。四年來,我的思考未曾停止,我對於事物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這些,自然不能夠完全地表現在序言裡面。為了真實的緣故,我不加改動地保存了原來的“自序”,連同收入本書的所有文章。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又決定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增寫一篇後記,以便簡略說明近年來我思想上的某些發展。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在收入本書的“‘法’辨”(寫於1986年初)和“死亡與再生”(寫於1988年下半年)之間,有一條思想的軌跡可以覓察。事實上,撰寫“死亡與再生”的同時,我還在寫《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一書。對我來說,這是一次系統探究中國古代法律性格的嘗試。它要求我考慮更多的問題,並且在更加廣闊的背景上去把握相關論題。自然,我吸收了自己前此數年中的研究所得,但那也是一次重新消化的過程。結果我發現,當我儘可能祛除主觀上的好惡,用客觀公允的態度去研究中國古代法律與文化及其相互關係時,我對於傳統的法律和文化,漸漸產生出一種新的理解,那即是人們所說的“同情的理解”。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以前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判斷,更不意味著背離我在“比較法與比較文化”以及“‘法’辨”諸文中宣明並且運用的一般方法。恰恰相反,我所以有後來的變化,正是貫徹了“舊方法”自然得出的結果。古人確實不曾以“權利-義務”模式去調整其社會關係;他們的法律確實不以人權為依據,不以保護自由為宗旨;甚至,傳統的價值系列裡面,並沒有“自由”這樣的概念。然而這並不等於說,這樣的一個社會,無真,無善,無美;它的歷史記錄,與人類的一般價值相悖。只有最偏執的西方價值中心論者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事實是,人類社會許多基本問題是共同的,不同人群卻以不同態度對待之,以不同方法解決之,這正是文化差異最根本最豐富的所在。明白中、西之間的差異乃是“文化類型”的不同,就可能對於中國的和西方的法律與文化,都有全新的但肯定是更近於真實的了解,雖然要實現這種可能,還需要具備其他條件和付出艱苦的努力。
最近幾年裡面,我聽到和讀到對我那些已經發表了的文字的各種評說。一位域外的評論者,在讀過包括“‘法’辨”和“傳統文化的更新與再生”(《讀書》1989年3月號。該文寫成於1988年上半年,原系《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的“跋”,《讀書》刊用時有較大刪節。本書未收此文。)在內的若干篇文字之後,說我繼承了“五四”傳統,而能以冷靜的學術研究作基礎,全面批判傳統,探索中國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這位評論者的看法雖然不無道理,但他顯然不曾注意到上面談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義的思想發展。一般的讀者只注意到我文章中的個別結論,而於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義輒不加重視,所以不能更進一步把握我思想的發展脈絡,這也是我常常引以為遺憾的事情。
最後還可以補說一句。對於歷史的“同情的理解”,不但使我學到了許多東西,而且為我下一步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記得1988年夏天,當我把《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書稿交出時,已經精疲力竭,不想就同樣主題再寫什麼了。但是半年以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靜思,我發現,平日許多散漫不相連貫的思想都在對歷史的“同情的理解”中間融合起來。它們把我引向某種更廣闊的背景,更深邃的思考。
我一直試圖用文化去說明法律,用法律去說明文化,現在依然如此,只是程度更深了一層。由於這種變化,過去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結論,對我都有了新的意義。我將在此基礎上做新的研究。那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也許,我可以在未來的十數年時間裡面慢慢地把它完成。
最後,還想說幾句感謝的話。
收入本書的文字,都是已經發表過的。這幾年裡,我因這些文字結識了許多朋友,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他們是讀者,更是良師益友。我始終生活在他們中間,在他們的關注下思考和寫作。應該說,沒有他們,就不會有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也不會有現時的我。這裡,我想特別提到原《讀者》編輯部主任王焱,他是出色的編輯,思想敏銳,學識廣博,懂得如何與作者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我能夠一開始就遇到這樣的合作者,實在是可以高興的事情。另外一位我要特別表示謝忱的是本書責任編輯許醫農女士。我們認識已經有幾年了,她是那種追求真理鍥而不捨的人,她對於事業的執著和在工作上的一絲不苟,總令我肅然起敬。我把這本書稿交與她處理,不但完全放心,而且由衷地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