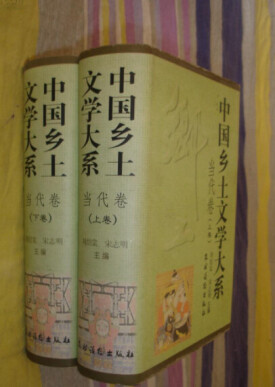鄉土文學
文學流派
鄉土文學,它的出現溯源於魯迅的《故鄉》上個世紀20年代,現代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比較接近農村的年輕作家,他們的創作較多受到魯迅影響,以農村生活為題材,以農民疾苦為主要內容,形成所謂“鄉土文學”。代表作家有彭家煌、王魯彥、許傑、許欽文、王任叔、蕭紅、台靜農,莫言、屈遠志等。鄉土文學是在“為人生”文學主張的影響和發展下出現的。

鄉土文學
1936年,茅盾更進一步指出“鄉土文學”最主要特徵並不在於對鄉土風情的單純描繪:“關於‘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於運命的掙扎。一個只具有遊歷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後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與了我們。”
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一些寓居於京滬大都市的遊子,目擊現代文明與宗法農村的差異,在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下,帶著對童年和故鄉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顯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從總體上呈現出比較自覺而可貴的民族化的追求,開創了現代文學史上堪稱一大創作潮流的風氣。代表作有彭家煌《慫恿》,王任叔《疲憊者》,許欽文《瘋婦》,台靜農《地之子》等。
所謂“鄉土文學”,往往讓人聯想到某種奇趣盎然、野氣撲人的田園詩意,月下小景、水鄉夜色或空靈雨景常常成為鄉土文學恬靜怡人的意境,黃泥的牆、烏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黃狗更是時常作為一種鄉土文學的典型背景,昭示著鄉土文學所可能具備的某種超然的美學特徵。不過,鄉土文學中也亦時常出現粗獷的民俗,剽悍的民風,甚至是野蠻的陋俗、愚昧的鄉規和殘酷的階級壓迫,所以,如果認為鄉土文學只是敘述心靈的凈土或只描寫詩意的田園風光,顯然不夠全面。
鄉土文學中,粗獷的陽剛之氣與纖細的陰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樸人性和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都可以為鄉土文學所容納,而愚昧與文明的衝突,在中國鄉土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更是形成了一個越來越突出的主題。至於鄉土文學的作家,如沈從文,自命為“鄉下人”,劉紹棠,自稱為“土著”,他們的鄉土作品的視野,表面上看,似乎只專註於鄉土間的純美故事;細究起來,現當代任何一位以鄉土文學為題材的小說家,幾乎都無法完全迴避關於現代意識和外部世界對鄉村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以直接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在另一些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作家的敘述可能間接地表達對於現代文明的某種否定態度。但是,不管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家對現代文明取何種態度,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鄉土文學”並非封閉的“鄉土文學”,這一題材的文學類型,總是直接或間接應對著現代文明的挑戰。

孔乙己插圖
在魯迅的鄉土小說世界里,鄉土環境,絕對不是寄予著某種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殺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魯鎮和末庄幾乎可以等同於魯迅所說的“鐵屋子”。大概只有在回憶童年的敘述中,魯迅才對故鄉表現出些許的溫情。而魯迅對鄉土環境的嚴峻態度,實際上為現代的許多進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隨。在鄉土生活和風習畫面中寄予重大的社會命題,顯示社會的變遷和變遷社會中的人物成為中國現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種鄉土文學的敘事模式。
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台靜農、許傑、彭家煌、沙汀、艾蕪,莫言等一批現代鄉土作家,以樸實細密的寫實風格書寫老中國兒女在各自的鄉土上發生的種種悲劇性故事:宗法制的農村中的世態炎涼和無產者的不幸,封建等級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邏輯和社會心理對賤者、弱者不動聲色的毀滅,封閉的邊遠鄉村中原始野蠻習俗對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這些鄉土文學中,被台靜農稱為“地之子”的現代中國農村的老百姓們,承受著巨大的苦難,而小說敘述者所營造出的愚昧與冷漠、悲哀與陰鬱交織著的鄉村氛圍,表現出這批鄉土作家對當時中國最低層社會的強烈使命感。當然,這批鄉土作家同時還是農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銳的諷刺的筆法,寫出了“半人半獸”“土著”人物把持的鄉鎮中的黑暗和無常。

孫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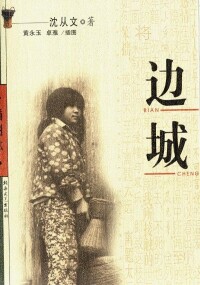
邊城
在沈從文詩意神話的長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說著某種無法抗拒的悲涼。翠翠那一雙“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親人的死亡和情人的離去的現實面前,不也宣告了詩意的神話的破滅了嗎?而沈從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幾乎完全可以將其視為關於鄉村底層人物的一曲悲歌。進入鄉土文學純美境界的沈從文,未必就不懂的社會的苦痛,只不過他是以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邊緣性異質性的鄉土文化的敘述,顯示處於弱勢的邊緣文化中沉靜深遠的生命力量,從而內在地對所謂文明社會的種種弊端構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時期的鄉土文學寫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從文式鄉土文學寫作類型的延續。在汪曾祺等作家的鄉土文學作品中,沈從文式的清澈空靈被賦予更為樂觀明朗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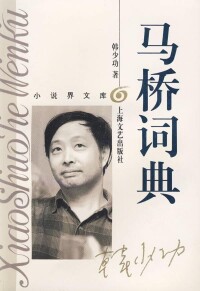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中,鄉土,特別是鄉土語言,成了鄉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歷史深度的縮影和索引。表面上,馬橋是一個靜態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視角,才可能將現代文明對馬橋的影響看得如此透徹,並獲得豐富的詮釋。在“地球村”的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當代,以韓少功、李銳、張煒為代表的中國作家們,已經不再象劉紹棠那樣以自我情感的過分投入作為呵護鄉土文學的寫作姿態,而是站在一個更自覺更冷峻的制高點,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敘述著中華各地鄉土文化的變遷。
莫言在自己的小說里大量運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包括內心獨白、多視角敘事、慢鏡頭描寫、意象比喻、自由聯想等等。
1987年莫言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的中篇小說《歡樂》曾引起文壇較大爭議,由於小說中赤裸裸的描寫和“那些超時空的變換,那些人稱的跳躍,那些幾乎是不加節制的意識流”,令到當時很多保守派文人無法接受,《歡樂》也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對象。當時《人民文學》雜誌的主編劉心武遭到停職檢查。1996年余華重提這篇小說,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一文中說,莫言對事物赤裸裸的描寫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卻因為這篇小說中的母親形象而流下了眼淚。
莫言的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在美國出版后,引起美國文壇不小迴響。美國評論家認為莫言的作品充滿現實主義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數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的一句話——現實即是諷刺。
莫言的中篇小說《幽默與趣味》經常被拿來與《變形記》作比較。他的《小說九段》也被認為是卡夫卡式的荒誕寓言。西班牙凱拉斯出版社創始人安赫爾·費爾南德斯曾說,莫言的文學作品令人們想起兩位熟悉的作家,彷彿是在同時閱讀卡夫卡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
弗吉尼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查爾斯·勞克林說,莫言的大部分小說有一種神話般荒誕的特質。

台灣鄉土文學
1977年4~5月間,《仙人掌》、《中國論壇》等雜誌先後刊出若干討論鄉土文學的文章和尉天驄主編的《當前的社會與當前的文學》專欄。銀正雄在《墳地里哪來的鐘聲》一文中針對黃春明、王拓等的小說,指稱1971年後的鄉土文學有“逐漸變質的傾向”一一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從中再也找不到原來樸拙純真、溫熙甜美的“鄉土”精神,而是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而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等文卻明確提出文學要“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有效地發揮其社會改良功能。這些針鋒相對的觀點形成了鄉土文學論戰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此後報刊雜誌和一些大學紛紛舉辦座談會和發表相關文章,文壇氣氛漸趨熱烈。可以看到,這階段鄉土文學陣營所受的外來壓力還不是很大,它同時也進行著對鄉土文學本身的檢省和討論。
台灣社會性質的厘辨
從1977年8月間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等在《聯合報》上發表開始,論戰進入第二階段。這時的論戰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規模急劇擴大。據侯立朝統計,至該年11月24日止,《中央日報》、《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聯合報》等9家報刊發表的抨擊鄉土文學的文章近60多篇之多(11)。另一方面,《夏潮》、《中華文藝》等也發表了大量反擊的文章。二是情勢更加複雜化。由於與官方有深厚淵源的一批作家、文人的介入,使原有的現代VS鄉土的文壇格局發生變化並進行新的組合。
“鄉土文學論戰”延續至翌年已漸趨平息。從有關聲明中可以看出當時輿論。1978年元月舉行的所謂“國軍文藝大會”上,“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升在大會上發出“團結”的呼籲:“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上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或偏激了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出自年輕人的一種天賦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
“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要麼是農村出身,要麼大部分從鄉村出來,這一代對鄉土生活了解和熟悉,只能寫鄉土,形成這種‘鄉土品種’。現在這批作家都老了,年齡都在60多歲,完成了自己的寫作使命。”
鄉土文學終有一天會消失的,消失過程也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的事,賈平凹並不認為鄉土文學很快就會消失,因為中國有它的複雜性:“現在的社會處於大轉型時期,中國在走城市化道路,但中國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為主的大國,改革開放后,城鄉距離拉大,雖然沿海地區農村慢慢在消失,但在更多地方還保留著農村的面貌。所以,鄉土文學消失要有一個過程。至於以後的文學是個什麼樣子,年輕作家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