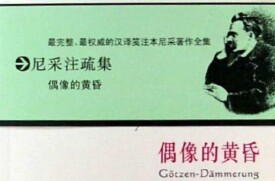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偶像的黃昏的結果 展開
- 2007年7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 同名書籍
偶像的黃昏
同名書籍
《偶像的黃昏》是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傅國涌。
書名:偶像的黃昏
作者:傅國涌
傅國涌先生是位有積澱、有眼光、有情懷的學者。他經年致力於鉤沉近現代史事和人物,發掘暌違已久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傳統,以之建構自己的精神世界,並由此感懷時事、臧否人物。閱讀他的文字,時時能夠感受到一種悵惘、冷峻和憂思,催人警醒,令人低徊。從《追尋失去的傳統》到《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從《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台前幕後》到《偶像的黃昏》,短短兩年多時間,傅國涌就有四本文集問世,其勤奮不難想見。與前三本書各自集中闡釋一個命題不同,《偶像的黃昏》收入的文章比較多樣,既有人物點評,也有世相雜談,既有學術文章,也有讀書雜感。正因為此,本書或許更能見出傅國涌先生的視野和關懷。
書名題作《偶像的黃昏》,乃是源於放在卷首的同名文章——《偶像的黃昏:從金庸到金庸酒——兼談金庸與中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難產》。
對於至今仍然迷信金庸的人們來說,這篇文章實不失為一服清醒劑。在給金庸作過傳的傅國涌看來,金庸仍然是個傳統士大夫:崇拜至高權力,迷信好人政治;認定“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媒體要聽從政府指揮;絕對仇視美國;始終貪戀財富。“他的權力觀、新聞觀、金錢觀、宗教觀以及他強烈的反美、仇美觀點,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貪婪、虛偽、狹隘的一面。一句話,在人格、思想、心理結構上他還沒有走出古代。”傅氏對金庸的這一“定位”與胡一刀相似。胡在《金庸與韋小寶》(2001)一文中說:“所可惜者,身為多壽多金的社會賢達,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進,政見每多保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沖,倒近乎韋小寶了。”傅氏在分析了金庸的四個精神來源后還有此一嘆:“金庸的選擇清楚地告訴我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要成就現代人格是何等艱難。”
除了金庸,被傅氏顛覆的大牌偶像還有李敖和王朔。其中對於王朔的躥紅,傅氏指出“在一個犬儒主義盛行的民族裡,王朔註定了要成為萬眾仰視的英雄、明星。這是一個人們什麼也不信的時代,王朔的登場正好以他那些別開生面的胡侃神聊掩蓋人們內心的恐懼、怯懦和無聊”:“王朔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醜陋與卑怯”。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寫於1976年的一本描述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社會犬儒主義的書中,曾引述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蘇聯異議人士的話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正如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王朔小說可以“上天入地”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與上述幾篇文章相比,《打翻的五味瓶——中國人走近諾貝爾文學獎的歷程》雖非一篇顛覆偶像的文章,但也可糾俗見之偏,從而使不倒的偶像更加真實。比如對於魯迅拒絕諾貝爾獎提名,一般都認為是魯迅自謙的結果,似乎不自謙就一定如何如何,但其實這自謙未嘗不是基於冷靜與理性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