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
來新夏
來新夏(1923年-2014年3月31日),浙江蕭山人,1946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1950年至今,歷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校務委員、圖書館館長、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情報學系主任等職。曾創辦南開大學圖書館系,歷任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教育部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2014年3月31日在天津去世,享年91歲。

來新夏
1946年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在天津擔任中學教師。天津解放后,被選送到北京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同年9月,分配至范文瀾先生主持的歷史研究室讀研究生,主攻中國近代史。在范文瀾、榮孟源等人直接指導下,完成了《太平天國的商業政策》論文,並參與整理北洋軍閥檔案。不久應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廷謬教授之邀,赴南開大學歷史系執教。1980年代同時擔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學情報系主任、出版社總編輯兼社長。一生主要從事古典目錄學及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時在歷史學、文獻學、目錄學、方誌學、鴉片戰爭史、北洋軍閥史、圖書事業史以及清人筆記研究等領域,均有專著問世。自稱“享受寂寞”、“學而不厭”,對古代圖書館事業史、藏書史、目錄學史等專業,研究成果斐然。編寫有《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概要》、《社會科學文獻檢索與利用》、《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清代目錄提要》、《古典目錄學淺說》、《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等;所撰《中國藏書文化漫論》一文,從藏書文化的基本理論、藏書文化的基礎、藏書文化與人文主義精神等,闡述和總結了歷代藏書家與藏書文化形成的規律性和普遍性。主編《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辭典》,書史研究論文20餘篇;歷史學、方誌學領域有《河北方誌提要》、《方誌學概論》、《北洋軍閥》資料叢刊、《中國地方志縱覽》、《中國近代史述叢》、《北洋軍閥史》、《林則徐年譜新編》等,晚年編著隨筆有《三學集》、《學不厭集》、《邃谷文錄》、《結網錄》、《出櫪集》、《隻眼看人》等。
1923年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市。1942-1946年間就讀於輔仁大學。

來新夏
1949年初在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後分配在該校歷史研究室,為范文瀾教授研究生,攻讀中國近代史。
1951年奉調至南開大學歷史任教,由助教循階晉陞至教授。他先後擔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校圖書館館長、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系系主任等職。
1979年在南開大學分校獨力創辦圖書館學專業。
1983年秋,來新夏教授在總校籌辦圖書館學系,於1984年秋公開招生。
《來新夏訪談錄》、《北洋舊事》、《共享閱讀樂趣,豐富美好人生》

來新夏

來新夏
祖父來裕恂很早就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但革命成功以後沒有謀取官職,過著清苦的生活。來裕恂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鈞儒、馬敘倫,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時候,馬敘倫擔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讓他去紹興縣做知縣。但來裕恂不大會做官,做了半年,反而把自己一些積蓄給賠進去了。因為一些公家的活動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個月以後他就掛官辭職走了。他一輩子就幹了這六個月的紹興縣縣長。當地人給他的評語是:書生本色,兩袖清風。
祖父的學問和為人對來新夏影響都很大。來新夏幼年時期是在祖父身邊成長的,祖父指導其讀了很多蒙學讀物,諸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直到來新夏離開祖父和父親到了北方,祖父還不斷寫信教導他應該讀什麼書。
來新夏於1942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那時候的輔仁正處在一個高峰時期,名師雲集,像陳垣、余嘉錫、張星烺、朱師轍都在學校任教。輔仁是個小而精的學校,校舍並不大,但是學風很樸實。當時每個班也就十幾二十個學生,基本上每個學生都能得到老師的親自教授,師生關係很密切。輔仁的史學特彆強。校長陳垣先生就是史學大家,目錄學家余嘉錫也都親自給學生授課。
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社會經濟很差,家裡也比較困難,來新夏在輔仁是連續四年一等獎學金的獲得者,獎金可以維持生活。每次獲獎都會有一個獎章,上面刻著一個“勤”字。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他就靠著連續四年獲得獎學金的資助而堅持了下來。
陳垣先生親自指導來新夏的畢業論文。他當時雖然是校長,但還親自給學生上四門課。他對學生要求很嚴。布置的作業不但必定親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寫一篇,然後和學生的一塊兒貼在教室里,讓學生自己體會:你寫得如何,老師寫得如何。
張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專家,那時候做輔仁的歷史系主任,長得鶴髮童顏,慈眉善目的。據說他中年的時候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他四十歲的時候坐火車去青島,張宗昌的兵看他頭髮那麼白,居然給他讓座。他蘇北口音很重,對學生很親切的。

來新夏《北洋軍閥史》
啟功跟來新夏關係是最密切的,他們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師生關係。他那時教國文和繪畫。來新夏讀大學的時候,因為生活困難,啟功老師就叫他每周日到他家裡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幾個年輕人在他家吃飯。有時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啟師母也幫他們補補釘釘。來新夏60年代接受審查的時候,很多人都疏遠了,啟功是唯一一個關心他的人。1996年有一次,來新夏去啟功家看他,他忽然問來新夏,“你幾歲了?”來新夏說你不知道我幾歲嗎,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說:“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個孔子,一個孟子,都是‘坎兒’,這麼一擠一撞,就都過了‘坎兒’了,這不值得大笑嗎?”
輔仁畢業后,來新夏到天津擔任中學教師。隨後被選送到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分配至歷史學家范文瀾主持的歷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國近代史。在做范文瀾研究生期間,來新夏得以參與整理大批北洋軍閥原始檔案,從此跟“北洋軍閥”結下不解之緣,之後專攻北洋軍閥史,五十年內先後寫了三本相關的書,這也成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來新夏就作為第一批被打倒的對象進了牛棚。之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區農村勞動。在長期勞動改造的年代里,來新夏成了一個勞動好手,學會了壓地、打場、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現在還會趕大車。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間,他安心地寫了好幾本著作。
“文革”當中,來新夏與穆旦成為一對難友。他們一起勞動、聊天,一起洗刷南開大學的游泳池,這一段經歷使來新夏對穆旦的個性和“文革”厄運有深刻的了解。他說,穆旦近年來日益被研究者關注,但很多文章卻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懷穆旦》一文中說“穆旦所遭的厄運,我都耳聞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時期的遭遇則我是唯一的見證人。為了讓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較完整的記述,后死者應該擔負起這種追憶的責任。”

縱橫三學自成一家:來新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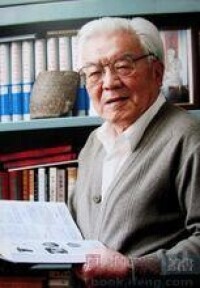
來新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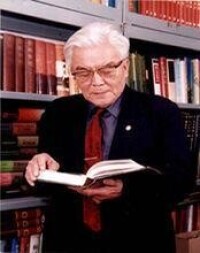
來新夏在查閱資料
30年前,筆者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求學時,適逢來師“文革”后“
解禁”,為我們講授歷代文選。那時來師已年近六旬,在我們眼裡鶴髮英姿,目光深遂,一副學者風範,更兼博學強記,口才雄辯,語言生動,極受學生敬重。
來師知我在檔案系統工作多年,便欣欣然笑道:那我們要算是同行嘍!
在我的錯諤中,來師講起了自己早年曾從事過檔案工作的一段難忘經歷。
先生建國前夕以全優的成績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曾師從陳恆、余嘉錫、啟功等大家。1949年初,被選送到華北大學學習,后被分配到由該校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直接受教於史學大師範文瀾先生。並在范老的指導下,發表了第一篇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史學論文。
這時作為研究生的來師在研究之餘,一項主要工作是對入城后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進行清理和分類。
來師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原始的檔案材料。這批檔案有百餘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整理的場所先是在東石衚衕舊黎元洪府第花園的八角亭,一間面積很大的房間里,有7個人參加整理工作,整理組組長是後來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的唐彪。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上一倒,塵土飛揚,嗆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只能穿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戴著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
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臟污之物,要抖乾淨就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直到下班,不僅外衣一層土,連眼鏡片都被灰塵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條黑杠,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什麼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於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環境關,進行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仔細看看內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談不上什麼研究——但無疑,這為日後研究北洋軍閥史打下了基礎。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袋裝檔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別成捆。為了進入正規的整理工作,集中10來天進行有關這段歷史資料的學習,讀了若干種有關北洋軍閥的舊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隱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從東廠衚衕搬到有四五間寬敞工作間的乾面衚衕,開始整檔工作。我們將檔案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類,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後,分類上架,所以看得比較仔細,並在特製的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容摘要,最後簽上整理者的名字。這次因為已經經過第一輪清理,不再有太多塵土,環境又比較寬敞幽靜,所以大家心情舒暢,休息時和在宿舍里常常交談閱檔所了解到的珍貴或有趣的材料。
我曾利用空閑時間,把自認為有用的材料抄錄下來。積少成多,慢慢
地我已經積累有兩冊黃草紙本。同時為了查對檔案中的事實和加深拓寬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又讀了大量有並北洋軍閥的著作,眼界逐漸開闊,鑽研這方面問題的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我也了解到當時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好的展開,以往的一些著作過於陳舊,而且數量也不大,而新著作幾乎沒有,相關論文也只有零星短篇,所以感到這確是一塊頗有價值的用武之地。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這段整理檔案的經歷,可能就沒有今天研究北洋軍閥的這些成績了。
“我以我是新中國第一批檔案工作者為榮!”年近九旬、被人民日報與季羨林等同稱為國學大師的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來新夏先生如是說。

來新夏《學不厭集》

來新夏《三學集》
第三點是一定要尊重傳統,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謂創新是在前人基礎上的創新,決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點,歷史是在很公正地篩選。那些經過歷史考驗保存下來的文獻,必定有它的道理和價值。學術固然有愉悅自身的功用,但這樣的“為己之學”只是學術的一部分,“為人之學”才是學術的根本立足點。
最後一點,做學問不要趕風。你只要做好你這塊領域就行了,不要什麼熱潮都去趕。作為學者,要經常保持一個“冷”字,求學時,要坐得起冷板凳,幹事業時,要經得起冷遇,觀察事務,則要保持冷眼。這裡的“冷”指的就是沉著、平靜、淡然。
近年,來新夏用電腦寫稿。“我對新鮮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試試,玩一把。”但他對電腦自有看法:“我認為電腦是個手段,不是學問。現在,年輕人把這點忘了,以為有電腦可以不讀書,不對的。因為電腦上的文章是別人給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後截取得對不對。現在年輕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論文,從電腦上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塊就成了文章,當然跟我們體制有關係,要求學生多少論文,量化。可以用電腦做科研,可以當檢索工具來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後,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來的經典著作。因為電腦上影印的文章差錯率還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電腦,電腦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學問的資源。”
如今,來新夏笑稱每天的生活是吃飯、睡覺兩大主題。“我能吃能睡,間或看點書,書不拘主流與非主流,不拘好壞。但我也不是空坐著消耗時光,做點事,整理舊的東西。”他家也常有年輕人來聊天。“我很喜歡跟他們交流,因為從他們那裡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鮮事物。”對恢復高考以後成長起來的中年一代學人,來新夏說:“這一代應該說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學者不多。現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顧一生經歷,來新夏看得頗淡:“很多人勸我寫回憶錄,我不贊成寫回憶錄。一個人寫回憶錄,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寫出來,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別像我們高齡,90歲的人,總有難過的事,等於在自己傷口上撒鹽,何必呢?”
時代周報:你研究的學術領域頗廣,到南開大學任教后,從哪裡起步?
來新夏:我到南開大學開始教近代史,從北洋軍閥開始著手。因為我在解放以後調到近代史所,我是從近代史所到了南開。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軍閥,因為我給范文瀾先生當研究生,他當時就從整理北洋檔案開始。後來我搞起古典目錄學這些東西,也是歪打正著。那時候把我控制起來,認為近代史政治性強,不讓我教近代史,後來我開課就開目錄學,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錄學為何物,以為是圖書館的編目,也就讓我開,所以成了我的學術領域。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學得不錯,我的老師余嘉錫先生親自教目錄學,他說:你可以對這個東西做點長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華書局出版過《古典目錄學》的入門讀物。
時代周報:現在學界有一種粗淺的看法,好像是北洋軍閥混戰時期亂得不得了,但當時的學術文化還是蠻有生機的?
來新夏:這個文化生機,有限制,但是沒有像後來這麼嚴。對報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時候的官員文化水平沒有那麼高,只要稍微調一下筆頭也就過得去了,二則無官不貪,稍微走動走動,搞點小動作什麼事也就解決了。北洋軍閥這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是我罪狀之一,為什麼放著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壞人的歷史,是你的陰暗心理作怪。我認為歷史總是兩面的,歷史不是單一的“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我說:沒有壞還顯不出好來。北洋軍閥的情況很混亂,各種派系交錯,我覺得把這些東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後來寫了北洋軍閥史。我研究北洋軍閥也致力50年之久,開頭寫了一本《北洋軍閥史略》,後來又改成《北洋軍閥史稿》,最後寫了一部《北洋軍閥史》,100多萬字,自個覺得算把這個事給結束了。
時代周報: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
來新夏:開頭我教近代史,總想有些新的東西給學生,讀書都要寫筆記的,所以我每看一書就寫一篇讀後的內容大要。開頭也沒有太注意,後來慢慢就稿子堆得越來越多,就覺得這些東西自己看過了,將來別人是不是還去看這個書,有沒有人這麼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繼續把這些做下去。我讀過這個年譜,都是親自檢驗的資料,一方面給後人學習,作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積累。這個稿子也遭受厄運,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燒。後來我又把它補齊了。所以,燒東西不怕,不把人殺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腦子,有腦子就可以恢復。
時代周報: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稿子也丟了,後來靠記憶又重新寫了出來。
來新夏:重新寫書這事在知識分子裡面不少。除了把這個人消滅,不消滅他人,還有腦子,還有記憶,還可以恢復。當然恢復期間是含淚的,是痛苦的。
一、學術著作《清人筆記敘錄》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
《古典目錄學》
《林則徐年譜新編》
《北洋軍閥史》
《結網錄》
《中國近代史述叢》
《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
《中國地方志》等。
二、古籍整理
《史記選注》
《閱世編》
《清嘉錄》等。
來新夏《出櫪集》
三、隨筆集
《冷眼熱心》
《路與書》
《依然集》
《楓林唱晚》
《邃谷談往》
《一葦爭流》
《出櫪集》
《學不厭集》
《且去填詞》
《來新夏書話》
《不輟集》(商務印書館,2012年4月)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獲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獲日本文部省國際交流基金獎和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獎榮譽獎。
《北洋軍閥史》獲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特評選授予來新夏先生2002年度“傑出貢獻獎”。
來新夏:誓不掛筆苦讀人(陳鑫)
不久前,來新夏先生迎來90壽辰。家鄉浙江蕭山、工作單位南開大學及在讀書界的朋友們,分別為他舉行了隆重的祝壽活動和各具特色的學術交流。來先生不反對熱鬧的慶祝場面,但拒絕了各種稱頌“封號”。他說,“讀書人”三個字才是對自己的最高評價,並表示作為讀書人的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掛筆”。
縱橫三學 自成一家
從幼年開始,來新夏就在祖父來裕恂的悉心指導下開始了讀書生涯。考入輔仁大學后,他受到陳垣、余嘉錫、張星烺、啟功等大學者的指點。其後,又在華北大學讀范文瀾教授的研究生。1951年,他奉調至南開大學任教,讀書寫作成為了畢生的事業。
在治學上,來新夏涉獵頗廣,人稱“縱橫三學,自成一家”。所謂三學,指的是歷史學、方誌學與圖書文獻學。這當中每一個領域都足以讓人望洋興嘆,但來新夏卻能遊刃有餘,並常常取得開創性成果。1957年《北洋軍閥史略》、1981年《古典目錄學淺說》、1983年《方誌學概論》、1987年《天津近代史》、1991年《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詞典》……這些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相關領域中的第一部書,開一時風氣,為學術的發展辟出一片新天地。
更為難得的是,來新夏的每一項研究都具有相當強的持續性,絕非淺嘗輒止。從《林則徐年譜》到《林則徐年譜新編》,再到《林則徐年譜長編》;從《北洋軍閥史略》到《北洋軍閥史稿》,再到《北洋軍閥史》;從《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到《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增訂本)》……從著作最初問世到擴充增訂,往往前後延續數十年。對學術,來先生從不滿足現狀,總是不斷進行探索,以求盡善盡美。其中有幾部書稿遭遇“文革”劫難,不得不從頭再來。2011年出版的《書目答問匯補》,凝結了來新夏近70年的心血,可謂彙集畢生功力。他對學術的認真、堅韌令人欽佩。
改革開放以來,來新夏還積極參與推動我國圖書館學、方誌學的研究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為學科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將學術服務於社會。
寫作隨筆 回報民眾
上世紀90年代,來新夏離休。雖然學術研究並沒有停止,但他可以從繁忙的事務性工作中脫身,“撥去萬累”更無拘束地讀書、寫作了。也就在此時,他“衰年變法”,又開闢了自己新的創作領域——隨筆。
他說:“當時的動機是讀了一輩子書,有許多信息應當還給民眾。過去寫的那些所謂學術性文章,只能給狹小圈子裡的人閱讀,充其量千八百人,對於作為知識來源的民眾,毫無回饋,內心有愧,而且年齡日增,也到該回報的時候了。”
對於一個已經取得很大成就的學者來說,古稀之年超越自我,開始一種新的嘗試,需要很大的勇氣。來新夏不顧朋友“不要不務正業”的勸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隨筆形式,把知識化艱深為平易,還給民眾。各大報紙的副刊、筆談中常常能看到來新夏的名字,一本本隨筆選結集出版,從1997年的《冷眼熱心》開始,《依然集》、《楓林唱晚》、《一葦爭流》、《邃谷談往》、《且去填詞》、《出櫪集》、《80后》、《交融集》……每年來新夏都有新書出版。今年,他又出版了最新“專輯”《不輟集》。據不完全統計,“來氏隨筆”已近800篇。
來新夏的隨筆內容豐富,既有上下千年的歷史評說,也有回憶親身經歷的煙雨平生,既談論掌故,又針砭時事,多年來連續入選中國年度最佳隨筆。“不務正業”的來新夏晚年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隨筆大家。
筆耕不輟 樂在其中
今日學界文壇中,耄耋之年依然高產的,雖非絕無僅有,但也屈指可數。啟功先生曾在贈來新夏的詩中寫到“難得人生老更忙”,稱讚他的筆耕不輟。
不過也有人勸來新夏何必這樣辛苦,不如找點樂子,安享晚年。其實,讀書與寫作早已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最大的樂趣。徜徉書海中,他得以施展才智、實現價值,得以神交古人、參悟人生,得以紓解苦悶、慰藉傷痛。有人說,來新夏的作品富有心靈史的意味,越了解他的經歷,才越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說起來,來新夏走過的道路並不平坦。青年時性格狷介、鋒芒過露的他,被老師贈號“弢庵”,勉其韜晦。然而由於才華橫溢、成績突出兼之“本性難移”,各種政治運動中,來新夏往往首當其衝,事業上也受到壓抑與貶斥。直至風浪過後,才在花甲之年逐漸迎來輝煌。起起伏伏、風風雨雨、天磨人忌,也許是一代學人的共同際遇。但無論如何,來先生總能在讀書、寫作中找到自我,立定腳跟。
“江山依然風月,人生依然故我。”在來新夏的文章里,我們看不到遭受衝擊后的畏首畏尾,看不到舔舐傷痕時的怨天尤人,也看不到志得意滿中的張狂自大,一切在他的筆下化作冷靜沉思。他記述往事釋然幽默,評論世情平實理性。他把各種條條框框看得很輕,但絕不故作驚人之語。學養與閱歷為他帶來了一種讀書人特有的智慧和通達。
“行百里者半九十”,來新夏常常以此自勉。他說,90歲只是人生路走到一半,後面還要加倍努力。“誓不掛筆”的他要將一個讀書人的使命履行到底。
在告別人世之前,91歲的歷史學家來新夏對護士提了一個請求:把我的眼鏡拿來,我要看東西;把我的假牙拿來,我要說話。
這也許是來新夏陷入昏迷前為人所知的最終遺言。他因肺部感染入院,直至一個月後心臟功能衰竭。上呼吸機前,他還給護士們“上課”,還想讀書。
2014年3月31日15時10分,春天還沒走完,來新夏走了。此前一天,還有學生撰文回憶,南開大學新年晚會有則燈謎,謎面是“落花流水春去也”,謎底就是大名鼎鼎的來新夏教授。
在歷史學、方誌學、圖書文獻學等多個學科都作出開創性貢獻的來新夏,素以“縱橫三學,自成一家”聞名。但他自謙只是“一個讀書人”。
他如約完成了讀書人的誓言——兩年前,南開大學為他慶祝九十大壽,他自稱“90后”,當眾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歲是新的開始,請朋友們監督,“有生之年,誓不掛筆”。
去世前幾日,來新夏主編的新書《目錄學讀本》付梓,他沒能看到。近千萬字的《來新夏文集》再過幾天就要交到出版社,他還沒校完。他新近在一家廣播電台開設的文化講座也還沒製作完成。
一切都已來不及了。
妻子焦靜宜湊在耳邊,試圖將他3月23日發表的最後一篇隨筆念給他聽。文中,來新夏形容自己“一直停不下來”。他總結,最後三年左右寫了三十來篇文章,還做過多次講演,感到“心無愧怍”。
文章題為“難得人生老更忙”。這是他在輔仁大學的師友啟功的贈言。來新夏八十大壽時,年過九旬的啟功已不能寫毛筆字,就以硬筆寫來祝壽詩。
他多年的助手和朋友、南開大學圖書館原副館長李廣生說,來先生何止“著作等身”,他個人撰寫的著作摞在一起,高過了天花板。
為來新夏整理文集的南開教授徐建華指出,來先生的許多成果都具開拓意義,多部專著是本領域或新中國成立后本學科第一部作品。
來新夏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1957年的《北洋軍閥史略》,這是新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北洋軍閥興亡史的專著,“文革”中成為他的麻煩之一。有人批評他“研究壞人的歷史”,“陰暗心理作怪”。
焦靜宜說,來先生曾經屬於“內控”人員,沒被定性為右派,但也排除在“群眾隊伍”之外,限制外出,不許上課。這客觀上催生了一位目錄學家——後來他開設目錄學課程獲得允許,因為這門學科“離政治遠”。
有人形容,來新夏屬於“百科全書”式人物,且口才極好,講課“記下來就是一篇完整文章”。
晚年的來新夏不再開啟新的課題,而是把舊稿補充完整。他的代表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是用毛筆寫成初稿12冊,但經過“文革”,僅余兩冊。另一書稿《書目答問匯補》也被沒收,多年後被學生從廢紙堆中發現。
與很多同代知識分子一樣,來新夏的學問經過了被焚燒、然後憑藉腦力重新恢復的過程。
焦靜宜說,來先生極少談起“文革”,也不寫回憶錄。他覺得,自己所經歷的,並非個人獨有的遭遇。
學生們公認,來新夏後來經歷了“衰年變法”式的轉型:這位歷史學家以高齡成為出版近20種隨筆集的高產作家。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寧宗一形容這位摯友,“在史學與文學兩條路并行的軌跡上”,進行了“從容的對接”。
而他自比“瘦駱駝的水囊”,只是讓人乾渴時“姑且喝上一口”。
他身上亦有瘦駱駝的毅力。在來新夏80歲之前,李廣生未見他“打過一個哈欠”。他每次拜訪,往往見到滿頭白髮的來先生坐在電腦前。
來新夏74歲那年開始學習電腦,起因是他預料到,上了年紀用筆寫字手會發抖,鍵盤則不會。
在“環顧左右,平生知己半為鬼”的年紀,來新夏身邊不乏忘年交。李廣生說,來先生善於交友,有人素不相識,只是慕名而來。只要門鈴一響,開門的往往是來先生。不少地方請他為方誌寫序,他甚至為5個拆遷的村莊題寫過《遷墳記》碑文,而在此之前,他親自考察新墓園“均能符合民意”才算答應。
在焦靜宜看來,與青年人的交往,是來新夏保持活力的原因。“他把跟這些年輕人的交往看做跟社會聯繫的渠道。”
浙江省紹興縣齊賢鎮群賢村的農民孫偉良,以換煤氣罐為生,雖只有初中學歷,但研究地方志頗有成就。十多年前,他寫信請教來新夏,二人自此建立了長期的讀書人的聯繫。2007年,這位農民在村裡建起一座“來新夏民眾讀書室”。
那個村莊來新夏去過三次。他寄去的包裹,孫偉良連原包裝都不捨得丟掉。
孫偉良曾向來先生提出,希望在南開讀個函授文憑。來新夏告訴他,如今教授多如牛毛,擁有文憑未必就算博學多才。紹興的文史富礦足夠挖掘,只要用心研究,比擁有文憑強得多。
跟來新夏的弟子們一樣,孫偉良稱他為“來先生”。
來新夏喜歡“先生”這個稱呼。他近年發現,“先生”似已成“古董”,研究生稱老師為“BOSS(老闆)”,師生關係變成雇傭的金錢關係。他“寧背守舊落後的惡名”,也拒絕“BOSS”之稱。
他還忌諱被人尊稱“大師”。在遺囑中,他要求後事從簡,不舉辦任何告別儀式。
很多人沒有來得及與來先生道別。這個讀書人的名為“邃谷”的書房設為了靈堂,沒有哀傷的樂曲,只有書的山谷。
親友們原本期待為他慶祝百歲壽辰,來新夏也很有信心會活到那一天。他今年出版的最後一本隨筆集《旅津八十年》,附有他密密麻麻、令不少晚輩汗顏的工作日程。
今年春節,來新夏整理舊物,發現尚有一筆“欠債”。2005年,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學術研究主任居蜜委託他整理些鴉片戰爭史料《潰癰流毒》,他因事務繁忙遺忘。他自覺愧對舊友,決定“盡生前二三年之力”完成。
這筆債永遠還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