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墓的闖入者
威廉·福克納所著偵探小說
《墳墓的闖入者》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在1948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是一部“偵探小說”。《墳墓的闖入者》是福克納創作生涯後期的一部著名的作品。這部小說深刻體現了福克納的種族觀念,作家表現了青少年在南方種族社會艱難的種族觀抉擇,批判了維護種族秩序的南方社會,從而借通俗偵探題材及偵探小說的範式實現了對現實的干預。而這部小說的作者福克納,受文化、社會、歷史等因素的影響,種族觀念先入為主,雖然他的種族觀日益成熟,但仍有本身的局限性。同時也可以看出種族主義無處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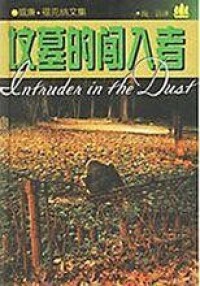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墳墓的闖入者》
這部小說風格的變化似乎是由於福克納採用了老百姓喜歡的通俗文學中偵探小說的格局。他在好萊塢的時候,大導演霍克斯問他為什麼不寫本偵探小說,他回答說,他想寫一個“關在牢房裡努力想破自己的案子的黑人。”他在前面提到的給奧伯的信里更明確地說,“這是一個關於謀殺的偵探疑案小說。”他後來跟弗吉尼亞大學的學生座談時又說,這本書“開始時是一個念頭當時不斷出現大量的偵探小說,我的孩子們老買,老拿回家來,到處都是,不管我走到哪裡都會碰上。我有了個想法,關於一個被關在監獄里將要被絞死的人,他只能自己做自己的偵探,他找不到任何人來幫他的忙。後來我又想到那人是個黑人。於是……就想到了路喀斯·布香。那本書就這麼寫出來了。……但我一想到布香,他就左右了這個故事,這故事就跟我開始時的想法跟我開始要寫的偵探小說大不一樣了。”
對福克納來說,1948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他在1942年發表《去吧,摩西》以後沉寂了6年。他一心一意想要寫的巨著《寓言》一直難產。另一方面,他經濟拮据,不得不從1942年開始就到他並不喜歡的好萊塢去打工掙錢。他與華納電影公司簽訂的合同條件很苛刻,對他很不利,因而心情很不舒暢。1946年1月他給他的代理人奧伯寫信說,“在法國,我是一場文學運動之父。在歐洲,我被認為是最優秀的美國作家,也是所有作家中最出色的一個。在美國,我靠在一次偵探小說比賽中獲得了二等獎才勉強得到一個蹩腳文人寫電影腳本的工資。”幸好,奧伯在1946年三月幫他爭取到電影公司的批准,使他可以在家寫小說。但他並沒有馬上寫《墳墓的闖人者》,而是繼續創作他的《寓言》,幫助馬爾科姆·考利編他的《福克納袖珍文集》,又寫了一本關於賽馬的書。只是因為《寓言》寫得很不順利,而出版商對賽馬的故事又不感興趣,他才在1948年一月開始寫《墳墓的闖入者》,連寫帶修改一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9月就由蘭登書屋出版,銷路比以往任何一本書都要好。評論家反映也不錯。同時,由於《福克納袖珍文集》的出版,讀者與評論界又開始對他發生興趣。《生活》、《紐約客》等雜誌紛紛要求為他寫人物專訪。於是,米高梅電影公司出高價買下《墳墓的闖人者》的拍攝權,並在他的家鄉拍攝。這使得他不僅有了經濟收益,還在一貫冷落他的家鄉名聲大振。用評論家米爾蓋特的話來說,“《墳墓的闖入者》完成了《福克納袖珍文集》所開始的重新確立福克納作為文學名家的工作。”同年,福克納得到美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他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第二年他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從此時來運轉。可以說,《墳墓的闖人者》是在他事業生涯的關鍵時刻使他交上好運的一部作品。
然而,這並不是福克納心血來潮寫的小說。早在1940年他就告訴他的代理人海亞斯,他想寫“一本偵探小說,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解決疑案的人是個黑人。他本人為這個謀殺案被關在監獄里,將要被處以私刑,為了自衛破了這個謀殺案”。他本人一度還很看重《墳墓的闖人者》。1948年他在寫書的過程中曾給奧伯寫信描述了小說的主要內容:“一個黑人,他被指控為殺人犯,被關在監獄里等著白人把他拉出去,澆上汽油,放火縱燒,……他自己做偵探,解決了這個罪案”。他還說,小說寫的“更多的是黑人與白人的關係,前提尤其是,或者更可以說是,南方的白人,比北方,比政府,比任何人都多欠黑人一份債,都必須對黑人承擔一份責任”。40年代末,他曾對一個朋友說,這是他寫過的最好的一本書。1955年,他訪問日本時,有位聽眾問他日本讀者應該首先看他的哪一本小說,他回答說,“我建議——題目叫《墳墓的闖人者》。我建議這本書,因為它談的問題很重要,不光在我們國家很重要,而且,我認為,對所有的人都很重要。”
跟福克納的其他作品相比,《墳墓的闖入者》有一個明顯的不同:福克納不再用暗示或隱喻的方式談社會問題,而是很明確、很直截了當地揭露了當時美國社會的一大矛盾種族關係問題;他的文體也一反以往隱晦曲折的做法,沒有多層次多視角,一切事件都是通過少年契克的角度來表現的;儘管其中有回憶,但時序並不混亂得讓人摸不著頭腦。雖然他還保留他的複雜的長句,但整個故事頭緒清楚,觀點明確,比較明白易懂。他在上面那封給奧伯的信里強調,“這是一個故事,沒有人在裡面嘮嘮叨叨地講道。”
同樣採用偵探小說格局的《押沙龍,押沙龍!》卻錯綜複雜,頭緒繁多,讓人無所適從。從兩本書的對比可以證明,福克納在《墳墓的闖人者》里確實是有意要使敘述清楚,讓故事線索明確易懂。兩本書的不同風格反映了作者思想的變化。
福克納是在《寓言》難產的情況下才寫的《墳墓的闖入者》。那本他一心一意地要寫成“可能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小說”,是一本主題先行的作品,背景是他並不熟悉的歐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福克納想用一個寓言故事來表現他對戰爭和西方文明的譴責,強調世界已經墮落到如果耶穌再次降臨仍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步。他違反了他一向習慣也主張的寫自己熟悉的人與事的做法,給自己帶來了不少困難。在寫不下去的情況下他重新回到他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寫起他一向想要寫的黑人自己做偵探的故事。他寫得很順利。然而,《寓言》那種主題先行的做法肯定影響了《墳墓的闖人者》的構思和寫作過程,使之成為一個思想性很強也很明確的故事。
《墳墓的闖人者》涉及的是福克納一向關注的黑人與白人關係的種族問題。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人道主義作家,他在《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和《乾燥的九月》等小說和故事中一再譴責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和對黑人的歧視與迫害。他在晚年非常關心社會問題,想在“國家的聲音中表達一點自己的意見”,也確實對種族問題多次公開表態。《墳墓的闖入者》是40年代末黑人民權運動日趨激烈的時候寫的,福克納惜題發揮,直言不諱地表明了自己對種族問題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墳墓的闖人者》是《去吧,摩西》的續集,因為主要人物路喀斯。布香就是《去吧,摩西》中的一個主人公。另一個主要人物加文。斯蒂文斯律師也在《去吧,摩西》中出現。兩部小說都涉及黑人與白人的關係。《墳墓的闖人者》沿襲的也是《去吧,摩西》敘事風格,突出的是思想內容而不著眼於霧裡看花的手法技巧。
法國學者路易斯·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看成一種附著在一定機制上的,對個體具有構造作用的生產活動”,認為意識形態通過一種“質詢”的方式,藉助宗教、教育、法律、家庭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個體轉變為意識形態的主體。在《墳墓的闖入者》中,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也通過這種“質詢”的方式成功地掌控了其中的四類白人,即“第四巡邏區人”、傑弗生鎮民、查爾斯·馬利遜(即契克)、律師加文·史蒂文斯,使他們成為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主體,分別接受了“黑色的野獸”、“黑鬼”及“桑博”這三種針對黑人種族的刻板印象。在《墳墓的闖入者》中,“第四巡邏區人”是極端種族主義分子,受到激進種族主義的影響,認為黑人是“黑色的野獸”。傑弗生鎮民與第四巡邏區人有所不同,他們對鎮里的黑人並無刻骨仇恨,但是,他們也受到種族主義的麻痹,對黑人持有“黑鬼”這種刻板印象。在鎮民們眼裡,一方面,“黑鬼”是奴性十足的;另一方面,“黑鬼”骨子裡還是狡邪凶蠻的。少年契克是在傑弗生鎮成長起來的人,對社區有強烈認同感,起初也認為黑人就是“黑鬼”。律師加文·史蒂文斯則與第四巡邏區人和傑弗生鎮民的種族觀念保持著距離,他具有較強的正義感,對黑人一貫同情,代表著傑弗生鎮中少數對黑白種族關係持開明態度的人。然而,就是加文也未能擺脫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質詢”,他對黑人種族抱有“桑博”(Sambo)這種負面刻板印象。美國南方文化專家喬爾·威廉姆森對“桑博”刻板印象有過研究,指出“桑博”是“有著孩子氣的小青年”,他“既討人喜歡,又讓人生畏”。在加文律師眼裡,黑人就是這種既有孩子般可愛,又有潛在威脅性的“桑博”。總之,上述四類白人都回應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質詢”,因而對黑人種族都抱有負面的刻板印象。
馬丁·N.麥格認為:“建立在普遍信念基礎上的各種族特徵,通過選擇性感知得以強化。也就是說,人們通常會注意那些能夠鞏固他們心中刻板印象的案例,而忽略或忽視那些不符合刻板印象的案例。”《墳墓的闖入者》中的白人接受種族刻板印象后,也是通過反覆的“選擇性感知”來強化這種錯誤認知,這在小說中突出體現在傑弗生鎮民身上。傑弗生鎮的一家食雜店老闆利勒先生就是鎮民中以“選擇性感知”強化種族刻板印象的典型。利勒先生和其他鎮民一樣,對黑人種族持有“黑鬼”刻板印象。當某些黑人在他店裡順手牽羊,拿走點不值錢的小東西時,利勒先生雖懶得去計較,但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事實上,某些黑人愛貪小便宜的根源在於種族壓迫導致的赤貧生活,絕非與生俱來的。利勒先生可沒有這種覺悟,在他看來,所有黑人都是“黑鬼”,天生就是小偷的德性。這樣,通過有選擇性地反覆感知黑人的一些不端行為,“黑鬼”刻板印象就在利勒先生的心目中不斷強化乃至紮下了根。傑弗生鎮民也和他們的代表利勒一樣,通過“選擇性感知”的過程,不斷強化頭腦中的“黑鬼”刻板印象,以致成為一個被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麻痹的整體。在小說中,在等待看路喀斯受私刑的場面時,形形色色的傑弗生鎮民彼此間的差別彷彿消失了,他們“不是許多面孔而是一張臉,不是一群甚至也不是五花八門的一片而是一張大寫的臉:即非貪婪也非心滿意足而只是活動著,沒有感情,沒有思想甚至沒有激情”。這就表明,通過反覆的選擇性感知,傑弗生鎮民對黑人種族的刻板印象積重難返,成為路易斯·阿爾都賽所稱的“自發或自然地生活在意識形態中”的主體。
阿爾都塞強調意識形態對主體的控制作用,而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認為阿爾都塞的觀點過於悲觀,忽視了主體質疑和反抗意識形態的可能性。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形態主體如果“必須有足夠的敏銳接受統治者的教導,那麼他們也就應有足夠的意識能夠質疑這些教導”。
在《墳墓的闖入者》中,契克就是這種具有質疑精神的意識形態主體。年方十六的少年契克是在傑弗生鎮成長起來的人,起初接受了“黑鬼”刻板印象。他的心理在一段時期和鎮民們一致,想報復路喀斯,讓他做一回壞“黑鬼”。路案發生之初,他也認為路喀斯是兇手。但是契克的年齡尚小,並且敏感聰穎,可塑性強,特別是他有過和路喀斯的特殊交往經歷,這些因素使他“代表了約克納帕塔法縣白人的救贖潛能”,能不斷地質疑“黑鬼”刻板印象。契克與路喀斯的特殊經歷源於契克十二歲那年的冬天。當時他掉進一條結冰的小溪中,被路過的路喀斯發現后救起,這個時刻他觀察到的路喀斯和傑弗生鎮民的描述迥異,路喀斯“不是傲慢,甚至也不是鄙視:只是自有主見和從容自若”。隨後在路喀斯的家中,路喀斯讓他裹著百納被,坐在溫暖的爐火邊暖身子,還把自己的飯菜端給他吃,這又讓契克覺得路喀斯和自己的外公一樣親切。對現實的敏感就使得契克開始質疑傑弗生鎮強加給他的“黑鬼”刻板印象。然而,這種刻板印象的力量仍然強大。契克於是拿出七角錢硬幣作為報酬,扔到地上,想讓路喀斯低頭彎腰撿起來,藉此確立他和路喀斯的尊卑關係,讓路喀斯做回“黑鬼”。不料,路喀斯命令和契克同來的兩個黑人小孩把錢撿了起來還給契克。這樣,“黑鬼”刻板印象再次受到契克的質疑。數年後,當路喀斯妻子莫莉去世的時候,契克親眼目睹了路喀斯黯然神傷的樣子,再次真切感受到路喀斯也有著深厚的情感,和白人沒有任何區別。這樣,通過多次與路喀斯的互動,一個充滿自尊、感情深厚的真實的路喀斯形象也逐漸進入契克的內心,與傑弗生鎮灌輸給他的“黑鬼”刻板印象形成了對話。
通過逐步質疑“黑鬼”刻板印象,契克在思想覺悟上已比加文進了一步,因而他在路案上比加文走得更遠,行動更得力。當契克聽到路喀斯解釋說克勞福德不是自己的槍打死的時,他就認識到案件可能另有隱情,不能因為路喀斯的膚色而讓他成為“替罪羊”。契克因此接受路喀斯的委託,決定冒著風險去第四巡邏區掘墳驗傷。由於時間緊迫,他毅然躍身馬上,和另兩人一起連夜歷經三小時的奔波趕到十英裡外的第四巡邏區,結果他們在文森·高里的墓中發現的是另一個白人的屍體,這就為路案的公正解決提供了關鍵的證據。契克的重要發現也促使加文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他採取果斷行動,連夜把路喀斯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解除了令人窒息的私刑風險並最終使案件得以公正處理。在當時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南方社會,福克納的種族觀念較為開明,他指出:“諸如盎格魯·撒克遜遺產和非洲遺產的東西並不存在,只存在人類的遺產。任何種族都不會欠缺什麼素質,只是可能還沒有體現出來罷了”。由此可見,福克納明確反對種族刻板印象,這點在《墳墓的闖入者》中也得到了有力證明。《墳墓的闖入者》深刻揭示出種族刻板印象的危害性,表明這種刻板印象是黑人遭受屈辱和不公的元兇,體現出作者對當時美國南方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的深切憂慮。《墳墓的闖入者》同時表明,南方白人只有反對種族刻板印象,以公正的眼光看待黑人,才有希望解決南方內部棘手的種族痼疾。
在《墳墓的闖入者》中,福克納在描繪契克經過的豬圈時,這樣寫道,“到了傍晚時分整個大地將會掛滿它們那鬼怪似的完整的油脂色的空蕩蕩的屍體。”這一偶然出現的事物卻也逃離不開製造恐怖氣氛的作用。而契克一直耿耿於懷的那七角錢硬幣就像月亮一樣永遠在那,“那每天夜裡懸掛在憤怒與無奈的黑暗深淵裡的死去的可怕的沒有熱氣的圓片依然存在。”本來被人們認為是美景的月圓之夜卻在哥特小說中成就了恐怖的氣氛。除此之外,“被影子蠶食得支離破碎的黑暗”、“跟尼尼微一樣的死亡時代的星期天的夜晚”、“亞麻布西服的白色幽光”、“靜悄悄的翻著眼白的眼睛”等等諸如此類的描述在這部小說中不勝枚舉。這些帶有恐怖色彩的描述成功地營造了恐怖的氣氛,也為小說奠定了哥特基調。
既然已經有了恐怖的氣氛,為了更加吸引讀者能追隨作者的筆觸去尋找真相,福克納也設置了許多神秘的懸念。比如,在廣場上衝出來的小汽車裡面發出尖利的年輕人的聲音,那麼車裡坐的人是誰?在契克三人去挖墳墓的路上,“黑糊糊的一團,一個在行動的東西,在道路暗淡的灰土映照下的比黑影還要黑的影子順著山坡走了下去。”這個黑糊糊的影子到底是什麼或是誰?在契克一行人第二天白天又去墳墓的時候,發現墳墓上的花並沒有被放好,他記得他們把土重新填進墳墓后就又把花放了回去,那又是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回來又碰過墳墓呢?再後來,他們發現棺材是空的,那兇手原來用來替代文森·高里的蒙哥馬里的屍體去了哪裡?而真正的文森·高里的屍體又被挪去了哪裡?迭起的懸念被抽絲剝繭,最終真相得以呈現。可見,懸念作為又一重要的哥特因素對故事情節的推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並且也是成功吸引讀者的一種手段。
比喻是最常見的一種能被賦予哥特涵義的修辭。哥特小說的作者往往本體比喻成恐怖的、陰森的、哀凄的事物,進而突出哥特小說的特點。例如,福克納把監獄里一動不動平靜地並排躺在床上的五個黑人比作是“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在描述牢房的門時,福克納用了這樣的比喻,“那笨重的鐵棒插進鐵槽時像那塗了防腐潤滑劑的世界末日那樣發出一種表示無可辯駁的終結定局的沉重而油滑的響聲。”很明顯,“屍體”,“世界末日”這類的詞語都映射出哥特涵義。
重複也是福克納在它的哥特小說中慣用的一種手法。雖然在英文作品中,重複很多時候可算是行文一大忌,但就哥特小說而言,重複這種修辭往往充滿了哥特意味,對小說里人物的行為和心理都能夠進行很好地詮釋,尤其是在表現人物糾結的心理時更能夠相得益彰。小說中,契克一再強調,哈伯瑟姆小姐“太老了”,“不應該幹這種事”,但儘管一味地重複強調,結果卻是大相徑庭,那就是哈伯瑟姆小姐最終幹了挖墓這件事。契克的這種糾結心理與哈伯瑟姆小姐的實際行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福克納對於契克在挖墓回到家后的睡意也進行了多次的重複描述。契克一次又一次地從“黑暗的睡意”和“長長的深深的睡眠的深淵”中掙扎出來。這些重複清晰地展露出了契克當時的精神狀態與心理狀態。雖然一直很睏倦,但他還是掙扎著要做完他想做的事。
擬人在哥特小說中運用的頻率也頗高。在《墳墓的闖入者》中,福克納也用了許多帶有哥特涵義的擬人修辭,像“入口處白色的欄桿張大著嘴向著他們賓士而來。”除了擬人,福克納還經常用一種諷刺的語氣來敘述,如“那建築在虛無之基礎上猶如深淵上用厚紙板建造的房子的耀人眼目的名聲偉業還有那過去是我們次要的民族工業而今成了我們國家業餘消遣的鬧鬧嚷嚷的亂七八糟的政治活動。”另外,福克納在小說中還用到了排比。排比不同於重複,它是在形式上的一種強調,例如“他們自己的悲哀他們自己的恥辱他們自己的懲罰。”所有這些帶有哥特涵義的修辭手法無一例外地為這部小說增加了它的哥特色彩。
敘事手法
在敘事時間上,福克納大量使用停頓的敘事手段拉長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之間的距離,造成了緩慢的敘事節奏,延宕的敘事進程迫使讀者注意到福克納似乎不是把路喀斯的案件放在敘事的核心。偵探小說文化定位的主要目標是滿足讀者追求奇險的欣賞情趣,表達為大眾所接受的文化觀念,因此,它把一個撲朔迷離的事件按照最吸引讀者的順序排列,設置一個個跌宕起伏的懸念,注重突出經典敘事的三個基本要素,即順序、懸念和結局。情節里的一切細節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即使這意義暫時不為讀者所知,但也必須是服務於揭示謎底的。但福克納並沒有在表現罪案的曲折、罪犯的兇殘狡猾以及偵探的睿智勇敢方面下功夫。小說共十一章,開篇以一句話交待了路喀斯因殺人被抓,插敘了契克與路喀斯認識的經過,第三、四章寫契克和舅舅去探監、契克受路喀斯所託去挖墳,由此發現了墳墓里死者屍體被掉包的關鍵線索。此後作家就閑置了案件的發展進程,到第十章才由加文草草揭開了案件的原委。這其中大量的篇幅與偵破本身無關,如大段不加標點的契克的內心獨白,他和母親、舅舅在一些瑣事上的對話,以及他和舅舅關於黑人問題的討論,“當一個並不佔素材時間的成分(因而是一個對象,而不是過程)被詳細描寫時,我們就可以區分出停頓。在這種情況下素材時間小於故事時間。”停緩的敘事節奏雖然會對讀者造成懸念,但過於迂徐的敘事極大地淡化了偵探小說對邏輯結構嚴密和敘事節奏緊湊的要求,導致偵探小說揭示犯罪、懲惡揚善主題的重要性滯后,而對於偵探小說來說,“犯罪之謎必須被揭開,這個揭開犯罪的過程就是偵探小說的唯一重要的主題。”這也是偵探小說的趣味所在,以及與其它小說範式根本區別之處。
小說引入敘事張力表現了在南方種族主義環境下契克改變種族觀念的艱難。修辭性敘事理論認為敘事“張力或衝突關係涉及價值、信仰或知識之嚴重斷裂的關係”,契克對黑人的接受和加文對黑人的拒絕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形成了文本的敘事張力,這種張力又因人物態度本身的複雜性而不表現為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
《墳墓的闖入者》是美國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納的重要作品之一,首次出版於1948年,這是一部獲得不少國外評論家充分肯定的小說。如邁克爾·米爾蓋特認為該小說“完成了《福克納袖珍文集》所開始的重新確立福克納作為文學名家的工作”。約翰·伯特甚至把《墳墓的闖入者》看成是可以與福克納的經典作品《押沙龍,押沙龍!》和《八月之光》相提並論的小說。

墳墓的闖入者
大學肄業一年,1925年後專門從事創作。他被西方文學界視作“現代的經典作家”。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說和70多篇短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被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這部世系主要寫該縣及傑弗遜鎮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家庭幾代人的故事。時間從獨立戰爭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場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現,實為一部多卷體的美國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寫傑弗遜鎮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沒落及成員的精神狀態和生活遭遇的《喧嘩與騷動》(又譯《聲音與瘋狂》1929);寫安斯·本德侖偕兒子運送妻子靈柩回傑弗遜安葬途中經歷種種磨難的《我彌留之際》(1930);寫孤兒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種族偏見的播弄、虐待下悲慘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寫一個有罪孽的莊園主塞德潘及其子女和莊園的毀滅性結局的《押沙龍,押沙龍!》(1936);寫新興資產階級弗萊姆·斯諾普斯的冷酷無情及其必然結局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鎮》1957,《大宅》1959)等。福克納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