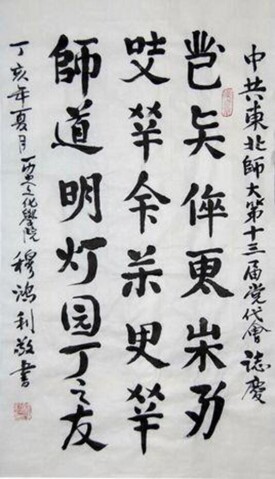女真語
語種
女真語是古代女真人在10世紀到15世紀初使用的語言,女真語屬於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古代語言,是滿語的祖語。女真語的三大主要來源,即源於突厥語、契丹語、源於古代蒙古語和中古蒙古語。女真原沒有文字,只是借用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和葉魯制女真字,天輔三年(1119)八月,字書成。女真文自西元1119年頒布使用至1234年金朝覆亡后停止使用,歷時120多年。
據稱,全世界屬於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語言計有14種,分佈在中國的有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和歷史上的女真語;分佈在俄羅斯境內的埃文語、涅吉達爾語、烏利奇語、奧羅克語、烏德語、奧羅奇語等;其中鄂溫克語也分佈在蒙古國的一些地區。
女真語和滿語之間存在較多相同語音特點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語音特點。在滿語的語音特點當中,有的反映比女真語更早期的現象,有的反映女真語以後出現的現象,有的則反映滿語與女真語平行的發展關係,因此,不能簡單地將滿語視為從女真語繼承而來,女真語和滿語是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
宋元女真語語音的輔音系統,概有雙唇音p、b、m,舌尖擦音s,舌尖塞音t、d,鼻音n,舌尖邊音l,顫音r,舌叶音č、j、š,舌根音k、g、x,后鼻音ŋ,小舌音q、γ,半母音y、w;母音系統有單母音a、o、u、i、e;二合母音ai、ei、au、ui、ia、ie、io、oi。女真語名詞、形容詞詞綴-n。女真語最初使用女真文,後來這種文字漸漸消亡。元朝之後,女真語中融入了大量蒙古語外來詞。女真語名詞有10個格,有音節式、輔音式兩種複數後綴。
輔音
| 唇音 | 齒齦音 | 舌叶音 | 舌根音 | 小舌音 | ||
| 鼻音 | m /m/ | n /n/ | ŋ /ŋ/ | |||
| 塞音及塞擦音 | 送氣清音 | p /pʰ/ | t /tʰ/ | č /ʧʰ/ | k /kʰ/ | q /qʰ/ |
| 不送氣清音 | b /p/ | d/t/ | j /ʧ/ | g/k/ | γ /q/ | |
| 擦音 | s /s/ | š /ʃ/ | h /x/ | |||
| 顫音 | r /r/ | |||||
| 近音 | w /w/ | l /l/ | y /j/ |
母音
| 母音 | 音位 |
| 單母音 | a、o、u、i、e |
| 二合母音 | ai、ei、au、ui、ia、ie、io、oi |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為女真語、滿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途徑。歷史比較語言學興起於19世紀,在西方已有120多年的歷史了,其奠基人主要是丹麥的拉斯克、德國的葆朴和格里木(亦譯格林)以及俄國的沃斯托克夫等,他們都各自獨立地促進了本國語言科學的誕生,並在歐洲各國掀起了對各種語言展開歷史比較研究的熱潮,範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深化。學者們按照語言的歷史來源和親屬關係,對各種語言作出了譜系分類,分出語系、語族和語支。19世紀70年代是歷史語言比較研究的轉折點,其主要標幟則是語音的歷史演變規律得到了進一步闡明,並確立了類推作用的原則。瑞士的著名學者索緒爾及其學生法國的梅耶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集大成者。梅耶的《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是一部總結性的著作。
在中國真正進行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則起步較晚,而且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歷史比較研究多是在描寫研究基礎上起步的。解放前乃至解放初期研究成果不多。八十年代后,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取得顯著的進展。阿爾泰語系語言歷史比較研究,雖然各有關語族語言間的比較研究及內部系屬分類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不過在整個語系的研究上尚沒有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阿爾泰語系的古代各族,有的建立過政權,創製過本民族文字,留下了許多民族語文資料。例如:滿族的先民女真族曾先後創製女真大、小字,記錄女真語。在有金一代直至後期,延用了四百多年。明末建州女真首領努兒哈赤又命學士額爾德尼、噶蓋依仿蒙古文字母創製無圈點老滿文,後來天聰汗皇太極時,又由達海加上圈點改為新滿文,保留了大量的滿語辭彙,滿文在整個清朝一直延用了三百多年。
早在清代,對女真語文和滿語文就進行了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滿語文處在“國語國書”的地位,不僅編印了大批的辭書,還有一些傳統的語文研究論著問世。然而,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覆滅,使用滿語的人口驟然減少,滿語文研究也隨之走向低谷。雖然自19世紀末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有一些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曾發表了一些關於女真語言文字和滿語文方面的論著。但是,歷史比較語言研究方面則尚屬鳳毛麟角。建國前曾著文介紹阿爾泰語系語言的是董同和先生,他在《阿爾泰系語言概說》中,分為敘說、突厥語、蒙古語、通古斯語等四個部分介紹了阿爾泰語系各族及其語言分佈、語言特點及其分類等。新中國成立初期,有關阿爾泰民族語言比較的論文則很少見。60年代著名女真語言文字學專家金光平發表《從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一文,是一篇從文字學角度對契丹文與女真文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文章,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並不斷地取得共識。1964年金光平、金啟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對女真文字的創製、構造、讀音和語法等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是我國學者系統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第一部專著,可以代表中國學術界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最新水平。書中第一章對女真語在通古斯語族中的地位;女真語與滿語的關係;女真語與蒙古語、漢語、契丹語的關係,均做了概略的論述,應該說,這是中國對阿爾泰語系各族語言進行比較研究的開山之作。為女真語與滿語、女真語與蒙古等其他族語言進行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開創了範例。80年代以來,阿爾泰語系比較語言學的著述逐漸增多,出現了可喜的局面。著名的契丹語文、蒙古語文專家清格爾泰先生與劉照雄先生合寫的《阿爾泰語文學概述》一文中對國外阿爾泰語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了扼要介紹。我的滿文老師、精通日、俄、英和蒙、滿、達斡爾語言的巴達榮嘎先生的《達斡爾語、滿語、蒙古語的關係》一文,也是一篇比較語言研究的重要文章,著重對古蒙古語與達斡爾語的對比、滿洲語與達斡爾語的關係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考論和對比,很有見地和說服力。著名的契丹語言、蒙古語文學者陳乃雄教授的《阿爾泰語系概要》講座稿,除一般性介紹外,也提出了自己對阿爾泰系屬問題的獨到見解。他認為,阿爾泰諸語言的關係既不能簡單地用“譜系樹”、“波浪論”、“錯合論”、“蔓延論”、“借貸論”加以概括,也不是“三個同心圓”機械擴展的結果,而是一些具有共同起源的語言,一方面受到祖語內在引力的制約,一方面又受到外來引力(包括地理、歷史等變遷)的影響,在人類發展的漫長歲月中,不斷經歷著自覺與不自覺的語言向心和離心作用,在緩慢持續地偏離同一個圓心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語言的形成和演化往往是在一系列語言“滾雪球式”的運動中實現的。在“雪球”滾動過程中,不光融掉一些表面的東西,同時又吸收或生成了更多的東西,使“雪球”越滾越大。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有些使用阿爾泰語言的集團完全脫離了母體,於是它們的語言發生了更為複雜的變化;有的可能保存下來,但在迥然不同的環境里接受著迥然不同的影響;有的可能消亡,轉用了別的民族語言;有的則可能在別的語言社會的影響下和本身獨特的經歷中逐漸形成了新的語言。此外還有幾篇文章也各有特色,如:林蓮雲的《我國阿爾泰語言的諧音詞》;胡增益的《阿爾泰語言中的經濟原則》;吳維的《融合與分化──中國阿爾泰語系源流概說》;金炳喆的《蒙古、突厥、通古斯三個語族共同詞的探討──〈五體清文鑒〉研究》等,有的是屬於某一專門問題的研究,有的是就某些方面的語言比較研究,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看法,尚待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總之,近十多年來,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探索,多數學者不斷取得一些共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不論歷史上是否存在過阿爾泰語共同體(或稱母語),也不管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語族彼此間是否有原始的親緣關係,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原始突厥語、原始蒙古語、原始通古斯語都還不是這些語言的起始,它們有可能從一種或一些更古老的語言或方言中繼承了某些語法形式和辭彙。所以對這些語言進行比較研究仍然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課題。
目前,中國阿爾泰語系歷史語言比較研究,一方面需要加強跨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另方面,也要注意本語族內部各語支,甚至是同一語支的民族縱向或橫向比較研究,女真語與滿語的歷史比較研究當然是屬於後者。
女真語是滿語的祖語,滿語是女真語的繼承和發展。它們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
女真語的複數後綴根據其語音形式可以分作兩類,一類屬於音節式的-sa/-s/-si;一類屬於輔音式的-l/-r。與女真語-sa/-s同屬一類的有滿語-sa/-s/-so,-so不見於現存女真大字石刻中。滿語的-si與女真語的-si相對應,滿語的-ta/-t,在現存女真大字石刻中尚未出現。女真語的名詞共有10個格,其中主格除在從句以外,其他場合皆以零形式出現,這一點與滿語相同。主格以外的九個格皆用專門的表音字予以表示,多數格後綴具有和諧變體。清朝建立后,女真語徹底被滿語替代。
從聯繫方面說,歷史上這兩種語言,本來就生長在一棵語言譜系樹上,所謂“肅慎女真連滿洲”,是說不同歷史時期對這個古老民族的不同稱謂,只是到了后金天聰汗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才將女真族稱改為滿洲族。皇太極明令宣布:“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珠申。夫珠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從此,便正式將顯赫數世的女真族改稱為滿洲。翌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改元崇德,改國號為清,其本人也改汗稱帝,是為清太宗。顯然,改族稱和改國號都是人為造成的。它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又是當時政治的需要。具體說來,一方面統一后的女真各部需要一個新的族名,因為原來的諸申(即肅慎、朱里先)的舊稱,已隨著女真族內部階級分化而下降為賤民之稱,不再能概括新的擴大了的民族共同體的全稱。雖然,在各部落中自有專名,但卻沒有一個可以施及全民族的通稱;另方面,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如果繼續沿用從前與宋朝對峙的大金舊稱,則易為明末漢人所厭聞,造成不必要的民族隔閡,何況此時多民族的后金政權,已不是金國號所能概括的,因而要改國號為清。
從區別上說,首先是反映民族語言的文字元號有別。原有女真文字是在完顏阿骨打反遼后建立大金政權之初,金太祖宗顏阿骨打於天輔二年(1118年)命開國功臣、女真族著名學者完顏希尹與耶魯(葉魯)創本族字,備制度。希尹等“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語,制女真字。天輔三年(1119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這就是女真大字。後來,金熙宗完顏亶又對女真字進行了改進,創製女真小字,於天眷元年(1138年)頒布,並於皇統五年(1145年)“初用御制小字”。與希尹等人所制女真大字俱行用,並在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廣泛地應用起來。女真文作為官方通用文字,用以撰寫國書諭令和文誥,設立女真字學校以教授女真文,培養女真字人材;立女真進士科,以升擢選官;譯述漢文經典,傳播先進的漢文化;女真字還應用於碑刻、符牌、銅印、畫押、墨書題記或官印銅鏡之邊款等。總之,女真字頒行后,由於金統治者的提倡,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領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由於女真貴族壟斷文化,廣大的女真下層人民並不可能人人都學會了女真字,加上女真字本身固有的局限和弱點,普及起來十分困難。因此,當女真族與漢文化接觸后,學習漢語和漢字的人逐漸增多。金亡以後,在元朝統治期間,女真族同蒙古族接觸頻繁,又有不少人學會蒙古語和蒙古文。而真正會女真文的人便逐漸減少,到了明中期以後,女真文逐漸變成了一種死文字,其使用範圍也僅限於女真族的發源地。到明末,很多女真人已經不認識女真字,甚或不使用女真字了。因而,當建州女真興起統一女真各部后,其首領努兒哈赤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命學士額爾德尼、噶蓋等以蒙古字母拼寫國語,創製無圈點滿文新字,也稱老滿文,頒行國中。從此,女真文便徹底廢止不用了,滿文終於取代了女真文。這種老滿文字母比較簡單,比女真文字易學,便於普及。但是也有弱點,它不能很好地記錄音素較多的女真語音,致使部分字母“上下字無別。故‘它、搭’、‘特、德’、‘扎、蜇’、‘呀、耶’等字不分,均如一體。若平常語言,按其音韻,尚可易於通曉。至如人名地名,則恐有錯誤”。加上老滿文屬初創,字母尚不統一,變異較多,不大規範,故天聰汗皇太極在天聰六年(1632年)正月,又命文士達海“可以原字頭照舊書寫,惟增加圈點,俾後學者視之,或有裨益於萬一。如有錯訛,仍能用舊字頭證明”。於是,皇太極頒布了新滿文十二字頭,規範了字母形式,較準確地區別了原來不能區分開的語音,由於增加了圈點,使一些語音得以區別開來。還增加了一套拼寫外來語(主要是拼寫漢語借詞)的字母。用這套字母寫出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或稱有圈點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