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兒文學
京味兒文學
北京是“京味兒文學”的發生地,因此對於“北京”的文化闡釋,是“京味兒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會上我們聽到的是作家學者們對“北京”樸素而直觀的理解。

京味兒文學
趙大年說,京味兒小說從未形成流派,也從未有過自覺的創作群體,只是有些作家在寫了帶有這種特徵的可觀的作品之後,被評論家和讀者歸為“京味兒作家”而已。星竹認為,作家不會在寫作之前做“我要寫京味兒了”這一設定,文學的精神在於自由,一旦在寫作之前就將主題、風格固定下來,文學就已經死亡。陸濤說,雖然他從不認為自己在“京味兒作家”之列,但是從《屈體翻騰三周半》開始到小說卻都被稱為“京味兒小說”。他認為文學一旦強調“味兒”,視野就會不再寬廣,作家就很難從整個人類的角度去把握自己的素材和問題。
京味兒文學是一個用得爛熟的詞,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來一直糾纏不清,此次會上也見仁見智。趙大年說,當年“京味兒文學叢書”編委會給“京味兒文學”歸納了四個特點:1、作品中必須運用北京語言,這是第一要素;2、運用北京語言描寫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環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發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質。因此,京味兒文學是地域性的文學。《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兒文學的顛峰,體現出北京語言崇高的美學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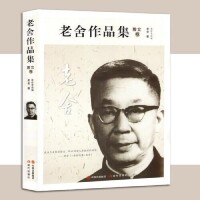
老舍作品集
對於“京味兒文學”這種地域化和傳統化的理解,一些青年作家有不同的看法。陸濤認為,京味兒文學應當是一種人文精神。任何文學都是從共性中尋找個性,從個性中尋找味道,而這個“味道”就是地域文化和人格力量在文學作品中散發出來的氣息。但是隨著北京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日益現代化的發展,原來正統意義上的“京味兒”事物必將慢慢衰落,新的“大都市文化”卻將應運而生,因此“京味兒文學”就應容納更豐富的意蘊,尋找和建立大都市的文學精神。畢淑敏也認為京味兒文學概念應該更開放和大氣,讓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流向在此有更多的表現,輸入更新鮮的血液。
對於將“京味兒文學”概念的外延擴大化的主張,青年作家田柯持不同意見。他指出,京味兒文學、京派文學和北京地區文學不是一個概念,京味兒文學是北京文學的一個分支和一種傳統,它在挖掘、展示皇城根兒子民的生活和心態上有獨特價值和發展餘地,但是對於表現“新人類”、大學生和中關村人等普泛化和現代化的人物與生活,卻有著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他認為承認這種限度,保持其個性,才能使京味兒文學的形象更為鮮明。
大量使用北京方言
京味文學的共同點在語言方面表現為純樸、純凈、平實、口語化、大眾化。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因為方言本身就給人一種親切的的感覺,京味小說也正因為這種共同的平易性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
濃郁的北京傳統味
中國向來是個禮儀之邦,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處處影響著每一位中國人,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歷代王朝的故都,所以從古老的風俗禮儀到傳統的倫理道德都積澱於北京人的心中。他們重禮節,講文化,北京人多禮,如:《二馬》中老馬賠本送禮。但傳統文化中落後的一些思想對北京市民的影響也很明顯,他們有些保守不願接受新新事物,封建的宗教倫理道德很濃厚。表現出了濃郁的傳統北京的文化、禮儀、習俗等等,對封建文化的繼承和對腐朽落後思想的揭發並與時代共進的現代主義精神。
有北京鄉土味
可以說,京味文學是鄉土文學的一種。鄉土味主要是指北京區別於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衚衕、四合院、大雜院、白塔寺的廟會,廠甸的春節,乃至小酒鋪閑聊,馬路邊唱戲等等無不浸透著一種獨特的鄉土氣息。京味小說展現給人們的獨具個性的人文、社會、歷史處處與舊北京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老作家林斤瀾先生說,當年劉紹棠曾提倡“鄉土文學”,“京味兒文學”無疑是鄉土文學之一種;但是孫犁先生多年前在為劉紹棠書作序時就指出過:“鄉土文學”講不通。多數文學作品都會涉及一些鄉土風情,但並不能據此認為它們就是“鄉土文學”。比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里,雖然人物和環境是紹興的,但是魯迅的小說觀卻並非是鄉土的。他塑造人物,是要“雜取種種人,雜取種種話”,最終做到解剖“國民性”。沈從文的小說雖然有濃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學追求並非是“湘西鄉土文學”,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學境界,湘西的風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學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學不應把“鄉土化”作為追求本身,而應當追求超越鄉土,到達純精神的高度。否則,如果各大報刊紛紛提倡寫吃寫喝的“京味兒文學”,文學的層次必將會越來越低,越來越“物質化”,也越來越重複。
林斤瀾先生指出,居住過北京的許多現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讚美過北京的韻味———藍天、黃葉、叫賣聲,從容、悠閑的情調,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里卻沒有。對他的故鄉和旅居過的地方,魯迅先生從未表達過沉醉之情,卻總是帶著嘲諷的目光去打量。任何一個對自己的時代和社會保持著批判立場的作家都是如此——他們無暇迷醉,他們要催促人類改進與前行。在這種價值理念的參照下,“鄉土文學”、“京味兒文學”的提法就值得商榷,至少不能把它作為一種文學追求來提倡。
京味小說派”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流派並非偶然。從歷史、文化、語言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具備了產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北京人,現代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中秋》、《峨眉》、《蒲柳人家》、《春草》、《地火》等等。
王朔,我國著名作家,編劇。從1978年開始,后發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中、長篇小說。後來進入影視業,電視連續劇《渴望》和《編輯部的故事》都獲成功。
藉助首都的影響力
“京味”的獨特性和影響力,如前所述,像北京這樣具有鮮明的民族標記、豐富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地域風貌的城市,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見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著獨樹一幟的光彩。再藉助於它作為首都的權威性,影響所及豈止於中國,實可謂名揚中外。
“北京話”的魅力
現今推廣全國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話”作為基礎的,二者大同小異,這使北京話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國的便利。北京話雖有一些方言土語,但大多是普通話稍加變化,如兒化韻、雙聲詞並不影響讀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說中使用幾個生僻的俚詞(如“敢情”、“找樂子”之類),往往正是體現京味色彩最濃之處,最富有鄉土氣息,作者必然會加以解釋說明,並巧妙運用,一般只會增添語言的魅力,“燒”出京味的香氣。所以,從總體來看,運用純熟“北京話”寫出的作品,在全國推廣是沒有多大障礙的。
作家隊伍
當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寫“京味”,但至少他們寫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說:“京味小說派”的後備隊伍是陣容強大的,這是“京味小說”的出現和繁榮的前提。
在中國文學史上,“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兩個術語往往被評論家們混用,但兩者實際上是不完全等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京派”,其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以及批評家的主要代表馮至、廢名、陳夢家、方瑋德、林徽因、孫大雨、孫毓棠、林庚、曹葆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梁遇春、方令孺、朱自清、吳伯簫、蕭乾、沈從文、凌叔華、蘆焚、汪曾祺、丁西林、楊絳、李健吾、朱光潛、梁宗岱、李長之等,乃至被許多學者推為“京派”首要代表的周作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外鄉人”!
只要仔細分析“京派”的作品,我們很容易看出,“京派”注重的是人與整個社會、與大自然的整體關係,而不太注重北京地域的色彩與味道。這與作為京味文學代表的老舍完全不同。在老舍的小說裡面有的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地道北京生活的描畫、純正方言口語的傳承、鮮活民俗風情的展現。
1980年代曾經出版過一套“京味兒文學叢書”,叢書編委會認為“京味兒文學”主要具有這樣四個特點:
第一,作品中必須運用北京方言;
第二,運用北京方言描寫北京的人和事;
第三,作品中環境和民俗是北京的;
第四,發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質。
按照這個分類,我們可以看出京味文學與京派文學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
能否和現代性兼容
趙大年認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新時期以來西方現代文化思想和文學藝術的湧入,中國新文學一直沒有停止吸收現代文明的營養,“京味兒文學”也不例外,《紅樓夢》之後有老舍,老舍之後還有林斤瀾、鄧友梅、劉心武,直到現在的王朔,事實證明“京味兒文學”一直是在承續銜接之中。說起老舍,趙大年指出,老舍先生是用英文寫過小說的作家,但是他的漢語白話小說卻一點看不出洋味兒來,這叫“大洋若土”;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說正相反,由於中西文化的修養都不深厚,寫得很有些“大土若洋”。
京味兒文化屬於歷史文化範疇,和某些特定的社會形態相對應。隨著北京作為政治、文化、社會交往的大都會,原有痕迹會越來越淡。因此對“京味兒文化”應重新定義,定位在“都市文化”上。一味追求京味兒文化,勢必導致向傳統的回歸與追尋,結果是製造一批比真實的“京味兒”更“京味兒”的偽民俗、偽文化;這種製造越酷似,文學作品的現實衝擊力越弱,偽文化的色彩越強。文學應表達的是對社會、人生的真實看法,不應沉迷在對舊有京味兒文化的留戀、把玩、回歸與塑造上。
京味兒文學不能作為終極性的文學追求,文學應當超越狹隘的“鄉土文學”觀念,這些已是共識。但是展望人類文明的未來——全球化,現代化,“經濟一體化”,隨著人類物質匱乏的苦難日漸消失(或可能消失),現代化差距的日漸縮小,人類處境的差異也將被漸漸抹平。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不久前對中國讀者說:現在和未來的日本年輕作家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的生活里已經沒有了鄉村,於是他們所有作家只能去寫都市;就這一點來說,中國的作家和讀者卻是幸運的,因為你們有無窮無盡的豐富新鮮的寫作資源。但是,從當下中國青年作家的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都市化”傾向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作品內部的生活表象的差異性已經很難辨認。如果說文學對於人類精神問題的探索可以千差萬別,但是行諸筆端的形象卻總是似曾相識,這前景總是不那麼令人振奮的。對於單一和乏味的恐懼使人相信:在文化基因庫(焦國標語)之豐富性的意義上,“京味兒文學”的存在的確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但是似乎也僅僅是這種價值了。
隋麗君女士指出,京味兒文學的主要問題是語言太“水”,而且一提“京味兒”就以為是“油北京”、“痞北京”;另外就是對人類的精神深處挖掘不夠。文學應當站在人類精神的高處,寫人類共通性的東西,這也就是為什麼王朔小說“不能過長江”、在台灣也賣不出去的原因。止於“味兒”、止於語言層面的共識和默契,其作品的命運就是如此。
當然,所謂“流派,流動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變,更不可能永世長存,文學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個形成、發展直至消亡的過程,有的壽命還較短。有人擔心,隨著時代的發展,“舊京味”將越來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說”前途堪憂。其實,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會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於時代新潮中,那麼,“京味小說”作為一種歷史,仍將有它存在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