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純
李思純
李思純,字哲生(1893——1960),四川成都人,著名歷史學家,元史學家。1893年生於雲南昆明。1919年赴法國巴黎大學勤工儉學,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歸國后,任東南大學、四川大學等學校教授。1953年為四川文史研究館館員。與陳寅恪、吳宓等史學大師多有交往。著有《李思純文集》(四卷,巴蜀書社,2009年5月版)。

曾外公李思純留學德國時所照
李思純在文、史、哲、政、法、新聞、外交翻譯領域都有較大建樹,尤其以史學、詩詞見長;從空間上橫跨亞、歐,從時間上縱歷清末、民國、新中國成立后十年三個時期。
1919年夏,由李劼人介紹,李思純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分會。 1919年11月,李思純與李劼人、何魯之、胡助等四位成都分會會員邀約聯袂同往法國勤工儉 學。李思純在法國生活很艱苦,經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冬天巴黎很冷,他住的寓所無錢生火爐,冷極了竟撿報紙燒火取暖。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學生的巴黎通訊處,倒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如蔡和森、蔡暢、王若飛、徐悲鴻、李璜等。
李思純先後在里昂、蒙彼利埃、巴黎求學。作為“少中”巴黎分會的活躍分子,李思純在《少年中國》上發表了《國語問題的我見》、《信仰與宗教》、《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等論著。他還醉心於翻譯法國詩歌,如將著名的《惡之華》譯成中國古體詩形式,這讓他成為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譯介法國詩歌最多最有影響的譯者之一,他的譯詩觀與譯詩方法在當時具有創新色彩。1925年歸國后,他曾將其法蘭西譯詩結成《仙河集》,附印於《學衡》第47期。
學貫中西兼文史
李思純就讀巴黎大學文科三年,從師瑟諾博司教授研究近代史及歷史方法。后在自《序》里說:“朝夕挾書冊以從,聆聽講課,後來轉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樓,日長多暇,乃譯成《史學原論》一書。”這書是由瑟氏與朗格諾瓦(法蘭西國家藏書樓主任)二人合著的。他們都是法蘭西負有盛名的史學家。李思純對他們推崇備至。1923年,回國的郵輪上,李思純譯完了《史學原論》的附錄,首次將書介紹至國內。
李思純留歐四年余,節食省用,還買了幾百本外文書籍,如霍渥兒特《蒙古史》及有關中亞、印度等史書。這為他作為史學大家墊下了深厚功底。在學術專著方面,1926年中華書局刊印了李思純的《元史學》,得到王國維、柳詒徵、陳垣等專家的寓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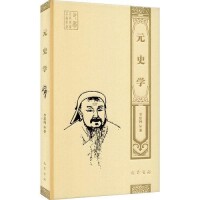
192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李思純著《元史學》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了李思純《江村十論》一書,是學術論文十篇集成,《說歹》、《說站》、《唱喏考》、《說外族王號異譯》諸篇與元史有關;《說斗將與兵器》、《說殉葬》、《說民族髮式》、《唐代婦女習尚考》、《譯經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則有關通史、民俗、社會習尚,以及少數民族之研究。1963年,中華《文史》第三輯刊出了李思純《學海片鱗錄》一卷,為讀書札記,內容精粹。
李思純與友人交往,多以詩詞唱賀。其最早之詩作見於1912年。后李留學法德,亦隨時作詩記物,並投《學衡》發表,吳宓與其成為至交與此關係極大。吳對李詩十分欣賞,並說:“今年六月,君歸國,困居上海,寄來《東歸旅程雜詩》三十七首(刊載《學衡》二十一期)。宓七月初,即去函定交,邀君來南京住宓家……並介見梅光迪君等,梅君引為同志、同道,即薦於學校,聘哲生為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法文》及《法國文學》教授。”
作為兼新舊文人品性的李思純,可謂萬里遊歷萬里歌。他曾為蜀中學界耆老趙熙的弟子,故詞作亦臻上乘。
啼笑皆非涉政界

李思純
李思純赴南京出席國大,似乎看透了當時的家國大勢,其心思並不全在於會事,而是作為個人遊歷交友與謀業掙錢的機會。在預備會期間,他即應浙江大學校長邀請赴杭州講學遊歷三日。李思純在會外的另一重要內容即會晤文人與朋友。此間訪晤人物眾多,皆為社會名流,如于右任、曾琦、李璜、梅貽琦、陳寅恪、傅斯年、李濟、竺可楨、章士釗、顧頡剛等政界與學界人士數十人,舊友新知不亦樂乎。
在《金陵日記》中,李思純記載相聚唱曲較多。國大結束后在杭州講學期間,2月16日訪譚其驤。兩點鐘“偕季龍伉儷及佘坤珊夫人赴湖濱西湖飯店,參與崑曲會,為杭州戰後第一次聚集,定名曰‘西湖曲社’”。多人唱曲十餘種,八點方散。可見當時學人雅興之高,且透露出抗戰後,在短暫的太平光陰里,江南民國學人時常有此等雅集相聚。
人間舊好勝新知
1943年夏,一代史學宗師陳寅恪,同時為成都燕京大學與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聘,經歷亂世流離之顛簸,來到了風光旖旎的成都華西壩,一時心境大好,賦詩道:“淺草方地廣陌通,小渠高柳思無窮。”不僅如此,還他鄉遇知己,李思純便是其一。他在抄贈李思純的一首詩中即有“人間舊好勝新知”的表達。李思純與陳寅恪的交情是從1922年開始的。李思純因法國物價太高而轉到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因無官費、少家濟,加之四川時局惡化,戰禍又起,一年後,他寫了《柏林留別陳寅恪》詩后就回國了。陳先生長他三歲,爾後竟成知交,因為兩人有著共同人生經歷、有著共同治學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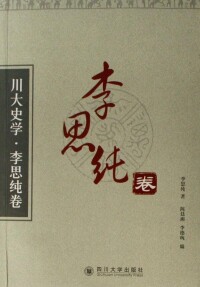
《川大史學·李思純卷》
陳寅恪此時正患眼疾,聚談之間仍有如此興緻,且談論中,陳寅恪囑咐李思純要“常往談,以解寂寥”。后李思純返川,陳氏又托李氏過渝時往其家代轉問候。李思純到陳家后,陳寅恪的胞弟陳登恪一家還留李思純午餐。陳登恪也曾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留學德國時,李思純就常與陳寅恪、陳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頭的咖啡館里清談。
1944年秋,李思純另一位至交吳宓也來到了華西壩。吳宓為古典文學兼外國文學名教授。兩人在學術上早有交往。1923年10月李思純在《學衡》第22期發表了《論文化》一文,而成為介紹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的最早的學界人士之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艱難歲月里,吳宓在接到李思純家庭生計告急書信時,還從自己本就微薄的薪酬中拿出部分接濟老朋友。這樣的情誼成為肝膽相照與相濡以沫的文人交往典範。
李祖楨 懷念我的父親李思純
作者:李祖楨
來源:《文史雜誌》,1989年4期,3-5
李思純(哲生),是我父親,1893年出生於雲南昆明。1919年秋,我父親和李劼人、何魯之三個青年同舟去了法國自費勤工儉學。當時在上海會聚的青年去歐洲的人還多,他們是受“五四”運動的影響而出國的。
我還記得大概是在1919年夏秋,由李劼人作介,在成都部分青年人自願參加,組成了“少年中國學會”分會,照了一張像。我認得出的有:李劼人、李思純、胡少寰、何魯之、李幼椿、孫少荊、周曉和(周太玄的哥哥)、穆濟波等。還有後來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虞),他是贊助者,不是少年但卻有一顆少年的心。這一學會早在“五四”前一年就在北京籌備。發起人有李大釗、王光祈(字潤愚,四川溫江人)、周太玄、曾琦等,後來毛潤之也參加了。王光祈最活躍,富有改造社會的空想,有理論和實踐精神,所以推舉為籌備主任,後為執行部主任。可以說“少年中國學會”是以王氏為主演,是在“五四”時期各種社會思潮下湧現出來的。
父親與王氏是老朋友,他們同是《川報》《群報》的記者(王氏當時為駐京記者),他們在上海半淞園,黃家闋多次晤談交遊,後來又在柏林交遊一年有餘(王氏先讀柏林大學後去波恩)。二人在“學會”中都屬無派見的,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又不是國家主義派,只是王氏的理想言談,有安那其主義傾向(即無政府主義)。時人多以王氏留德十八年不歸為憾,父親則反思其事,認為在國外研究的成績比在國內大,王氏是自有其理論識見,不願政治千預。王氏和我父親,都是愛國知識分子,據說王氏在德國曾作過不少反日侵華宣傳,成效很大。王氏是土秀才加洋博士模式的人物,所以與我父親很契合。父親與王氏的性格、識見,甚至走的路子(中間路線),都是相近似的。
父親是流著眼淚出國的,因為沒得錢!他的父親只是個滇省邊縣候補縣令,辛亥任命后候補資格自然取消了。他的祖父倒是一個知州,在中法越南戰爭中,光(州)宣(州)之戰得勝立功授官,可是為官不到兩年即丁憂返川,不復出仕,不久病卒。父親雖是宦門之子,清末便有“海棠花下破衫來”的詩句,在上海飽嘗酸風冷雨,出國時,幸得張君勱的資助,又謀得《時事新報》駐歐通迅記者。 004
父親就讀巴黎大學文科凡三年,從聽瑟諾博司教授講述近代史及歷史方法。自《序》其情況說:“朝夕挾書冊以從,聆聽講課,後來轉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樓,日長多暇,乃譯成《史學原論》一書。”這一書是由瑟氏與朗格諾瓦(法蘭西國家藏書樓主任),二人合著的。他們都是法蘭西負有盛名的史學家。父親在巴黎生活很艱苦,冬天巴黎很冷,他住寓所無錢生火爐,冷極了竟撿報紙燒火取暖。他經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可是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學生的巴黎通信處,火熱的心也燃燒著他從今天要跨到明天。他在巴黎忙著學習法文,拉丁文,和寫通訊稿,也結識了不少新朋友。我特別要提的是蔡和森、蔡暢、王若飛、徐悲鴻、李璜等,他說他與王若飛更合得來。
父親終於到柏林去吃廉價麵包了,因他祖母死了家計接濟不上。他知道學業未成又勢在必返,因而發奮譯書(即《史學原論》)。父親說:此書為“討論抽象史法而體大思精之作。”又說:“談歷史方法之書尚未有逾此者。”(此書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以後又再版,列入歷史叢書。又收入《萬有文庫》列入史學類書。)此書有幾個觀點值得一提:1、無史料即無史學,即使是第一手史料,著作者也有傾向性。因此要運用校讎、考證、鑒定等方法。不應輕信和盲從,早出的書未必較晚出的立言可信。2、一切校讎考證之目的,皆不是史學家的真正目的。史學家的真正目的在於探求“史原”。即著作的原始,透視歷史的真象,裸露歷史的本來面目,自然可以察古、鑒今、而知來。譯文還強調說:“歷史使吾人狎熟於一切社會形式之變動,而將吾人畏懼變更之傳染病,療治痊癒。”可見此書論史是有求變革,向前看的目光的。它已進入了新史學的範疇。3、本書鑒定史料,提出了“離立其所含之各個記載”,是現代“篩選法”的影子。此書還講了“天人趨合”與我國先哲講的“天人合一”不是一回事。但與現代史學新思潮的“宇宙法”學說,更有明顯的暗合。以上幾點,說明此書與現代史學新思潮的脈搏是緊密相連的。
父親住在柏林(1923年),自然要學德文,同時,漸漸他愛上了音樂(他早年就是個崑曲愛好者),喜歡聽交響樂,歌劇。也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我特別要提出的是,他和朱德、康克清同在舞場相識。自然那時他還不知道有這麼榮幸;他會和一位未來的紅軍元帥共舞呢。他在柏林結識陳寅恪是一生的幸事。陳先生長他三歲,爾後竟成知交。50年代還寫信,寄詩,互通肺腑之言。父親留歐四年余,節食省用,還買了幾百本外文書籍,如霍渥兒特《蒙古史》及有關中亞,印度等史書,父親無官費、少家濟,加之四川時局惡化,戰禍又起,1923年他寫了《柏林留別陳寅格》詩后就回國了。在船上翻譯完《史學原論》的附錄。
歸國後任南京東南大學外文系教授,此後以詩文投稿《學衡》。他的譯稿《法蘭西詩歌集》(即《仙河集》)也刊出部分,《戈歌魚麻古讀考》一文亦刊出,他不是《學衡》派,但是個贊助者,是憑著自己愛好古典文學和珍惜傳統文化而寫稿的。他思想上不沾復古主義,作品上很少封建塵埃。
在南京一年,主要在寫《元史學》一書,他治元史的方向在證誤、校補,即引域外新的資料,以補訂國內大師著作之不足,可見父親早年頗有雄心大志成一“蒙古通史”。用綜合體著述。如他說的:“一干眾枝,一枝眾葉,分為五部(包括蒙古餘緒帖木兒汗國),合為一史。”不過雄心雖有,大志難成,他的雄心到暮年時唯有“書空坐一室,咄咄向天涯”之嘆。
不過父親的《元史學》(1926年由中華書局印行),得到王國維、柳詒徵、陳垣、朱希祖幾位專家學者的寓目,釐正偽誤(見《元史學自序》)。他確也補了幾篇元史學文字,如《補馬可波羅傳略》,《補元代基督教傳布史略》等。
父親還有《學海片鱗錄》一卷,中華《文史》1963年第三輯刊出。是讀書札記,很精粹。足見讀書淵博,功力深厚,識見不凡,發人之所未發。又《江村十論》一書,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是學術論文十篇集成,如《說歹》、《說站》、《唱喏考》、《說外族王號異譯》諸篇與元史有關。此外有《說斗將與“兵器》、《說殉葬》、《說民族髮式》、《唐代婦女習尚考》、《譯經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則有關通史、民俗、社會習尚,以及少數民族之研究。
1924年他回成都探親,省督楊森,聘任他為“四川外國語專門學校”校長。父親說:一年來,別無他事,唯經常跑將軍衙門向楊森要錢辦學!比教書還傷腦筋!1925年李鶴林(郫縣人,留學生,共產黨人,后被開除?)來信促去武漢。他卻去了學術中心北京。
他來到清華園,訪問了老友陳寅烙、吳宓。又謁見了國學大師王靜安(國維)梁任公(啟超)。王先生親書五言秀句數首賜贈;梁先生則“竟晚作長夜之談。”父親俱有詩記其事。同年他在北大任教(預科),在輔仁大學、北師大兼課,他和章士釗、張東蓀、陳垣庵、馬敘倫諸先生都是師友之交,與賀麟、劉半農等先後認識。后又在國立編譯館任編纂,所以熟人不少。 005
回川后賦閑兩年,只在“成都高師”、“國學專門學校”(前身即尊經書院)兼課。
抗戰年興,父親任川大歷史系教授,后兼師院史地系主任。又兼授華大哲史系,迄於解放。1960年3月14日在省文史館病發(腦溢血)經醫院搶救無效逝世!年67歲。
父親手稿,曾被抄失!但佚存還多(清還)。如詩近千首,詞近百闋,自署《岫雲廬詩詞》。他是趙堯老(熙)及門弟子,故詞作亦臻上乘。此外有《成都古迹考》、《成都大慈寺考》和“龜城志”,可見他是要學常璩為地方寫史志。還有《崑曲名譜曲手鈔本》、《國史四裔地名同名異譯彙編》(殘稿),以及《康行日記》《昔游詩》等。
我認為父親治學是比較全面的,文、史、哲、政、法、新聞、外交翻譯都下了很大功夫,(自是以史學,詩詞見長)。從空間說足跨亞非歐,從時間說閱歷清末、民國、解放后十年三個時期。他有史筆,也有詩筆,有科學識見與聰明感受,好文辭而不陳腐。所以父親不是一張畫,一部小說,所能圓滿描繪的。他的心靈也是較美好的。下面錄父親詩一首以志懷念。
《戊寅(1939)重九日作》
河朔江淮兵氣荒,誰家凈土過重陽?
烽煙啼雁嘶千劫,血淚凝楓染四方。
憔悴黃花垂晚萼,艱難青鬢上繁霜。
漫天風雨人間世,不待登高已斷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