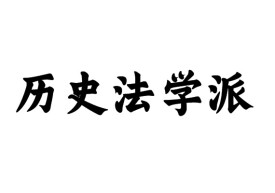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派是18世紀末期在德國興起的法學派別。因反對古典自然法學派,主張法律由歷史傳統形成而得名。代表人物有胡果(GustavHugo,1764—1844)、薩維尼等。認為法律並不是“理性”的產物,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律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自發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法律淵源首先是習慣而不是立法;等等。主要目的是維護封建習慣法,反對代表新興資產階級意志的立法。至19世紀後期,該學派漸趨衰落。
.背景1

歷史法學派
背景2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聯軍攻入巴黎,拿破崙第一次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反法同盟旋於維也納召開會議,重商建立歐洲秩序。翌年,由於英、法、俄等歐洲大國擔心德意志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后如虎在側,聚集在維也納的政治家們遂決議建立一個鬆散的“德意志邦聯”,作為德意志統一問題的暫時替代性解決方案。
背景3
拿破崙以《法國民法典》為利索而束縛各國,並將其強制施行於德意志各邦。在1814年拿破崙被推翻之後,該法典已經在多數省份施行。北萊茵各省保留實行該法,並且一直如此。在德意志其他部分,該法作為一種政治落魄的標誌,幾乎很快遭到拋棄。以何種形式取而代之的問題,隨即浮現。
背景4
在當日德國,整個思想學術領域都正在從事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不僅在法的研究中,而且在民歌、民間童話、民間話本、民間習俗以及語言、詩歌和宗教等等一切領域的研究中,民族意識均如沛然春水般涌流。
背景5
蒂博是德國哲學法學派的領袖,持守以溫和的理想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傳統自然法學說。其在拿破崙戰爭后倡議對德國進行法典化改造,反映了其理性主義的哲學訴求和經由法典化尋求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政治抱負,他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足以摹寫人類的心思,並轉而據此設計出人類行為的完美規則,為人世生活編製恰切法網,因而遭到了以薩維尼為首的歷史法學派的激烈抨擊。
背景6
德國人從來不曾屈服於語言的羈絆,而且在有關詞句的運用上,尤其是在那些具有確切含義、精審配置的語言結構的運用上,享有極其廣泛的空間。德語的能量不會為任何語言的立法所限,而且德國人依然相當嚴重地徜徉、耽溺於神秘主義。
所謂法律

歷史法學派
法律與民族
法律與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逐漸調試,契合不悖,從而賦予法律以自在自為的功用與價值,而法的功用與價值,也正在於表現和褒揚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法律因而成為民族歷史凝成的生活方式的規則形式。
法律的生命力
來自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法律之為良法,也在於此;法律的無效,失去民眾廣泛的信守,也正因失於此。“如果說有什麼應予譴責的話,當是法律與民族兩相背離。”
法律精神
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涵蘊並存在於歷史之中,其必經由歷史才能發現,也惟經由歷史才能保存和擴大。喪失了與民族的初始狀態的生動聯繫,也就喪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為寶貴的部分。
民族、性格和法律的聯繫

歷史法學派
語言
法律,一如語言,乃是一個連綿不絕的歷史發展過程本身。法律也同樣受制於此運動和發展。此種發展,如同其最為始初的情形,循隨同一內在必然性規律。簡言之,法律隨民族之成長而成長,隨民族之壯大而長大,隨民族對於其民族個性之喪失而消亡。
立法的任務
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與“共同意識”,經由立法形式善予保存與肯認。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卻決然不能創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藉由一個詳盡無疑的立法制度,即刻創造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範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
在民族生活本身尚未整合成型
關於民族現實生活的考察也未見成效之時即貿然立法,其法根基必然淺薄,等而下之者,甚至於民族生活兩相忤逆,新法頒行之日,必是對生活本身的摧殘之時。薩維尼反對制定法典,非法典本身,而是視法典若兒戲。
所謂循沿歷史
體認、發現和重述民族生活及其規則形式,目標在於追溯每一既定製度直至其源頭,從而發現其根本的原理原則,或可將那些毫無生命、僅僅屬於歷史的部分剝離開來,從而“涵詠其真正的精神,繼續其未竟的事業。”

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學生、德國著名私法學家薩維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佔有權論》 (1803)、《論立法及法學的現代使命》(1814)、《中世紀羅馬法史》(1815~1831)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1840~1849)等。繼胡果和薩維尼之後,歷史法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薩維尼的學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習慣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頓教科書》(1838 )、 《教會法入門》(1840)和《法理學教程》 (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歷史法學派的代表還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溫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派
基於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準。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

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派法本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製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
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範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併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儘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羅馬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還有溫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該學派強調當前德國法學家的任務,是對德國歷史上的羅馬法窮根究底,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其中內含的原理,區別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死亡了的。胡果和薩維尼,都試圖在研究羅馬法的基礎上構造一門概念清楚、體系完整的民法學學科,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羅馬學派開始向概念法學發展。
法的精神
19世紀中葉以後,羅馬學派又分為兩派,一派以溫德海得等人為代表,在研究《學說彙纂》的基礎上,使概念法學發展得更為充分、更加系統化,從而形成了“潘德克頓法學”(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則以耶林為首,逐步意識到概念法學的弊端,主張對法不應當僅僅作歷史的、概念的研究,還必須從法的目的、技術、文化等角度來研究。
歷史法學派中的羅馬學派轉變為“潘德克頓法學”,是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開始出現統一的趨勢,統治階級開始認識到,統一的德國對於其擠入帝國主義列強是必要的。為此,在德國出現了統一立法的趨勢。1848年以後,《德意志一般票據條例》開始在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絕大多數盟國實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絕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實行。其後制定民法典的呼聲也甚高。而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則體現了國家的意志。這無疑刺激了“潘德克頓法學”的成文法至上主義。
“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由專事研究《學說彙纂》的學者海塞(Heise)創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溫德海得。
溫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頓法學”的核心人物,也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溫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關於前提的羅馬法理論》(1850)、《條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頓教科書》。溫德海得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後者中。該書是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集大成。首先,該書在對所有“潘德克頓法學”文獻進行概括、整理和闡明內容的同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該書體系完整、理論結構嚴密,不僅在各項制度研究上運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邏輯性操作構成的系統的法學方法,而且將其推廣到了整個私法學領域;第三,傳統的“潘德克頓法學”作品,或偏向於理論或偏向於實用,而本書則第一次將理論和實用結合在一起。它是對以往“德國普通法”理論的集大成,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具有極大的權威,不僅支配了整個德國的民法學,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1900年《德國民法典》 (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說成是“小溫德海得”。)。
“潘德克頓法學”的特點,一是對概念的分析、闡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尤其是溫德海得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確立的五編製民法學體系,成為1900年《德國民法典》(包括後來的日本和舊中國等的民法典)的淵源;三是以羅馬《學說彙纂》作為其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的歷史基礎。“潘德克頓法學”,顧名思義,它是《學說彙纂》(Pandekten之音譯)的註釋學,
歷史法學派
這是近代德國民法學明顯區別於《法國民法典》的地方(後者以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為藍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脫離現實、從概念到概念、從條文到條文的傾向。
在溫德海得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至頂峰的同時,以耶林為首的“目的(利益)法學”(功利主義法學)也在羅馬學派內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羅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為權利而鬥爭》(1872)、 《法的目的》 (全2卷。1877~1884)。在這三本書中,耶林對“潘德克頓法學”只注重概念、脫離社會現實利益(權利)鬥爭、脫離社會法的目的的傾向進行了批判。在《羅馬法的精神》一書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權利概念。薩維尼將權利定義為“意思的力”,耶林主張將權利定義為“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對人的目的和動機作了研究,這種目的或動機形成兩個大的系列即個人的和社會的。個人對社會行為的利己動機有兩種:報答(Lohn)和力(Zwang);社會動機也有兩種:義務的觀念和愛的觀念。這一學說為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台創造了條件:目的是法的創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兩者不可偏廢等等。這些思想,對以後的社會學法學的勃興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歷史法學派中另一個學派日耳曼學派,其特點是埋頭於德國本民族法(日耳曼習慣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創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麥爾(K.J.A.Mittermaier,1787~1867)、阿爾普萊希(W.Albrecht,1800~1876)、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以及祁克等。該學派自1830年以後,開始與羅馬學派決裂,而1846年在呂貝克召開的“日耳曼法學家大會”則是這種決裂的公開化。
日耳曼學派堅持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該學派也贊成羅馬學派的研究方法,主張用邏輯的、概念的、體系的手段來研究歷史上的法律。但是,與羅馬學派不同,該學派主張發掘德國私法自身發展的歷史。與羅馬學派為近代民法學的體系、原則、概念和術語奠定了基礎相對,日耳曼學派的貢獻除了為近代提供社會團體主義理念之外,還表現在促進了近代商法學和有價證券法學的發達方面。而對日耳曼法學的總結、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則是祁克。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德意志團體法論》(全4卷,1868 ~1913 )和《德意志私法論》(全3 卷,1895~1917)等著作中,其內容非常廣泛,其中,關於法的本質、法和道德的關係以及社會法思想代表了他的歷史法學派的基本立場。
祁克指出:“所謂法,是指法規以及法律關係的整體,而法規則是將人的自由意欲置於外部並且以絕對的方法予以制約的規範”。他認為,“法以國民對法的確信為根據,法規是規定(國民)各自意志的界限,要求正確生活秩序的理性的表白”。“法是表示出來的社會的確信,所以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準則。法的淵源是(人類)的共同精神。……法的理念是正義。各法規的最高目的是實現正義。”“正義是不可喪失的人類的價值。……如果法律不忠實於正義,只以實利為目的,那麼法的公正嚴肅就不復存在,實利也得不到。”
1917年,祁克發表了最後一篇重要論文《法律與道德》。在這篇論文中,祁克對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作了深刻闡明。他指出,法和道德具有緊密的聯繫,以1900年《德國民法典》為例,其中相當多的條款規定,如果違反了社會道德義務,法律將給予處理。同時,法和道德都是精神性社會的生成物,法的淵源有在社會中無意識發生的信念中產生和在自覺創造的信念中產生兩種情況,前者是習慣法的場合,後者是立法的場合。道德也有從無意識的信念中發生和從個人自覺形成的一般信念中產生的場合。前者是社會的共同行為規範,後者是被形式化了的倫理規則。
祁克認為,法與道德也有根本區別,即法具有強制力。由於文明社會中強制力由國家獨佔,所以法和國家互為因果。道德則不然,它的目的是人的內心服從,它與國家的強制力遙遙相對。同時,法律源自社會信念,而道德則源自個人信念。法律是允許、命令和禁止人的行為的規範,而道德則以人的思維為對象,著重於人的內部的意志決定。兩者有交叉又有區別。在相交叉的領域,兩者都有拘束力,而越出了交叉的範圍,則屬於兩者各自管轄的領域。當然,一般而言,道德管轄的範圍比法律要大得多。此外,法和道德也有衝突之時,即對道德允許的,法有時會禁止;對道德禁止的,有時法律卻是允許的。因此,必須協調兩者的關係,既要發揮道德的規範作用,也要倡導法律的教化作用。
在《德意志私法論》第一卷中,祁克還對社會法思想作了闡述,他指出,“與人的本質一樣,在法律上也存在著個人法和社會法的差別。這是因為,人作為個人在其是一種獨立的存在體的同時,也是構成社會的成員。”祁克認為,“個人法是從主體的自由出發,規律個人相互平等對立的關係的法律;社會法將人視為擁有社會意志的成員,將人視為整體的一分子。……所以,社會法是從對主體的拘束出發,規律有組織的全體成員的法律。”在《國家法的基本觀念》中,祁克進一步指出:“社會法,是從人的結合的本質出發,對人的共同形態的內部存在進行整理,從小的團體到大的團體,從低的團體到高的團體,日積月累的建設性的法則;是從夫妻到家庭、從家庭到村落,逐漸向上、逐漸擴大,最終至國家的構造起來的組織法。”
總之,祁克的理論,既是對歷史法學派觀點的繼承,又有許多創新,尤其是他的社會法思想,對後來社會學法學的誕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誠如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樣:“祁克首次在個人法領域之外,提出還存在著社會法領域,這是對現代法學的最大功績。”
第一,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形成和發達作出了貢獻。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誕生於法國,但由於當時法國學術界對法典的過分崇拜,導致了忽視習慣法和判例法,僅僅以法典條款為研究對象的註釋學派的誕生,該學派統治法國近一個世紀,阻礙了民法科學的發展。與此相對,在德國,由於學者們埋頭於對羅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創立了一個龐大的民法體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學學科。而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國法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歷史法學派的成員:胡果、薩維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溫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說,如果沒有歷史法學派,那麼,近代民法學就不會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第二,歷史法學派在挖掘、整理、恢復人類法律文化遺產方面作出了貢獻。現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學學科的歷史基礎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從中世紀起就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如義大利波倫那大學的前、後期註釋法學派(伊納留斯、阿佐、阿庫修斯以及巴爾多魯等)、16世紀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阿爾恰特、居亞斯等),以及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朴蒂埃等,都對羅馬《國法大全》進行了整理、註釋。歷史法學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予以總結、彙集、出版,從而使古代羅馬法的經典文獻能為創建近代法學服務。後者即日耳曼法,雖然從11世紀后,也為一些學者所研究,但大規模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歷史法學派中的日耳曼學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論》和《德意志團體法論》,在保存、恢復和闡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超越。
第三,歷史法學派人物眾多,觀點也不一致,不能以薩維尼否定自然法理論、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反對編纂統一法典而否定該學派對世界法學發展的整體貢獻。
第四,即使是薩維尼,筆者認為也是應當肯定的。這裡涉及的問題是:一、薩維尼的作品《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對近代民法學的誕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學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薩維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觀點,如同自然法學派認為法起源於人的理性一樣,是人類在認識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在比較虛無的“人類理性”之外,去尋找法的起源的途徑。正是受了薩維尼這種歷史主義的、民俗學的法學研究的啟發,後人便進一步將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了法學之中,從而創立了法社會學、法文化學、法經濟學等,豐富了人類認識法這一社會現象的手段。薩維尼的觀點是人類試圖科學地認識法的起源的無數智慧鏈條中的一環,不能全盤否定。三、至於薩維尼的政治立場,由於其出身貴族,加上他反對自然法學派和反對編纂法典等,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動保守的。但從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從政時表現來分析(1842年他擔任普魯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專心於改革貴族制度、擁護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確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據條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說19世紀40年代后的薩維尼是一名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和法學家也並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