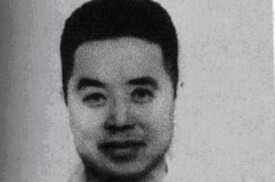孫定國
軍事家、哲學家、演說家
孫定國(1910—1964)山東省乳山市東珠村人。
1徠930年在本鄉小學任教。1934年赴太原,在閻錫山軍官教導團學兵隊當學兵。1936年9月加入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1939年調任山西新軍二一二旅旅長。同年12月參加山西新軍反擊舊軍的。
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裝新軍,歷任副官、總隊長、旅長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晉軍西路軍總司令陳長捷指揮所部的第六集團軍投入戰鬥,孫定國所在的彭毓斌軍執行肅清晉南新絳、稷山等地敵軍的任務,初次展現了他的指揮軍事才幹。當時他第一批加入了薄一波的“犧盟會”。
1939年(一說1941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在擔任晉軍訓教總隊長和新軍212旅旅長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時,都忠實執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事變”中,他率軍脫離了閻錫山,轉戰至晉東南太岳區,與薄一波等領導的部隊(決死一縱)會師,為發展和壯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裝做出了貢獻。
任太岳軍區212旅旅長
1940年任太岳軍區212旅旅長,以後相繼擔任了太岳軍區第二分區司令員、太岳軍區副司令員、鄂豫陝後方副司令員等職。
1948年孫定國被派往後方的馬列學校學習,從此即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他先後擔任了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校黨委委員、中科院學部學術委員等職務。此外他還著有許多哲學著作。
1956年康生重出江湖,此時正是“高饒事件”之後。康生看好孫定國的理論和寫作能力,便以同鄉的名義拉攏孫定國,囑其為自己整理和擬寫一個在八大會議上的發言稿,以便自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然而當1967年孫已死3年後,康生卻說這是黨校“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造謠,說我在‘八大’會議上的發言提綱是大壞蛋、大流氓、大騙子孫定國寫的,這純粹是流言,造謠,誹謗!難道我是文盲,不識字,連個提綱都不會寫,讓別人代筆?”不過,也是在“八大”后,康生就以黨內大理論家的面貌出現了——先後被任為“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理論小組”組長、《毛選》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也是從此,孫定國過不上好日子了。
孫定國是新中國成立后著名的哲學專家,學術地位也很高,如1956年北大哲學系受命編寫新中國第一套中國哲學史教材,參加者有馮友蘭、周輔成、楊憲邦、任繼愈、張岱年、李澤厚等諸多名家,孫定國與陳伯達、郭沫若、侯外廬、杜守素、趙紀彬、楊榮國、楊獻珍、艾思奇、胡繩等人任審查委員。
忠實地執行和履行自己作為黨內一名理論家的使命,在歷次理論運動中披掛上陣。1953年批判梁漱溟時,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的世界觀》《駁斥梁漱溟的“職業分途”的反動理論》,1954年批判胡適時他的《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等,都是影響很大的文章。
在中央黨校的行政領導中,楊獻珍、侯維煜、孫定國被視為“三駕馬車”。楊、侯、孫都是戰爭期間曾經戰鬥在山西抗日根據地的老革命,後來也都在中央黨校工作(楊獻珍曾是馬列學院教育長,侯維煜於1953年調入)。侯維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
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太谷縣委書記兼抗日自衛隊政委、八路軍獨立支隊政委、晉冀豫游擊支隊第三大隊政委等。
1939年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先後在延安抗大和中央黨校學習。新中國成立后,侯維煜歷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教育長、校黨委書記,中共華北局秘書長等職。後任馬列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和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黨委第二書記等。那時楊、侯、孫三人“密切配合,相互體諒”,“一起聆聽少奇同志的教誨,一起貫徹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個所謂理論權威的破壞,最後也一起遭受那個理論權威的殘酷迫害。”(楊獻珍《教誨十年,遺愛千秋——緬懷劉少奇同志對黨校工作的關懷》)

孫定國遺書
此後,康生在中央黨校發起了一個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運動,儘管“合二而一”論與孫定國毫無關係,但他還是被叫回黨校接受調查,在種種名義的批鬥會議上受到辱罵和訓斥。特別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會上,陳伯達用他的權勢肆意凌辱孫定國,稱之為“冒牌的哲學家”,並且首先用“大壞蛋”、“大流氓”、“大騙子”這種低級的稱謂來稱呼孫定國。孫定國辦公桌玻璃板下原有一張陳伯達署名的贈聯,抬頭是“定國同志”的字樣,可是這時陳伯達不認賬了,居然聲稱:“你把我扔到紙簍里練毛筆字的廢紙偷了出來,裱糊上,到處招搖撞騙,說是我給你寫的字,我陳伯達能給你這樣的壞人寫字嗎?”他還厲聲喝道:“你是死不要臉!”於是,“後來,‘斗’孫定國同志時,發揚了陳伯達式的‘戰鬥精神’,向他臉上吐唾沫”(楊獻珍《屠害忠良,終身陰賊——揭露康生反革命兩面派的嘴臉》)。顯然,對這樣的侮辱,就是常人也難以忍受了。就在這天夜裡,孫定國在寫下一份遺書後,義無反顧地走進黨校西南角的人工湖裡!他是從一個冰窟處躍入水中的。那一年,他54歲。
他留下妻子和5個孩子走了,而他們得到的卻是一紙丈夫和父親“自絕於黨,畏罪自殺”的通知書!更令人氣憤的是曾經叫囂“我陳伯達能給你這樣的壞人寫字嗎”的黨內理論家,在孫定國冤死後竟然憑藉權勢,將孫生前用自己的全部積蓄甚至是借債的藏書,其中還有價值在1.5萬元以上的善本書,僅以其原價的三分之一席捲而去。
那場著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運動,以將楊獻珍撤職、調離、逼死著名學者孫定國,開除講師黎明出黨(後於“文革”中投井自盡),挖出“合二而一”論小集團,並且先後從中央黨校調出或遣送回鄉多達百餘人而告結束。當然,不久之後的“文革”中,這些“合二而一”論的分子們,凡是僥倖不死的,又一次遭受到莫大的衝擊和凌辱,直到這一“罪案”在“文革”后終於獲得平反。
孫定國臨死前寫下的遺書是耐人尋味的,然而迄今還未見有人解讀過這份遺書孫定國在遺書中所提到的那個人,在涉及到這封遺書的公開出版徠物中,都是匿名的。顯然,孫定國在決心赴死之前,決定不顧一切,要以自己的黨性,向黨揭發其言行。其實,在那一歷史條件下,這樣的事或人,實在是太多了。那麼,這個至今還被隱去名字的人物是誰呢?據推測,他就是黨校校長楊獻珍。
在馬列學院或中央黨校,自始就有火藥味極濃的意識形態的理論論戰,其雙方則主要是黨校內部的楊獻珍與艾思奇這兩軍對壘,且無論是建國初年的楊獻珍為首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與艾思奇為首的“單一經濟基礎論”,還是後來沸沸揚揚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以及“合二而一”論,它們都不過是後來“文革”的一場理論批判的小型預演。深知其內幕的孫定國最終無法選擇自己再次“站隊”的事實,他便以死來選擇逃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