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徐訏
徐訏(拼音:xū注音:ㄒㄩ)(1908.11.11—1980.10.5),原名徐傳琮,筆名徐於、東方既白,浙江慈溪人,中國現代作家。一位曾被稱為“鬼才”的教授作家,以寫作傳奇小說且高產而著稱。
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36年赴法國留學,獲博士學位。抗日戰爭爆發后回到中國,定居於上海。1937年,以小說《鬼戀》一舉成名。1943年在重慶發表其早期長篇小說代表作《風蕭蕭》,風靡一時,該年也被出版界譽為“徐訏年”。1950年移居香港。1956年在香港發表其後期長篇小說代表作《江湖行》。1972年被推薦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曾任香港浸會學院文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徐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文壇鬼才”之譽。著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詩詞、散文、劇本、文學評論集等60多種,計2000多萬字,其中長、短篇小說50餘部。台灣曾出版有《徐訏全集》。其小說注重情節曲折性、傳奇性,注意人物心理描寫,其浪漫主義既有精巧的現代包裝,又滲有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成分,是對中國傳統浪漫主義的超越。 1980年,徐訏在香港因病去世,享年72歲。
1908:11月11日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東部洪塘(現屬寧波市江北區)。童年涉獵《三國演義》、《紅樓夢》和《野叟曝言》等作品,也看了一些林譯小說。
1921:到北平,就讀於成達中學。
1922:因受堂叔影響,到上海轉讀天主教聖方濟中學。同年,因不滿洋修士的偽善,一學期后重回成達中學。
1925:就讀於北京潮南第三聯合中學。
1931:畢業於北京大學,獲得哲學學士學位。留校擔任助教,並修讀2年心理學,對行為主義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有相當了解。北大讀書時發表短篇小說《煙圈》。
1933:離開北平,赴上海,從事寫作。投稿於林語堂的《論語》半月刊。
1934:任上海《人間世》編輯,積極溝通京海兩地作者,出版了42期,1935停刊。
1936:3月,與孫成合辦《天地人》半月刊,至10期止。秋天,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哲學,接受伯格森的生命哲學。《阿拉伯海的女神》脫稿,寫《鬼戀》。
1937:7月,抗戰爆發,即籌備回國。
1938:1月底,返回已成“孤島”的上海,致力寫作,賣文為生。作品發表於《中美日報》、《宇宙風》、《西風》等。5月,與馮賓符合辦《讀物》月刊,又辦“夜窗書屋”,並在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擔任翻譯工作。
1942:年初,經桂林、陽朔到重慶,主編《作風》雜誌。於台灣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兼任教授。

上海書店影印本
1944:以《掃蕩報》駐美特派員名義赴美國。
1946: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整理詩稿,與劉以鬯辦“懷正文化社”。
1948:開始構思並創作《時與光》。詩集出版。
1950:到香港。
1953:《幽默》創刊,擔任主編。《彼岸》出版。辦創墾出版社。
1954:在台灣與張選倩女士結婚。《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出版。
1956:《江湖行》第一部出版。
1957:擔任珠海學院中文系講師。《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出版。
1959:《江湖行》第二部出版。
1960: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學教授。《江湖行》第三部出版。
1961:《江湖行》第四部出版。
1963:兼任新亞書院中文系講師。編輯《新民報》副刊。
1964:《時與光》脫稿。
1966:“文革”題材作品《悲慘的世紀》開始連載。
1968:創辦《筆端》半月刊。
1969:擔任浸會學院中文系兼職講師。
1970:任浸會學院中文系主任。
1975:組織“英文筆會”。
1976:創辦《七藝》月刊。
1977:兼任浸會學院文學院長。
1980:5月,退休。7月,赴巴黎出席“中國抗戰文學會議”。8月,因病進香港律敦治療養院。9月,為天主教徒。10月,因肺癌病逝,享年72歲。

民國時期的徐訏
1950年之後,徐訏隻身離開上海去了香港。徐訏在香港和台灣安居了近30年,寫了60餘部著作,在香港、新加坡任大專院校教職,四處講學,聲譽遍及海外各地。直到1980年因癌症去世,他在香港一住30年。這30年,對這位久負盛名的小說家而言,既有與大陸妻女生離死別的痛苦,也有與香港社會格格不入的矛盾,可以說心態極不平衡。然而,他的“專業作家”的願望,30年間卻始終只能是一個美夢。他首先必須就業掙錢,才能養家糊口。30年間,他當過報刊編輯、大學教師,辦過出版社、雜誌社,卻連一天的專業作家也當不上。種種的不愉快,種種的不平衡,使他成為身在曹營心在漢,自外於香港的“香港人”。徐訏對香港的無法認同,既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他居港30年,居然一句不學更不說香港話,他說的是上海話或者家鄉話——浙江慈溪方言。他請客吃飯,一般要到由滬遷港的餐廳,如“紅寶石”、“紅星”、“溫莎”或有上海廚師的餐廳。就連看京戲,也要看一些由滬來港的“票友”的演出。這樣一種濃重的上海“情結”,正是他不願認同香港的有力證明。這種情結,在其小說創作中也有突出表現。
論徐訏的當代意義

徐訏(左)與林語堂
徐於一九五零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對於中國最廣大的作家來說,一九五零年無論如何都是有特殊意義的年頭。許多作家既為社會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歡欣鼓舞,又不能迅速調整自己的創作心理以適應這種變化,因而有時不免手足無措,出現了創作斷層現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都曾有過這種困惑。相反,徐訏大概由於身處香港,與“十里洋場”舊上海的政治文化環境反差不大,反而在創作上出現了一個持續而穩定的創作高潮。就小說而言,他就有《彼岸》、《江湖行》、《時與光》、《悲慘的世紀》等長篇小說和《盲戀》、《痴心井》、《爐火》等一批中篇小說,此外還有《鳥語》、《結局》、《花束》、《有后》等許多短篇小說集。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上海印書館出版了徐訏的長篇小說《江湖行》。在此之前,這部小說已在香港的《祖國周刊》等幾家大期刊上連載過,受到了讀者和評論界的熱烈歡迎。司馬長風認為:“《江湖行》尤為睥睨文壇,是其野心之作。”
趙聰也說:“《江湖行》是他來港后的巨構。據說曾構思三年,又經過五年的寫作與修改,然後才定稿的,這部《江湖行》應是他的代表作,遠遠超過以前的《風蕭蕭》。”陳紀瀅則推崇它為“近二十年來的傑作”。蕭輝楷稱它為“足以反映現代中國全貌的史詩型偉大著作”。而徐本人對《江湖行》亦有偏愛,自稱:“我最喜歡《江湖行》。……這部小說雖然缺點很多(原因是擱擱寫寫,不夠統一,連筆觸都不一致),但內容結實。”顯然,長達一千多頁的《江湖行》不僅是徐創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對他人生經驗的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它不僅對於徐訏個體的生命和文學歷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更為深遠的文學史意義。
比較同時大陸當代文學日益狂熱的政治化傾向,《江湖行》這樣的充滿個人性、抒情性和藝術魅力的純文學作品無疑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特殊饋贈。大致看來,香港時期徐訏的小說題材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回憶為主,寫大陸上的生活,以《江湖行》為代表;一類是寫香港移民的生活,以《女人與事》、《結局》為代表。總的來說,徐訏香港時期的創作呈現出的是典型的現代主義特徵。但同時,由於徐一直把香港當作一個漂泊地,他的懷鄉情結使他對香港的現實也有了特殊的體驗,這某種程度上也加強了他小說的現實性。比如他的小說中就有寫江湖傳統的《傳統》;有借對神偷的描寫暴露舊中國黑暗的《神偷與大盜》;有表現香港社會拜金主義、“文化沙漠”的《失戀》;有寫人心勢利、世態炎涼的《舞女》;有寫在香港找不到職業,用玩具手槍行劫被捕的《手槍》等等,這些具有“現實主義”特徵的小說即使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其現實意義和認識意義也仍然是巨大的。這裡尤其應該提到的是作者寫於一九六零年前後的收在短篇小說集《小人物的上進》中的一組直接反映大陸社會現實的小說。一般論者由於政治原因皆對其忽略不論,而我認為,公正地說,這些小說自有其特殊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徐向來講究寫作“距離”和“情感過濾”,大陸當時的社會生活對徐來說雖沒有時間距離,但有著顯而易見的“地理距離”和“文化距離”。站在今天的歷史或藝術的高度審視當時大陸的當代文學作品,我們必須承認其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是違背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原則的,而且還帶有極濃的“偽飾”傾向。
而徐對當時中國大陸的“大躍進”乃至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以及大陸人婚姻狀況的描寫,卻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和深刻性。按照評論界的分析,大陸文學對“大躍進”那段歷史的認識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中才真正達到公正和客觀的。如果我們把徐的《康悌同志的婚姻》與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作一比較,就會有許多有趣的發現。兩部小說雖然同樣表現政治權力對於愛情婚姻的主宰以及由此而來的人性異化,但寫作時間上前者卻整整早了二十年。有人稱徐訏為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先鋒作家,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另外,寫於一九六六年,脫稿於一九七二年的長篇小說《悲慘的世紀》,以寓言的形式描寫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避開其政治偏見不談,其最早用文學形式表達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的思想,這無疑也是具有先鋒性的。

徐訏
西方漢學家伯圖西奧里(Gillian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萊(K·E·Priestly)也有同感,認為徐在二十世紀中國作家中穩固地居於領先地位。司馬長風甚至把他與魯迅和郭沫若相比:“環顧中國文壇,像徐訏這樣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數得來的僅有魯迅、郭沫若兩人,而魯迅只寫過中篇和短篇小說,從未有長篇小說問世,而詩作也極少,郭沫若也沒有長篇小說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無論詩、散文、小說、戲劇、批評,都無法與徐的作品相比,也許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質的方面,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雖然這樣的評論不見得就很公允,我們也很難完全認同,但它們至少從一個角度證明了徐訏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長期以來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徐這樣一位作家卻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動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義被排斥在我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視野和文學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的價值才開始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通過許多學者的努力,徐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與價值已經形成了許多共識,但是對於徐的當代意義,以及徐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價值似乎還重視不夠。本文對徐香港時期小說創作現代主義特徵的研究就是試圖在此領域做初步嘗試,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香港批評家廖文傑
李輝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內對徐訏評價很低,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完全沒提徐訏小說一事。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書影響性較低,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完全不同了。王璞在徐訏論文中的註釋中則以為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對徐訏不置一詞,可能是因為徐當年與石堂兩篇論戰的文章有關,但她寧可相信這遺漏是聖伯夫式的失手。但其實夏志清原來曾對徐訏與石堂論戰一文頗推許,1975年,夏志清曾在《書評書目》上發文說以前看了徐訏兩本書,覺得不對口,以後他出的書一本也沒看,並說一個作家一開頭不能給人新鮮而嚴肅的感覺,這是他自己不爭氣,不能怪人。廖文傑說,不過一個文學史家這樣也未免有點輕率與偏見吧。在徐訏去世多年後,夏志清又去函給《純文學》雜誌,說因早年在上海讀了徐訏的《鬼戀》、《吉布賽的誘惑》,不喜歡這種調調,故不考慮把他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連《風蕭蕭》都未看,對他可能是不公平的。(節選自《載道與言志。官方與民間——從搜尋徐訏資料帶來的感想,並作徐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
學者吳義勤
徐訏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曾經被嚴重“誤讀”的作家之一,在其誕辰100周年之際,重新評價他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是非常必要的。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來看,徐訏的文學價值無疑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一個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束縛的作家,是一個能夠超越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學觀念的具有恆久性魅力的作家。直到今天,他的小說在港台和海外華人圈中仍然有重大的影響,並有一個持續的、龐大的讀者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徐訏所建構的融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現代性文藝思想體系,自由穿梭於現代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之間的藝術能力,以及“雅俗共賞”的成功實踐與藝術經驗都無疑是他留給我們的值得珍視的寶貴遺產。在我看來,他留給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大遺產就是真正在藝術實踐的意義上解決了困擾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的“雅”“俗”對峙問題,他的小說真正為我們拆除了“雅”、“俗”對峙的樊籬,突破了“雅”、“俗”的壁壘,完成了“大雅”與“大俗”的轉化與融合,其“雅俗共賞”的成功經驗甚至對我們sa年代以來的那些先鋒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擾中國文學數十年的所謂“曲高和寡”的藝術怪圈也有著有益的啟示。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徐訏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個人的文學成就上,更體現為他的藝術經驗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史建構的獨特啟示。在紛繁混亂的20世紀,我們的作家為歷史、現實、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學代價。徐訏的成功為中國作家如何保持藝術上的純潔性、創作風格的獨立性和對於現實的超越性提供了異常寶貴的經驗。(節選自《徐訏的遺產——為徐訏誕辰100周年而作》)
學者馮芳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哲理寫作群中,徐訏創作具有其它作家難以比擬的長處:一是其哲理的深廣度。其作品具有既深且廣的哲理價值,甚至其哲學思想已自成體系,鮮有作家可以匹敵。二是其追求現代性達到了極高程度。徐訏寫了大量的文章來促進個人主體現代性、社會現代性的發展,這使他走在推動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潮頭浪尖上。三是其反思現代性危機的突出能力和“諧和”理想的建構。現代科技理性中存在的“二律背反”帶來了現代性危機:個人主體失去精神信仰,陷入價值觀危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金錢異化,就業競爭激烈;人與自然的關係惡化為生態嚴重失衡。早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大哲反思現代性危機之時,徐訏便已在同步思考,他思考的結果是:將科學理性精神與東方宗教哲學並駕齊驅,回歸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同時對古代“天人合一”思想進行揚棄,為個人主體性不夠突出的中國文化添加了個人主義,形成了個人與集體乃至宇宙“諧和”的存在論思想,徐訏對現代性的反思代表著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達到的高度。他在1950年代初提出“諧和論”又過了幾年,海德格爾才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遊戲學說”。徐訏的“諧和”哲學不僅可以緩解現代社會的危機,還為現代人提供了精神救贖之路。經過文革后又幾十年的發展,當今學界才初步達成類似共識,中國才在1990年有了生態美學。時間證明,徐訏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思是頗具有前瞻性的,其反思現代性危機的突出能力和“諧和”理想的建構堪稱與世界思想界同步。因此,徐訏前期的哲理性寫作具有突出的價值:它代表著現代中國最進步力量的自我建設與自我反思,同時他已經作出了建構。(節選自《不懈地追索》)
曉草
筆者發現徐訏和他的作品有一個“內冷外熱”現象,即了解徐訏作品的海外讀者多,內地讀者少,寧波的讀者更少。研究徐訏和他的作品亦是如此。徐訏研究的“外轉內”全因一個學生的偶然發現。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揚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因寫畢業論文走進該校圖書館的特藏室,發現一大排《徐訏全集》並放在《魯迅全集》旁邊。“什麼樣的作家其作品會比魯迅還多?”強烈的好奇心驅使這位學生從中拿起一本書冊來讀,這一讀不僅讓這位學生在特藏室發現了徐訏,而且還讓他成為大陸研究徐訏的第一人。因為關注和發現,這位學生完成了畢業論文《徐訏論》,1993年,蘇州大學出版了他的專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論》,這位學生就是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山東省級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吳義勤。之後,包括寧波大學在內的諸多院校紛紛將徐訏和他的作品列為研究對象。因為關注徐訏,筆者從收集的1980年10月16日的《香港時報》中發現:徐訏曾在1972年被香港中國筆會推薦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2007年底,上海市作家協會與上海三聯書店共同策劃、出版《徐訏文集》,文集已經付梓,在徐訏百年誕辰之際將舉行首發式等紀念活動。據上海市作家協會臧建民先生介紹,《徐訏文集》將成為上海市作家協會策劃的“海上文庫”第一套入庫作品。
1927年,徐訏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4年後獲得學士學位,又在同校研修兩年心理學。在北大讀書時,他發表了詩作,當時學校的一楊姓教授讀了他的詩作,評論:徐志摩的詩,其感情流於輕浮,而徐訏的詩感情比較凝重。我們從這一評論或許很難說出有多少價值,但這對於徐訏,一個剛剛在文學殿堂外徘徊的文學青年,是何等的重要!10年後,徐訏發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說《鬼戀》,這是徐訏留法時期的作品。一舉成名之後,又連續發表了《荒謬的英法海峽》、《吉布賽的誘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系列化的中篇傳奇小說,從而確立了徐訏在小說界的地位。徐訏的小說大都冷峭孤僻,讓人讀來真有毛聳發立的感覺,人們便戲稱他為“文壇鬼才”。“鬼”字不太好聽,可“鬼才”則是褒詞,而且也是對徐訏小說的形象描述。1943年,他的代表作《風蕭蕭》連載后,“重慶江輪上,幾乎人手一紙”,再現“洛陽紙貴”。《風蕭蕭》迷住了當時海內外的華人,這一年堪稱為“徐訏年”。而且以後兩年間,此書連出五版,成為一代人的愛國啟蒙書籍。在現代文學史上,“五四”時代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處於雙峰並峙的狀態,但到了上世紀20年代末,前者即開始呈現衰退的趨勢。20年以後,徐訏再次舉起浪漫主義大旗,《風蕭蕭》等一大批小說重振浪漫主義的雄風,同時小說中揉進了現代主義的成分。這樣,徐訏的很多作品既充滿浪漫、唯美色彩,又具有現代主義的深刻性,為此,仿效他的作家很多,最有名的是無名氏,以致當時文壇產生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有人稱之為“後期浪漫派”。顯而易見,在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史上,徐訏具有里程碑的作用,這是徐訏對現代文學的特殊貢獻。(節選自《姚江水哺育的大作家徐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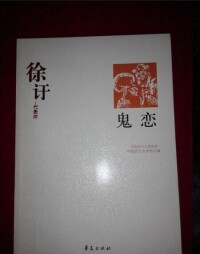
徐訏
《海外的鱗爪》(散文集)、1939,西風杖
《春韭集》(散文集),1939,夜窗書屋
《吉布賽的誘惑》(中篇小說)1940,夜窗書屋
《一家》(中篇小說)1940,夜窗書屋
《生與死》(話劇)1940,夜窗書屋
《西流集》(散文集)194O,夜窗書屋
《成人的童話》(短篇小說集)1940,夜窗書屋
《月亮》(話劇)1940,珠林書店
《契約》(話劇)1940,成都東方書店
《海外的情調》(短篇小說集)1940.夜窗書屋
《孤島的狂笑》(話劇)1941,夜窗書屋
《荒誕的英法海峽》(中篇小說)194l,夜窗書屋
《月光曲》(話劇)1941,夜窗書屋
《野花》(話劇)1942,成都東方書店
《鬼戲》(話劇)1942,成都東方書店
《兄弟》(話劇)1942,夜窗書屋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長篇小說)l943,光明書店
《母親的肖像》(話劇)1944,成都東方書店
《風蕭蕭》(長篇小說)1944,成都東方書店
《盲戀》(中篇小說集)1945(出版單位不詳)
《鳥語》(中篇小說集)1945,懷正
《阿拉伯海的女種》(短篇小說集)1946,懷正
《舊神》(中篇小說)1946,夜窗書屋
《煙圈》(短篇小說集)l946,夜窗書屋
《蛇衣集》(散文集)1947,夜窗書屋
《燈屋集》(話劇)1947,懷正
《潮來的時候》(話劇)1948,夜窗書屋
《黃浦江頭的夜月》(話劇)1948,懷正
《進香集》(詩歌集)1948,懷正
《待綠集》(詩歌集)1948,懷正
《借火集》(詩歌集)1948,懷正
《燈籠集》(詩歌集)1948,懷正
《鞭痕集》(詩歌集)1948,懷正
《幻覺》(短篇小說集)1948,懷正
《爐火》(中篇小說)1952,香港大公書局
《期待曲》(中篇小說)1952,香港大公書局
《輪迴》(詩集)1952,香港大公書局
《彼岸》(中篇小說)1953,香港大公書局
《殺機》(短篇小說集)1953,香港大公書局
《痴心井》(中、短篇小說集)1953、香港大公書局
《有后》(短篇小說集)1954,香港大公書局
《百靈樹》(短篇小說集)1954,亞洲
《結局》(短篇小說集)1954,亞洲
《傳統》(短篇小說集)1955,亞洲
《婚事》(長篇小說)1955,亞洲
《父仇》(短篇小說集)1955,亞洲
《花束》(短篇小說集)1956,亞洲
《私奔》(短篇小說集)1957,亞洲
《太太與丈夫》(短篇小說集),1958,亞洲
《時間的去處》(詩集)1958,亞洲
《燈》(短篇小說集)1959,亞洲
《女人與事》(短篇小說集)1959,亞洲
《神偷與大盜》(短篇小說集)1959,亞洲
《江湖行》(長篇小說)1960,香港大公書局
《徐訏全集》(l—15卷)1966—1970,台。正中(未出齊)
《三邊文學》(散文集)1973,香港上海印書館
《大陸文壇十年及其他》1973,香港大公書局
《花神》(短篇小說集)1977,黎明
《悲摻的世紀》(長篇小說)1977,黎明
《巫蘭的惡夢》(長篇小說)1977,黎明
《原野的呼聲》(詩集)1977,黎明
《傳薪集》(散文集)1978,台。正中
《傳懷集》(散文集)與麗明籌合集,1978,台。正中
《時與光》(長篇小說)1979,黎明
《小說匯要》(理論)編選,1974,台北集成圖書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