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煨蓮
洪煨蓮
洪煨蓮(1893.10.27-1980.12.22),男,原名業,字鹿岑,譜名正繼,號煨蓮,英文學名William。福建侯官(今閩侯)人。著名歷史學家。1980年12月22日,洪煨蓮在美國去世,終年87歲。
洪煨蓮幼學於家,1910年入福州鶴齡英華書院,1915年赴美留學,1917年獲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文學士學位,191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碩士學位。1920年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獲神學學士學位。1920-1922年在美國巡迴演講,爭取美國友好人士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強佔青島。1923年受燕京大學之聘,協助哈里・盧斯為燕京大學在北平西郊建造新校舍募得巨款,當年返回北平,參與新校舍建設,並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燕京大學執教的23年期間,曾歷任文理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職。1924年受燕京大學之命與哈佛大學協商,為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和爭取查爾斯・馬丁・霍爾的亞洲文化教育事業基金做出了重要貢獻。1925年赴哈佛大學講學。1930年回國,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兼導師。1933年、1940年先後獲得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名譽神學博士。
在燕京大學期間兼任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總編輯20多年,1937年獲巴黎茹理安(儒蓮)獎金。1941年12月與陸志韋、趙紫宸、鄧之誠等人被日軍逮捕入獄,次年出獄后拒絕為日偽工作。1945年燕京大學復校,仍任歷史系教授。1946年赴哈佛大學講學,1947年任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1947-1948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起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1958年兼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73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中西文化學術交流倡導者獎狀”。
洪煨蓮在1928年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精心制定圖書館管理制度,注意國內外新版書刊和明清史志善本圖書的採購,在圖書目錄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進。
洪煨蓮博聞強識,治學嚴謹。非常重視工具書的編纂與應用,自創“中國字庋擷法”,著《引得說》,用以編纂各種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纂經、史、子、集引得64種,81冊,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大便利。為引得所做的《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文字從數萬言到近十萬言,考訂有關學術源流,彙集相關論述,論述版本流傳演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洪煨蓮對於杜甫的詩與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入獨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洪煨蓮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和中西文化交流事業,為發展燕京大學、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著作:《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英文專著)、《洪業論學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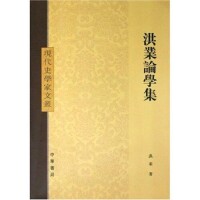
《洪業論學集》
1953年,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自傳之後,請胡適為他作序。在序言中,胡適這樣寫道:我在北大與燕大為鄰,對燕大的成長非常關心,司徒雷登領導的燕大成績非常可觀,“我趁此向燕大的中國學人致敬,特別要向洪業博士致敬;他建立的燕京圖書館,出版《燕京學報》,而且創辦一項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叢書,功勞特別大”。
燕京大學教務長
洪業,號煨蓮,1893年10月27日生於福州。他的父親洪曦是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辛卯科舉人。
洪煨蓮的啟蒙教育是在私塾中進行的。1904年,他隨父親到山東曲阜任上,進入縣立新式學堂讀書。後到福州,就讀於美國傳教士開辦的英華書院。1915 年畢業后,得到書院董事漢福德・克勞弗德的資助,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衛斯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協和神學院,獲得文學士、文碩士、神學士等學位。
1922年,他被聘請為燕京大學教會歷史助理教授。翌年8月攜妻女回國。
作為一個學通中西的教育者,洪煨蓮經常思考如何將中國幾千年的學問融入大學教育的框架之中。他認為一古腦將其歸入“國學”是不科學的,也太不負責任了,應該將古人留下來的東西分成:語文、數學、科學、人文四大類。中國的考古、藝術、哲學、宗教等都應該與相對應的西方科目結合在一起,來教和學。
1924年,洪煨蓮出任燕大文理科科長(又稱教務長)。他深知燕大要想在國內高校中立住腳,必須要把中文系辦好。他辭退了教中文的幾位“老古董”,高薪聘請資歷高深的教授。並取消預科,創辦了文理科研究院。嚴格規定學生各科平均成績達不到乙等者,學校將勒令其退學。執行該規定第一年的400多名學生中,有93名學生因為沒有達到標準而退學。洪煨蓮對學校課程的設置和改進想了很多辦法,對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了一定的促進改革作用。洪煨蓮為燕大圖書館的建設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洪煨蓮任教務長期間,燕京大學由一所默默無聞的教會學校,一躍而成為與清華北大齊名的國際性知名學府,洪煨蓮功不可沒。
“我是賣國賊,你得救救我”
1925年的一個夜晚,洪煨蓮的學生王近仁突然打電話要見他。一見面,王近仁便跪在自己的恩師面前:“我是賣國賊,你得救救我。”洪煨蓮被弄得滿頭霧水,趕忙將他扶起來,“別說胡話,你一個窮學生哪裡有賣國的資格。”
王近仁向他哭訴道,自己為了掙點錢維持學業,去年向學校請了假,給一個從哈佛來的叫華納的美國人當翻譯。華納提出了一個到西北探險的計劃,在王近仁的安排下,他們到了敦煌。在莫高窟附近的一個廟裡住下后,華納說要研究佛教古物。有一天睡到半夜,王近仁在朦朧之中發現華納不見了,趕忙出去找。在一個窯洞里,他看到華納正在用一塊布往壁畫上蓋。發覺身後有人,華納嚇了一跳,見是王近仁,他神色非常尷尬地說道:這些東西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很高,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把它們遺棄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無異於暴殄天物。美國的許多大學都想搞這方面的研究。所以,他現在正試著用甘油滲透的棉紗布,把壁畫揭下來帶回美國。一旦試驗成功,他還會再來,到時候還要請王近仁幫忙。
當時,王近仁就覺得有點不對勁兒,但沒往深處想。可現在那個華納又來了,帶著好幾個人,還有大量的甘油和棉紗布。王近仁知道,他們是要動真格的了。
洪煨蓮倒吸了一口冷氣,一旦華納的計劃實現,敦煌遺址將被洗劫一空。他再三叮囑王近仁,一定要裝得像個沒事兒人一樣,繼續跟華納到敦煌去。
天一亮,洪煨蓮便雇了車去見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秦汾。秦汾非常重視這一情況,當即用電報逐個通知北京到敦煌沿途各省、各縣有關人員,有一批美國人要到西北考古,請各地官員予以悉心關照,加派武裝保護他們的安全。
洪煨蓮懸了一夜的那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華納帶著他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從北京出發。令他奇怪的是,沿途所到之處,都有政府官員出面接待。到了敦煌之後,每個外國人都由兩個中國士兵片刻不離地保衛著“安全”,華納他們根本就沒有下手的機會。敦煌壁畫免此浩劫,洪煨蓮功不可沒!華納垂頭喪氣地踏上了歸程,路過蘭州時,他把甘油和棉紗布都送給了當地一所教會醫院。
“熊掌怎麼還沒上來?”
1928年,哈佛大學邀請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洪煨蓮赴美講學。授課之餘,洪煨蓮的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哈佛的圖書館里。館藏有關中國近代外交材料之豐富,令他欣喜若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協約國獲得的德國外交史料,蘇聯公布的沙俄時期檔案,西方人親眼目睹的太平天國等等,讓人眼花繚亂,愛不釋手。“奇文共欣賞”,他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急忙寫信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國內研究近代史的蔣廷黻、簡又文等好友。
其中,洪煨蓮最感興趣的是一本1887年版的德文書―《蝕經》。書中計算出從公元前1209年到公元2161年,3000多年間80個日蝕的日期、每次日蝕的經過以及在地球的哪個地方能看到它。歷代留下來的古籍中有不少“偽書”,即使在那些“真書”中也有許多錯誤的記載。辨別史料真偽,是學者們在研究當中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洪煨蓮欣喜地發現,《蝕經》這本書能為學者們在去偽存真的過程中提供強有力的佐證。
1930年,洪煨蓮回到燕京大學。在教學過程中,他發現許多受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學生,對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接觸有限,認識不深。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查找資料,對他們而言很有些吃力。洪煨蓮因此產生了編纂引得(即索引,英文index的音譯),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想法。
這年秋天,經過學校本部年會的批准,引得編纂處成立,主任和總纂一職由洪煨蓮兼任。田繼綜、聶崇岐和李書春分別擔任編纂。引得編纂處的主要任務是將中國主要的古籍進行系統地重新校勘,用現代眼光作出全新的評價,並加編索引。此前,雖然有人做過這項工作,但大都不如洪煨蓮主持下的引得編纂處做得系統、紮實。
引得編纂處整理了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莊子》、《墨子》、《荀子》、《十三經》等大量古籍。引得中有十幾種是關於古人的人名、字、號、傳記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這方面非常講究,相互之間的稱呼,因為彼此關係的不同而不同,名、字、號、別名、郡縣裡望等等都可以用來稱呼某人。況且有的人有好幾個字和號,歷史上同名同姓的人更多,功力淺一點的研究者很容易搞混。而在前四史的人名引得和這些綜合引得的幫助下,從上古至清代歷史上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了。
在書目方面,引得編纂處搞了《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明代敕書考附引得》、《藏書紀事詩引得》等。這些引得為研究者提供了古籍何朝出現、何代佚失等相關線索。
1931年到1951年,編纂處共出版正刊41種,特刊23種,共計64種,81冊。這一系列工具書在為研究者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可靠、準確、帶句讀的版本。引得序言中對古籍自身價值、版本優劣所作的精闢獨到的分析,更令後學者耳目一新。直到現在,除一些被更新的索引替代外,許多種引得仍為國內外研究者所使用。
在燕京大學歷史系的講壇上,洪煨蓮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培養一群具備世界觀的中國歷史學家,希望他們能從璀璨的中國古老文化遺產中有所發現,將其中的精髓永遠地傳承下去。他隨時留意那些有願望有能力做歷史工作的學生。首先,這些學生得有清醒的頭腦,其次還需要具備搞學術研究的獨立精神。一旦發現可塑之才,洪煨蓮便刻意予以栽培。但同時又對學生們進行嚴格要求,文章所引用的論據必須是第一手的,並且要詳細標明出處。
洪煨蓮在學生中培養歷史人才是有計劃的,主要是斷代史。在他的鼓勵下,學生中有鄭德坤搞考古,齊思和研究春秋戰國,瞿同祖專攻漢代,周一良研究魏晉六朝,杜洽研究唐代,馮家升研究遼代,聶崇岐研究宋代,翁獨健研究元代,王鍾翰研究清代。如今,他的學生們大多已經作古。他的學生的學生也多已成長為中國歷史學界的中堅力量。若泉下有知,洪煨蓮當可笑慰了。
對於特別可造就的學生,洪煨蓮便鼓勵他們學習外語,盡量幫助他們出國深造。翁獨健是福建人,在燕京大學,他不僅學會了日文、英文,而且還能讀懂蒙文、法文、德文、俄文和滿文。洪煨蓮拿出以前一個學生的文章,交給翁獨健修改。翁改好后,洪煨蓮看了非常滿意,就讓他整理《道藏子目引得》。自己卻暗地裡跟哈佛大學聯繫,推薦翁赴美深造。拿到哈佛大學同意接受翁獨健的電報后,洪煨蓮將這個心愛的學生叫到了辦公室。翁獨健被這從天而降的喜訊驚呆了,“事先您怎麼一點消息都不透露給我呢?”洪煨蓮慈愛地看著他,微笑著說:“我怕辦不成”。
洪煨蓮開的“歷史方法課”,令學生們受益匪淺。他請學校圖書館的職員,利用星期天時間,到市場上去收購廢紙。這些廢紙中什麼都有,包括日曆、藥方、符咒、信件等等。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便帶了學生到廢紙堆中去挑挑揀揀。洪煨蓮要求學生要一張張地看,紙上寫的是什麼,什麼時代的東西,有什麼背景……一旦發現有歷史價值的東西,他就要求學生據此寫一篇文章拿到《大公報史地周刊》發表。
他們在廢紙堆中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有一次翻到幾頁清朝檔案,洪煨蓮當即交還給政府了。還有一回,發現了一封信。仔細辨認,竟然是清末一位著名學者寫給封疆大吏端方的效忠信,自告奮勇要為清政府偵察革命黨的活動。
《大公報史地周刊》由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師生輪流負責。當時《大公報》的主編是張季鸞,報社付給每期周刊100元,作者每千字可以得到5元稿酬。年底結完賬,清華、燕京義務編周刊的人就一起將餘下的錢吃掉。有一年到厚德福去吃熊掌,恰好張季鸞帶著報社的員工也在那裡。張過來和洪煨蓮打招呼。邊談邊吃,聊了好一陣子。洪煨蓮很納悶就問周圍的人,這熊掌怎麼還沒上來。同桌的人告訴他,你早已經吃過了。洪煨蓮後悔得不行,第一次吃這麼珍貴的東西,凈顧著聊天了,居然食不知味。
“我向武力鞠躬”
1941年12月8日早晨,洪煨蓮接到了燕大哲學教授張東蓀的電話:美國和日本開戰了。幾乎與此同時,手持上了刺刀的三八槍的日軍士兵已經把住了燕京大學的校門。不久,司徒雷登也在天津被捕。
燕大1941年的聖誕節沒有了五光十色的聖誕樹和白頭髮、白鬍子的聖誕老人。日本軍部派有末精三少將來到燕園,要求燕大在日本指揮下進行改組,自然不會有人聽從。幾個星期後,日軍決定解散燕大,美麗的校園成了日軍醫院。
聖誕節過後沒幾天,洪煨蓮和鄧之誠、蔡一諤三人同時被捕。大約關了一個星期左右,日本人開始對他們進行審訊。一進審訊室,翻譯要求洪煨蓮“給太君鞠躬”。年近半百的飽學之士,在山河破碎之際,竟然被迫向一個20多歲的侵略者行鞠躬大禮,這是何等的悲哀。破巢之下安有完卵!洪煨蓮面色凝重地說:“我向武力鞠躬”。畢竟面對的是一位大學教授,日本軍官不敢太過放肆,搬了一張椅子請洪業跟他面對面地坐下。先問洪業的姓名、年齡、籍貫、學歷、為什麼到美國讀書、到過日本沒有、在日本有沒有朋友等等。類似的談話大約進行了半個多小時,日本軍官突然發問: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我是。”(後來他才知道,被捕者抗日如果不明說,日本人會動刑的)“你為什麼抗日?”洪業非常坦率地答道:“我不得不如此。請給我二十分鐘,不要打斷。”日本軍官答應了。洪業說:“我不仇視日本人民……但我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戰爭什麼時候終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總有一天要終了。戰事結束時,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我可憐日本人民,因為他們受軍人哄騙了,當他們有一天覺醒時,便會發現所有的宣傳都是假的,你們宣傳說日本的目的是要亞洲各國共同繁榮,這完全是騙人的話,……你們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個韓國。”審訊的日本軍官聽了洪業這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后,臉色發白,不待翻譯將洪業的話譯完,便揮手讓衛兵將他帶回牢房。
洪煨蓮回到牢房,偷偷地將受審經過說給同牢的難友聽。下午,洪煨蓮被再次帶去審問。當翻譯叫他“給太君鞠躬”時,洪煨蓮又說:“我對武力鞠躬”。
這時候,年輕的日本軍官忽地站起身,來到了桌子旁邊,深深地彎下了腰,用流利的中國話講道:我向一個不怕死敢講實話的人鞠躬。沒有材料記載當時洪煨蓮是一種怎樣的心情,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用他堅強的愛國心以及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洞察力,在精神上徹底征服了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
不久以後,洪煨蓮和鄧之誠、蔡一諤、張東蓀、陸志韋、侯仁之等其他燕大同仁一起被轉押到一所日本監獄里。在那裡,他們被搜身、蓋手印,而且每個人都分派了號碼,洪業是056號。
在監獄里相互之間不準交談。洪煨蓮和同仁們發明了兩套英文密碼互通信息,即用身體各個部分代表26個英文字母,大家在抓癢的時候,便可以將消息傳遞出去。再有就是靠聲音,短短敲一下是第一個英文字母,長長地敲兩下是第二個英文字母,依此類推。他們被相互隔離以後,互相間傳遞信息就完全靠第二套密碼進行。
到1942年4月中旬,日本人意識到這些教授們雖然有反日思想,但對他們都構不成太大威脅。懾於他們在中國國內以及國際包括日本的影響,決定將所有人無罪開釋。洪煨蓮等燕大教授在一個月之內陸續出獄。
希望能在宗教、教育、政治等領域有所成就
洪煨蓮出獄后,生活沒了來源,全家只有靠典當過日子。地毯、中英文打字機、書籍等等,都賣掉了。最讓洪煨蓮心疼的是一套《二十四史》,多年來他在上面做了許多眉批,但是迫於生計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天津東亞毛紡織廠老闆宋裴卿在一天夜裡,送來一大筆錢。他讓洪煨蓮把錢分給其他教授。為了避免引起日軍的懷疑,對外就說宋老闆從大家手中收購了不少字畫。洪煨蓮把錢分成10份,偷偷地給各家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當時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了避免留在敵占區的著名人士因生活所迫而屈身事敵,為了鼓勵洪煨蓮等燕大教授飽受囹圄之苦而不失愛國氣節,專門撥了一筆款項。但是經過國民黨底下人員的層層盤剝,真正發到教授們手中的也只夠買幾斤豬肉的了。
因為不肯向敵偽低頭,教授們自然找不到事做,經濟上的拮据造成了不少人家中關係緊張。為了躲避壓抑的家庭氣氛,教授們經常湊在一起打麻將消磨時光。有一回,天太晚了,洪煨蓮和陸志韋便借宿在朋友家中,兩個人促膝而談,聊了很多。
陸志韋問洪希望在哪方面有所建樹。洪煨蓮說他希望能在宗教、教育、政治等領域裡有所成就。接著他反問陸,陸志韋說他在教育方面很有些想法,他希望有機會出任教育部長。他自認為抗戰前期,自己在代理校長任上幹得還不錯。等戰爭結束了,還想繼任燕京大學校長。
洪煨蓮非常誠懇地說道,燕大復校后,校長人選大概就在你我之間,到時候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從燕京大學校長到教育部長應該不算太難。可沒想到陸志韋卻語出驚人,我不想做國民黨的教育部長。照我看共產黨能成功,我希望能在共產黨下做一任教育部長。
我愛美國,我更愛祖國
抗戰勝利后,洪煨蓮回到了滿目瘡痍的燕園。他感到這四年裡與外界隔絕得太久,對學術界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他想到美國去,一來儘快掌握學術界有哪些進展,二來為學校的經濟想些辦法。接到哈佛大學請他去講學半年的聘書後,洪煨蓮於1946年4月離開了北平。
1947年春,夏威夷大學聘請他到該校任教。洪煨蓮打算在那裡結束課程后回國。但是國共兩黨內戰正酣,經濟急劇惡化。夏威夷到處花紅柳綠,鶯歌燕舞,而國內卻是餓殍遍野。如此情境,令他躊躇不前。是年夏天,他決定先搬回康橋再做打算。
朝鮮戰爭的爆發,令洪煨蓮徹底放棄了回國的念頭。這個抉擇令他痛苦不堪,放棄回國,等於放棄燕大,等於放棄了自己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的東西。但是從太平洋戰爭以來的幾年裡,飽受流離之苦,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已經消耗殆盡,年過半百的他已沒有勇氣去迎接一個未知的挑戰。
雖然身在海外,洪煨蓮仍心懷故國。他常對朋友們講:“我愛美國,我更愛祖國。祖國是我父母之邦。”
中國大陸三年困難時期期間,洪煨蓮聽說他的得意門生,一向被稱為“齊胖子”的齊思和,因生活艱苦瘦了許多。他想有所表示,卻苦於無法聯繫。恰在此時,新加坡南洋商報編輯向他約稿,洪煨蓮便寫了《我怎麼寫杜甫》一文。嗣後,再三叮囑該報編輯,請他不必將稿費匯來美國,只需代自己買些食物寄給北京齊思和。
1979年10月,中國社科院兩學者赴哈佛講學,其中一位是鄧之誠與翁獨健的學生。洪煨蓮見到他們后非常興奮,親自下廚做飯招待。整個晚上他都在不停地詢問留在國內的朋友和學生的情況。經歷過“文革”浩劫,他所問的人大部分都故去了。洪煨蓮慨然長嘆,杜詩中有“訪舊半為鬼”,他現在是“相知多為鬼”了。洪煨蓮對文物更是關心,從米萬鍾的勺園圖到孔廟的石碑,到濟南的泉水……對故土幾十年的思戀,豈是這一個短短的夜晚所能表達完全的。
分給學生們的硯台
洪煨蓮在美期間,花了相當大的功夫整理杜詩,他不但在哈佛開了杜甫課,而且在耶魯大學、匹茲堡大學、夏威夷大學等高校演講時,也都以講杜甫的作品和品格為主。
他將自己多年來研究杜甫的成果整理成書,《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於1952年出版。這本英文專著分上下兩冊。上冊收錄了杜甫的詩作374首,並詳細說明其時代背景與史實的關係。下冊是註解,註明各詩的出處,中外人士的翻譯,歷朝歷代給杜詩所作註解,其中大量夾雜洪煨蓮本人的觀點和看法。該書對杜甫的生平有很多新發現,對杜詩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在序言里,洪煨蓮很謙遜地說自己英文不好,可能造成某些失實。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他將杜詩譯得非常傳神。這本書在杜甫及杜詩研究者當中,是當之無愧的權威之作。
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的教授柯立夫,與洪煨蓮結識於20世紀30年代,兩個人交誼甚篤。柯立夫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梵文、漢、滿、蒙等十幾種文字,對中國的邊疆歷史、地理,尤其是元代歷史相當有研究。20世紀50年代,他經常在星期日下午到洪煨蓮的寓所來,兩個人或討論問題,或同讀一篇經史書籍,以此展開學術交流。洪煨蓮有關元史的兩篇重要學術著作,與柯立夫的啟示是分不開的。
《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一文,長達數萬字,在包羅古今中外學者對《秘史》有關論述的同時,提出了新觀點。洪煨蓮認為《秘史》最初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原著》,是根據1264年一個老年文盲的口述整理而成。1368―1418年間刊行於世,改名為《元朝秘史》。這部作品問世后,成為世界各國各大學講授蒙古史的重要參考教材。作為研究蒙古史的權威,柯立夫教授對洪煨蓮的結論另有看法。但是為了避免破壞兩人之間的友誼,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閣,一放就是幾十年。直到洪煨蓮去世后5年,柯立夫才將其拿出來出版。
洪煨蓮的高足、國內著名清史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王鍾翰先生在回憶業師時曾寫道:“先生窮年累月,用力最久最深,莫過於《史通》一書。”洪煨蓮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發表過《史通點煩篇臆補》一文,文章引經據典,逐字逐句恢復了劉知幾原文的本來面貌。從1923年起,他便搜集了許多與《史通》有關的資料,並作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赴美之前,因為沒有思想準備,洪煨蓮沒有攜帶與此有關的材料。1950年,他決定不再回國后,便給聶崇岐寫信,請他將這些材料寄到美國來。聶很快回信,說許多相關書籍是50年前出版,屬於古籍,不能出國。洪煨蓮的手稿需經政府審查后才能寄出。但不幸的是,到 1952年中美之間斷郵,洪煨蓮只有望洋興嘆了。到美國之後,他只寫有《“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辯》等四篇文章。
改革開放以後,中美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起來。洪煨蓮請王鍾翰幫助處理自己留在國內的三萬多冊書籍和其他私人用品。王遵照老師的囑咐,將有保存價值的東西捐給學校圖書館或博物館,把圖書分給了做學問的朋友們。
在洪煨蓮的物品中,有一些古硯台,這是他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收集的。洪煨蓮還專門為此撰寫過一篇文章,說準備像老和尚傳缽一樣,等到適當的機會,把這些硯台分送給學術上有成就的學生,象徵著自己的學術後繼有人。他請王鍾翰把所存硯台分給在國內的學生。
1980年3月洪煨蓮在晨練時跌倒,造成肘骨骨折,此後身體每況愈下。是年12月16日夜,洪煨蓮突然神智不清,跟身邊的人講起了福州家鄉土話。1980年12月22日,在海外飄泊了30餘年的一代學人洪煨蓮撒手人寰,客死異鄉,終年8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