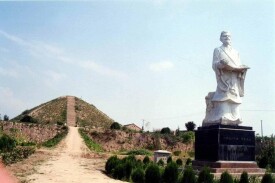公元519年
公元519年
公元519年,陰曆為己 亥年,又有北魏神龜二年的說法。這個時間是北魏朝時期。
南朝梁天監十八年
柔然建昌十二年
高昌義熙十年
(1)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令,右僕射王為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1)春季,正月甲申(初四),梁朝任命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為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2)丁亥,魏主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宜稱‘詔’以令宇內。”
(2)丁亥(初七),北魏國主頒布詔令,宣布:“太后臨朝執政已經將近六年,應當用‘詔書’的名義來向全國發令。”
(3)辛卯,上祀南郊。
(3)辛卯(十一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4)魏徵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逾坦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4)北魏徵西將軍張彝的兒子張仲瑀上書,請奏修訂選官的規定,以限制武將,不讓他們在朝中列入士大夫的清品。因此,議論和抗議之聲到處都是,這些人在大街上張榜,約定集合時間,要去屠滅張家。張彝父子卻平靜自如,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庚午(二十日),羽林、虎賁等將近一千人,一同來到尚書省叫罵,尋找張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張始均,沒有找到,就用瓦片、石塊砸尚書省的大門。尚書省的官吏們都很害怕,沒有人敢去阻擋他們。於是這些武士們又手執火把引燃了路上的蒿草,用石頭、木棍作為兵器,一直攻入張家住宅,將張彝拖到堂下,盡情地捶打污辱,並且燒毀了他的住房。張始均跳牆逃跑了,但又趕回來向賊兵求饒,請求他們饒他父親不死,賊兵們趁勢毆打他,將他活活投到火里。張仲瑀受傷逃脫了,張彝被打得只剩一絲游氣,過了兩晚就死掉了。遠近都因這件事而受到震驚。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鬧事的羽林、虎賁中的八個首惡分子,殺掉了他們,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乙亥(二十五日),又頒布了大赦令來安撫他們,於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資格入選。有識之士都感到北魏將要發生動亂了。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后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當時官員名額已經很少,應選的人都很多,吏部尚書李韶停止選擇錄用工作,遭到很多埋怨;於是朝廷便另外任命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崔亮奏請制定了新的錄用標準。規定不管應選者是賢是愚,只以其待選的時間為依據,時間長者優選錄用,因此那些長時間待選的人都稱讚他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給崔亮寫信說:“商周時期由鄉間學校選拔官員,兩漢時期由州郡推薦人才,魏晉兩代因循漢代舊例,又在各州郡設置了中正的職位主管這件崐事,雖然沒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但是所選的人才每十人中也有六七人是應當入選的。然而朝廷選拔人才,只要求他們文採好,而不考察他們的本體如何,考察孝廉只根據他們的章句學問如何,而不看他們有無治理國家的方法。設立中正官職只辯識他們的姓氏,而不考察應選者的才能、品行,選取士人的路途不廣,淘汰的辦法不嚴密。舅舅您被委任來主管銓選官員之事,本應改換掉那些不妥的章程,為什麼反而以年資長短為任用的標準,這樣一來,天下的士人誰還會再注意修勵自己的名節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說:“你所說的的確有深刻的道理,但是我前不久採取的那種辦法,也有它的道理,古今不同,時機合適時便應當加以變革。從前子產鑄造青銅刑書來挽救時弊,但是叔向以不合先王之法來譏刺他,這和你用古代禮法來責難隨時變化有什麼不同!”。洛陽令代京人薛琡上書說:“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官吏的手上,如果選拔官吏只按他們的年資,而不問他們的能力大小,象排隊飛行的大雁一樣按順序來,或象穿在一起的魚一樣由先而後地拿著名冊叫名字,那麼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夠了,按順序用人,怎能叫做銓選人才呢!”薛琡的上書交上之後,沒有得到答覆。後來薛琡又因此而請求拜見皇上,再次上奏:“請求陛下命令王公大臣推薦賢才來補任郡縣長官的職務。”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讓大臣們議定這件事,但是事情亦沒有下文。後來,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作了吏部尚書,因論資排輩這種辦法對自己有便利,就繼續奉行,北魏的選拔任用官員不得當,是從崔亮開始的。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徒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俊、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當初,燕國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魏國,他的兒子高謐作了侍御史,因為犯了法被流放到懷朔鎮,幾代人居住在北部邊疆,於是就養成了鮮卑人的風俗習慣。高謐的孫子高歡,深沉而有大志,家境貧困,在平城服役,富家婁氏的女兒看到他,認為他不同一般,便嫁給了他。他這才有了馬匹,得以充當鎮上的信使。他到洛陽時,見到張彝被打死一事,回到家之後,就傾盡財物來結識賓客。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高歡說:“皇宮中的衛兵們結夥起來焚燒了大臣的住宅,朝廷卻畏懼他們叛亂而不敢過問,執政到了這種地步,事態如何便可想而知了,豈可死守著這些財物而過一輩子呢?”高歡和懷朔省事雲中人司馬子如、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戶曹史咸陽人孫騰、外兵史懷朔人侯景、獄掾善無人尉景、廣寧人蔡俊等人,特別地友好親密,他們均以仗義任氣而稱雄於鄉里。
(5)夏,四月,丁巳,大赦。
(5)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6)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6)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為司徒,京兆王元繼為司空。
(7)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收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眾皆愧之。
(7)北魏接連幾代都很強盛,東夷、西域都不斷地向其進貢,他們又設立了互換物品的市場來取得南方的貨物,因此國庫非常充實。胡太后曾經臨幸藏絹的倉庫,命令隨行的一百多個王公、妃嬪、公主各自取絹,按自己的力氣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為扛的絹太重,跌倒在地,李崇扭傷了腰,元融扭傷了腳,胡太后奪下了他們的絹,讓他們空手而出,當時的人們都把這事當成了笑話。元融是元太洛的兒子。侍中崔光只取了兩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說:“我的兩隻手只能拿得動崐兩匹絹。”其他的人聽了后都很慚愧。
時魏宗室權幸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于禁苑,僮僕六千,伎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當時北魏宗族中受寵掌權的大臣們都爭比奢侈豪華。高陽王元雍是全國的首富,他的宮室園林和帝王的園林不差上下,有六千男僕,五百藝伎,出門時儀仗衛隊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彈唱,一頓飯價值幾萬錢。李崇與元雍同樣富,但他生性吝嗇,他曾對人說:“高陽王的一頓飯,等於我一千日的費用。”
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碗,赤玉卮,製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嘆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河間王元琛,總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駿馬,馬槽都是用銀子做的,房屋的窗戶之上,都雕飾著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真是金碧輝煌。他曾經召集眾王爺一同設宴飲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瑪瑙碗、赤玉杯,都製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產。他又陳列出藝伎、名馬和各種珍奇寶貝,令王爺們賞玩,然後又帶領眾王爺一一參觀府庫,其中金錢,布帛不可勝數,得意之下便回頭對章武王元融說:“我不恨自己看不見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認為很富有,回府後卻傷心嘆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繼知道這一情況之後便去勸解他,對他說:“你的財物不比他的少多少,為什麼這麼嫉妒他呢?”元融說:“開始我認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陽王,不想還有河間王!”元繼說:“你就象在淮南的袁術,不知道世上還有個劉備呀。”元融這才笑著坐起來了。
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為“蕭衍常蓄窺覦之志,宜及國家強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
胡太后愛好佛教,沒完沒了地修建各種寺廟,下令各州分別修建五級佛塔,以致百姓的財力匱乏,疲憊不堪。眾位王爺、權貴、宦官、羽林分別在洛陽修建寺廟,互相用寺廟的華麗來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設立齋戒大會,給僧人的布施動輒以萬計數,又常常沒有節度地賞賜身邊的人,耗費的財物不可計量,卻不曾把好處施捨到百姓頭上。這樣,國庫漸漸空虛,於是就削減眾官員的俸祿和隨員。任城王元澄上書,指出:“蕭衍一直對我國蓄有窺覦之心,所以我們應當趁國家強盛,兵強馬壯,早日規劃統一大業。但是近年以來,國家和個人都很貧困,所以應當節制不必要的費用,以便周給急務之需。”胡太后雖然沒有採用他的意見,但因此而常優待禮遇他。
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藉以修寺及供他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為“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有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北魏從永平年間以來,為修建明堂和太學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過一千人,有關部門又把這些人借去修建寺廟和服其他勞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沒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為此而上書,認為:“如此而廢棄治國的大業,資助不急需的費用,確為不該,故而應當撤消、減少各種勞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學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禮之期,百姓可以知曉禮樂。”朝廷下令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明堂和太學仍然不能建成。
(8)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准,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昞然。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禮,宮、商宜濁,徵、崐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雲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鐘管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眾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鐘為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准十三弦,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准當施柱,但前卻柱中,以約准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弦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中弦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即於中弦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眾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製作,不敢依許;事遂寢。
(8)北魏陳仲儒請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標準來校正八音。有關部門質問陳仲儒說:“京房的音律標準,今天雖然有樂器存在,但通曉的人很少,請問陳仲儒你是受什麼師傅指點,從什麼典籍中學習到的。”陳仲儒回答說:“我生性喜愛彈琴,又曾經讀過司馬彪的《續漢書》,見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規則是很明白的。於是我就極力用自己的愚鈍的頭腦,鑽研了很長時間,頗有收穫。用音準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來調校樂器。我研究過聲調本身,宮、商兩音應當低沉,徵、羽兩音應當輕清。如果按公孫崇的說法,只用十二音律劃分樂音,而又說變換宮調,清音濁音就都齊備了。因為黃鐘管最長,因此就用黃鐘管作為宮音,則每每跑調。如果平分成八個音,仍然需要分別採納各種樂器,以配成美妙的樂聲。如果把應鐘作為宮音,蕤賓作為徵音,這樣一來則徵音濁沉而宮音輕清,雖然具有韻律了,但卻成不了曲調。如果用中呂當作宮音,那麼十二音律就全無可取了。現在按京房的樂書所定,把中呂當作宮音,然後用減弱的音為商音,用起始的音為徵音,這樣才形成韻律。而公孫崇卻把中呂作為宮音,仍然使用林鐘為徵音,這怎麼能夠和諧呢?然而音樂十分微妙、精密,史傳所記都很簡略,如過去記載定律數之准,共有十三弦,隱間九尺,但是沒有說明需要弦柱與否。而且,一寸音節中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細密,難以分辨。我曾經私下裡試驗過,准應當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調中間的弦柱,以此來確定音準的分度,這樣產生出來的音韻就已經自然和諧了。它的中弦粗細應當與琴宮相同,用轉弦的軫來調音,使它與黃鐘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數劃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濁音節,其餘十二弦應當如箏那樣設立弦柱,就是將中弦上的一周的樂音,按度數標誌在十二弦上,然後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進行,取十二律的商、徵兩音。商、徵二音一旦確定,再用琴五調的調聲方法來協調樂器,然後錯采眾音來修飾它,如果不按照這種方法進行,聲音就不會和諧。況且燧人氏不向老師學習就掌握了用火的辦法,焦延壽不曾交學費拜師就變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說自己有知識的人想要教別人卻沒有人跟從他學習,心地通達的人沒有老師也能有所體會,但凡有一絲一毫的收穫,都與他的心胸有關,何必一定要經過老師的指授才能創造大事業呢!”尚書蕭寶寅上奏說陳仲儒的學問沒有老師傳授,就輕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認可,於是這件事就放下了。
(9)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已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為“歷奉三朝,骨鯁之跡,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孫也。
(9)北魏中尉不平王元匡因為自己的建議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駁回,非常氣憤,便又重新收拾好過去與高肇抗衡時所做下的那口棺材,準備再次以死相抗,來彈劾元澄。於是元澄也上奏了元匡的三十多條罪狀,廷尉判處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十二日),朝廷下令免除元匡死罪,剝奪了他的官爵,讓車騎將軍侯剛代替了他的中尉職務。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了處治元匡的意見,認為:“元匡曾經侍奉過三代皇帝,他的剛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內外都知道。因崐此孝文帝獎賞他‘匡’這個名字。先帝既然已經在先前容忍了他,陛下您也應當在現在寬待他,如果最後貶黜了他,那麼恐怕會因此而堵住了忠臣的口。”不久之後,又任命元匡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孫。
(10)九月,庚寅朔,胡太后游嵩高;癸巳,還宮。
(10)九月庚寅朔(十四日),胡太后巡幸嵩高;癸巳(十七日),回到宮中。
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相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餉領軍元義。太后召義夫妻,泣而責之。義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義之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義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義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既而義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胡太后曾經在閑聊時對兼中書舍人楊昱說:“如果我的親戚在外面有不稱人心的事,你一旦聽到了,千萬別隱瞞。”楊昱上奏揚州刺史李崇用五車裝載財物,相州刺史楊鈞製作銀質食具饋贈領軍元義。胡太后就召來元義夫妻,哭泣著責備他們。元義因此怨眼楊昱。楊昱的叔父楊舒的妻了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義的從曾祖。楊舒死後,元氏多次請求搬到別的地方住,楊昱的父親楊椿哭著斥責他,不肯聽從,因此元氏很仇恨他們。正趕上瀛州人劉宣明圖謀叛亂,事情被發覺后,劉宣明逃亡。元義指使元和以及元氏誣告楊昱藏匿劉宣明,並且說:“楊昱的父親定州刺史楊椿,他的叔父華州刺史楊津,曾經一起給劉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圖謀造反。”元義又使這個罪名成立,並派了五百御前衛兵在夜間包圍了楊昱的住宅,進行搜查,抓了楊昱,但是一無所獲。胡太后察問其事,楊昱報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胡太後為楊昱鬆了綁,判處元和以及元氏死刑。事後元義營救了他們,結果元和被免除官職抵罪,元氏終於也沒有治罪。
(11)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11)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八),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12)庚申,魏大赦。
(12)庚申(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
(13)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13)這一年,高句麗王高雲去世,他的長子高安繼位。
(14)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余皆罷遣。深,祉之子也。
(14)北魏因為感到選拔官員過濫而不精,就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以及范陽人祖瑩等八人因為有才能而留用,其他人都被罷職送回去。羊深是羊祉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