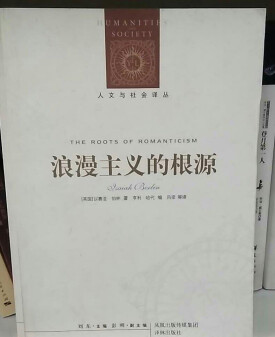浪漫主義的根源
浪漫主義的根源
本書根據以賽亞·伯林1965年關於浪漫主義的梅隆系列講座的BBC錄音結集而成,自浪漫主義定義問題始,中經浪漫主義之濫觴、成長和壯大的過程,至浪漫主義的巨大影響終。結構瞭然,思維縝密,處處閃耀著天才洞見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渾酣暢的即興風格,是一曲令人魂銷神醉的思想詠嘆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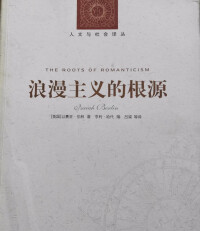
浪漫主義的根源
——約瑟夫·巴特勒
巴特勒這句話是以賽亞·伯林最喜歡的引語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開頭是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誤會,因為這部集子無論如何不能算做伯林關於浪漫主義的新書。自伯林於1965年三四月間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A. W. 梅隆系列講座上做了關於浪漫主義的脫稿演講之後,他曾試圖將其變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後的那些年裡,特別是他於1975年卸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一職之後,他不斷擴展自己的閱讀,積累了一堆筆記,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他把所有筆記存放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重新開始整理他的資料:他列出一些標題,並把篩選出來的筆記口述錄製到磁帶上,歸納到預設的標題之下。他甚至考慮利用已有的材料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寫一個長長的序言,而不是獨立成篇,作為他的一個專題研究。但這個計劃屢屢擱淺,部分原因可能是資料準備的過程太長,致使寫作的興味闌珊。據我所知,到後來他對這本計劃過的專著未著一字。
顯然,對於伯林的讀者來說,他未將演講修訂成書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對他本人來說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壞事。如果當初就完成此書的寫作,那如今這本充其量只算是編輯過的講稿就永遠不會出版。一旦經過精心修改和擴充,伯林演講所特有的那種清新、直接、強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風難免會變得晦暗。伯林還有一些脫稿演講最終都是以錄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來,我們不妨拿這些演講與那些終於修訂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講參照過的文字稿本做個比較,就會看出伯林為了出版曾經三番五次修改過他的內容。顯然,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鍊,但有時不免減弱了口頭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過來說,根據一篇尚未斧削的長篇底稿——伯林稱之為“殘篇”——來做演講,而非照本宣科,演講內容就會顯得酣暢淋漓。或許,以多元論的術語衡量,這二者之間的優劣根本不可比較。在這種情況下,優也罷,劣也罷,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種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標題是伯林自己早年計劃寫作該書時擬用的。在演講時,他將標題換成了“浪漫主義思想的來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為在索爾·貝婁1964年出版的小說《赫索格》的開篇幾頁里,書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猶太學者,正在經歷一場自信的危機。他在紐約的一間夜校里試圖講授一門成人教育的課程,卻未能成功。這門課程的名稱恰好就是“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romanticism)。據我所知,這完全是個巧合。伯林自己明確否認它們之間有任何直接聯繫。不過,無論如何,先前的標題顯然更加響亮。如果伯林當時確實因為某些理由放棄使用一個更好的標題,這些理由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以賽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俄國里加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自由四論》(1969,后擴充為《自由論》)、《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羅斯思想家》(1978)、《概念與範疇》(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
編者序
一 尋找一個定義
二 對啟蒙運動的首輪進攻
三 浪漫主義的真正父執
四 拘謹的真正父執
五 奔放的浪漫主義
六 持久的影響
參考文獻
索引
校後記
一 尋找一個定義
也許你們期待我的演講一開始就給浪漫主義做些定義,或者試圖做些定義,或者至少給些歸納概括什麼的,以便闡明我所說的浪漫主義到底是什麼。但我不想重蹈這種窠臼。傑出、睿智的諾思洛普·弗萊教授指出,當一個人意欲從事對浪漫主義課題的歸納時,哪怕只是無關宏旨的話題,比如說吧,英國詩人萌發出了一種對待自然的全新態度——姑且說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吧,他們的態度完全迥異於拉辛和蒲柏的態度——就會有人從荷馬的寫作、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時期的阿拉伯史詩、中世紀西班牙詩歌中,最終從拉辛和蒲柏的詩中找出相反的證據。因此我不準備歸納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傳達我所思考的浪漫主義的含義。
事實上,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要比浪漫主義文學本身龐大,而關於浪漫主義之界定的著述要比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更加龐大。這裡存在著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義是一個危險和混亂的領域,許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們迷失了自己的知覺,但至少可以說,他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維吉爾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腳印指向一個方向;又如波呂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進入,便不可重見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般地涉足這個領域。
浪漫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對我而言,它是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裡最偉大的一次轉折。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歷史進程中的其他轉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到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
不僅是思想史,就連其他有關意識、觀念、行為、道德、政治、美學方面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主導模式的歷史。任何時候觀察一種獨特文明,你都會發現這種文明最有特色的寫作以及其他文化產品都反映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支配著寫出這些東西的作家、畫出這些東西的畫家、譜出這些音樂的作曲家。因此,為了確定一種文化特徵,為了闡明該文化的種屬,為了理解人存身其間思考、感受、行動的世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儘可能地分離出這種文化所遵從的主導模式。以希臘哲學或古典時代的希臘文學為例。如果你閱讀,比如說,柏拉圖的哲學,你會發現支配他的是一種幾何或數學模式,很明顯,他的線性思維原則基於如下的觀念——即存在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可動搖、不可摧毀的真理,由此,人們可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導得出某種絕對正確的結論;人們可能通過柏拉圖所推崇的這種方法獲得絕對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種可以獲取的絕對知識,只有我們能夠獲取這種絕對的知識。幾何學,或者說廣義的數學,堪稱這種絕對知識的範式,最完美的範式。根據這種絕對的知識、根據這些真理,人們可以一勞永逸地,恆定不變地,無須更改地組織我們的生活;一切苦難、懷疑、無知,人類的各種罪惡、愚蠢都將從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種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藉助某種嚴格的原則,或某種方法就可達到真理,至少這是與冷靜超然的數學真理相似的真理——這種信念影響了后柏拉圖時代的許多思想家,當然也影響了具有類似信念的文藝復興思想家,像斯賓諾莎那樣的思想家,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紀思想家,他們認為有可能——如果不是絕對的話——達到某種近乎絕對的真理來整飭世界,創造某種理性秩序,由此,悲劇、罪惡、愚蠢,這些在過去造成巨大破壞的事物,最終可以通過應用謹慎獲得的知識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這是一種模式——我僅以它為例。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將人類從錯誤中解放出來,從困惑中解放出來,從不可認知但又被人們試圖藉助某種模式認知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但是,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結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過的人類。這些模式不能解釋人類全部經驗。於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終成為另一種意義的獨裁者。
讓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一種與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時期的聖經文化與猶太文化。你會發現一種完全不同的主導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對於希臘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家庭生活的信念,源於父與子的關係,也許還源於部落成員之間的關係。人們據此解釋自然和人生。這種基本的關係——比如父子之愛、兄弟情誼、諒解、尊卑之間的等級關係、責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來的贖罪需要——這套綜合屬性成為創造《聖經》的人們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人們解釋整個宇宙的依據,但對希臘人來說純屬不可理喻。
比如一首為人熟知的聖詩。當讚美詩的作者說:“以色列出了埃及……滄海看見了就奔逃,約旦河倒流。大山踴躍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大地“因見主的面便要震動”。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這完全無法理解,因為關於世界親自應和神的命令的信念,關於萬事萬物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有生命的事物還是無生命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都必須根據人類的關係,至少要根據時或神性時或人類的人格關係來解釋的觀念,都與希臘人關於神以及人神關係的觀念相去甚遠。因此,對於那些受到猶太影響、習慣從神跡啟示的角度閱讀的讀者來說,他們在閱讀希臘人的作品時,很難領會為什麼希臘人缺少責任觀念和義務觀念。
讓我來嘗試說明一下不同的文化模式會顯得多麼陌生。為了追溯意識變遷的歷史,我必須這樣做。人類歷史上已經發生過不可盡數的革命,但有時很難追溯這些革命的本源,因為我們籠而統之地認為所有的革命好像都一樣。維柯這位義大利思想家,大概是第一個使我們關注古代文化陌生性問題的人。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紀盛極一時。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一個生活貧寒、聲名隱微的人也曾盛極一時。比如,他指出,一首著名的拉丁六韻詩的結尾“JovisOmniaplena”(朱庇特主神遍及一切),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就有些不可理喻之處。一方面,朱庇特是一個投擲雷電的大鬍子神靈。另一方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omnia”——都被這長著大鬍子的神靈“充斥”了。維柯充滿驚人的想象卻又中肯地指出,那些與我們相距遙遠的古代人,他們的觀念與我們的觀念肯定大相徑庭。他們就是能夠構思出來這種想法——他們的神靈不僅是一個掌管神祗和凡人的大鬍子巨人,而且充斥了整個天空。
再舉一個大家更為熟悉的例子。當亞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討論友誼這一主題時,他出乎我們的意料地說,朋友有很多類型。比如,有種友誼指兩人之間熱烈的愛慕之情;另一種友誼卻存在於人們的商業關係之中,存在於貿易往來之中,存在於買賣過程之中。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世上有這兩種類型的友誼並不奇怪:有些人會全身心投入愛中,至少是對愛懷有滿腔熱情;而有些人只有買賣鞋子的關係——但二者都可以視做友誼。不過,這個事實,也許,在經過了基督教,經過了浪漫主義運動,或者別的什麼運動之後,在我們看來,就顯得不可思議。
我舉這些例子僅僅是要說明古代文化比我們想象的要陌生得多,人類意識已經發生過很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只有通過對古代著作進行批判性的解讀才能體察得比較清楚。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例證。我們可以把世界看做有機的——就像一棵樹,各部分共生共存,互相依賴——也可以用機械論的眼光認知世界,把世界視為一些科學模式的結果,其中各部分並不唇齒相依,國家,或者其他的人類制度都是一種零件,只是用來推進人的幸福,避免無謂的傷害。這些極不相同的觀點,屬於不同的思想背景,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
恰巧成為規則的是那些獲得優勢地位的學科——比如說物理、化學——作為富有優勢的學科,它支配自身發展的想象,在其他領域得到應用。在十九世紀,社會學成為優勢學科;在我們這個世紀,則是心理學大領風騷。我的論題是浪漫主義運動是一場如此巨大而激進的變革,浪漫主義之後,一切都不同了。這將是我要集中論述的觀點。
浪漫主義從何處興起?當然不在英國,儘管從理論的層面來講,無疑始於英國——所有歷史學家都會如是說。無論如何,英國不是浪漫主義以最戲劇性方式展開的舞台。這裡就生髮了一個問題:當我談論浪漫主義的時候,我指的是一個歷史事件(我似乎正在說它是的),還是一種與特定階段無關、不受其控制的普遍的精神狀態?赫伯特·里德和肯尼斯·克拉克都認為浪漫主義是一種隨處可見的永恆的精神狀態。肯尼斯·克拉克在哈德良的詩句中找到了浪漫主義的證據;赫伯特·里德也找到了很多例證。在浪漫主義研究方面著述甚豐的塞埃男爵列舉出柏拉圖、普洛丁和希臘小說家赫利奧多羅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認為他們都是浪漫主義作家。事實上可能正如他所說,但我不想涉足這方面的研究。我所要論及的浪漫主義有時問的限定,我無意涉及永恆的人類態度,只想關注在特定歷史階段發生、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某次變革。因此我準備將注意力集中到十八世紀的後期。變革發生,不在英國,不在法國,而是在德國。
根據通行的歷史觀和歷史變革觀,我們理解的十八世紀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就從法國的十八世紀講起吧。那是一個優雅的時代,一切都平靜安詳,在生活和藝術領域,人們都遵守規則,理智高於一切,理性主義步步推進,教會勢力節節敗退,非理性的東西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猛烈攻擊下全線崩潰。到處都是安寧的氣氛,到處都是雅緻的建築。到處都信奉普遍理性不僅可以用於人類生活而且也可用於藝術活動、道德、政治哲學。再後來,一種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襲來了。出現了情感和熱情的大爆發。人們開始對哥特建築,對沉思冥想感興趣。他們突然變得神經質和憂鬱起來;他們開始崇拜天才汪洋恣肆不可名狀的想象力;他們開始背棄對稱、優雅、清晰的概念。同時,其他的變革也在發生。大革命爆發;人民不滿,國王掉了腦袋。恐怖降臨。
兩場革命之間是否關聯,這點不很清楚。當我們閱讀歷史,我們會有這種感覺:在十八世紀末,災難性的事件發生了。起初似乎風平浪靜,隨後便有了突變,一些人歡迎它,一些人譴責它。譴責它的人認為這是一個優雅和平的年代。不明了這一點的人就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愉悅(plaisir de vivre),塔列朗如是說。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個做作虛偽的年代,而革命開創了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人與人之間更易理解的統治。不管怎樣,問題是:所謂浪漫主義革命——一場藝術和道德領域裡全新的動蕩變革——和通常所說的法國大革命的關係如何?在巴士底獄廢墟上起舞的人們,砍掉路易十六頭顱的人們,可是受到天才崇拜熱的影響,或所謂突然爆發的情感主義的影響,或把西方捲入騷亂洪流之中的思潮影響的同一撥人?顯然不是。可以肯定,法國大革命為之而戰的信念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則,浪漫主義通常與之關聯的理念即獨特性、深刻的情感反思和事物之間的差異性,二者的差異勝於相似性,它們之間完全沒有聯繫。
那麼如何解釋盧梭呢?盧梭被稱為浪漫主義之父,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正確的稱謂。但導致了羅伯斯庇爾思想形成的盧梭,導致了雅各賓派思想形成的盧梭,在我看來,並不是那個與浪漫主義有明顯聯繫的盧梭。這個盧梭是寫出《社會契約論》的盧梭,這部經典著作談到了回歸人類共有的原初法則;談到了施行普遍理性的統治而不是情感的統治——普遍的理性能將人們聯合在一起,而情感卻會分裂人們的聯合;談到了普遍公正與和平的統治——普遍公正與和平能消弭那些使人情智分裂、人與人之間緊張對立的衝突、騷亂和動蕩。
因此,要看清浪漫主義的劇變和政治革命的關係還非常困難。何況還有工業革命,與此也並非沒有瓜葛。畢竟,思想不能繁殖思想。社會和經濟的因素對於人類意識的劇變負有相當的責任。眼前亟待解答的問題是,又是工業革命,又是古典主義庇護下的法國大革命,又是浪漫主義革命。比如,就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偉大藝術來說吧。如果你看大衛的大革命繪畫,你很難把它與浪漫主義革命聯繫在一起。大衛的繪畫有一種雄辯,一種雅各賓黨人嚴峻的雄辯力,令我們想到斯巴達,想到古羅馬。它們傳達了一種對於輕浮、淺薄生活的拒絕姿態,令我們想起馬基雅維利、薩伏那洛拉,還有馬布利這些人,他們曾以普遍永恆的理想的名義譴責他們時代的淺薄。而浪漫主義運動,正如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的那樣,是對各種普遍性的激烈反叛。因此當務之急,是要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我如何理解這場突變,我為什麼會認為在那些年裡,也就是1760年到1830年之間,變革發生了,歐洲意識領域發生了一場劇變——為了讓大家明白我這些想法依據何在,我想先舉個例子。設想你在西歐旅行,就說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歐吧。設想你在法國,與維克多·雨果那些前衛的年輕朋友交談。設想你到德國去,同斯塔爾夫人拜訪過的人物交談,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紹給法國人的。設想你遇到浪漫主義理論家施萊格爾兄弟,或歌德在魏瑪的一兩個朋友,比如寓言家、詩人蒂克什麼的,或任何與浪漫主義有關的其他人士,以及他們在大學的追隨者,那些深受詩人、戲劇家、批評家作品影響的學生、年輕人、畫家、雕刻家。設想你在英國與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響,或最受拜倫影響,或與受拜倫影響的任何人交流,不論他在英國、法國,還是義大利,還是遠離萊茵河、易北河。設想你和這些人交談,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轍。他們認為,最高意義的價值是諸如正直、真誠,隨時準備為某種內心理想獻身,為某種值得犧牲一切、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的理想奉獻一個人的所有。你會發現他們對知識或科學進步根本沒有興趣;對政治權力沒有興趣,對幸福沒有興趣;他們對於為了找到個人的社會位置而去適應社會,與政府和平共處,對國王或共和國保持忠誠特別沒有興趣。你會發現,常識、溫和適度的態度與他們的思想毫不沾邊;你會發現他們相信為自己的信念戰鬥至最後一息的必然性;你會發現他們相信殉道的價值,無論這種殉難為的是哪種信仰;你會發現他們相信少數比多數更神聖,失敗比成功更高貴,成功往往是贗品或粗俗一類的東西。理想主義的信念,不是哲學層面上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動來實踐的信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準備為某種原則或某種確信而犧牲的精神狀態,一個永不會出賣信念的精神狀態,一個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狀態(因為他信,他願意這樣)。這種態度以前不曾多見。人們所欽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誠、靈魂的純凈,以及獻身於信仰的能力和堅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種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