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黃帝四經》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初付於帛書老子乙本前,當時稱《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后經專家鑒定,認為此書是失傳已久的《黃帝四經》。《漢書.藝文志》曾經著錄此書,但漢以後就失傳了,學者根據書的內容、文字、篇章數目等研究,認為此書成書時期當晚於《老子》,早於《管子》、《孟子》、《莊子》。最晚不晚於戰國中期。《黃帝四經》出土,經過今人唐蘭先生考證后,確認為《黃帝四經》。這是一部“治國之本”的書,它由四篇文章組成。這就為海內外黃帝子孫重新認識黃帝、黃帝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
《黃帝四經》與《歸藏》、《老子》、《莊子》,共為中華民族的幾部源頭性經典,它們不僅是哲學跟文化的重要載體,而且是古代聖哲關於文學、美學、藝術、審美的智慧結晶。黃帝四經等道家思想是歷史上除了儒學外被定為官學與道舉的學說。
1973年轟動世界華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黃帝四經》,包含四部經典:《經法》、《十大經》、《稱經》、《道原經》。
黃學起源於戰國,盛行於西漢初期,曾是百家學術之林,《黃帝四經》是其代表經典。西漢時期流行的“黃老”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是個謎。現《黃帝四經》出土,經過今人唐蘭先生考證后,確認為《黃帝四經》。這是一部“治國之本”的書,它由四篇文章組成。這就為海內外黃帝子孫重新認識黃帝、黃帝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
1989年,大陸餘明光先生把“黃帝四經”進行了註釋,由已故的周谷城先生題寫書名“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餘明光先生在書的“前言”里寫到:“黃學被淹沒了兩千餘年都不為人所重視,與此聯繫的西漢初期流行的‘黃老’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是個謎!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帝四經’,這就為我們研究和恢復這個學派在歷史上的地位,重新認識‘黃老’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
《黃帝四經》體現了道家學說由老子一派變成黃老學派的轉變,對先秦各家各派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中黃老學派、稷下學派與法家至為深刻;它的出現推翻很多一貫以來已經被認定的經學理論,於經學研究有極重要的地位。
黃帝學術思想,是尊道生法、修身治國、刑名相承、名理相應、民本與法制和諧并行的系統型文化體系,其中以《黃帝四經》論述法道修身治天下的內容最為全面,總體內容立足於四經修治,從道法、常法、律法、兵法等角度全面論述如何修身、治國、平天下,形成了成熟的法道文化體系。“執道,守一,好信,順時,守度,畏天,愛地,親民”是其正治思想核心。其中,“天時,地利,人和”的修治思想,已是家喻戶曉。“經紀”、“民富”、“囯強”等詞,更是現代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時尚要素。“南北有極”的記錄,則展示了祖先對地球的深度科學慧觀認知。《黃帝四經(九宮版)》,不僅是中國精神文明治國方略之大成,而且是世界上最古老而獨特殊勝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專著。《黃帝四經九宮版》蘊含道法和常法之源,記錄了2500年前天人合一模式下慧智共運、內聖外王、修身治世的寶貴經驗和方法,是實現民族復興與國家昌盛的必修教材。
《黃帝四經·觀》的宇宙生成模式“一一天地一陰陽一四時一剛柔一萬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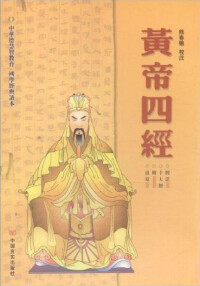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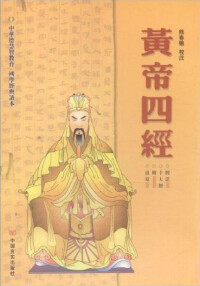
封面
| 《黃帝四經》之《經法》篇 | 〔道法〕第一 | 〔國次〕第二 | 〔君正〕第三 |
| 〔六分〕第四 | 〔四度〕第五 | 〔論〕第六 | |
| 〔亡論〕第七 | 〔論約〕第八 | 〔名理〕第九 | |
| 《黃帝四經》之《十大經》篇 | 〔立命〕第一 | 〔觀〕第二 | 〔五正〕第三 |
| 〔果童〕第四 | 〔正亂〕第五 | 〔姓爭〕第六 | |
| 〔雌雄節〕第七 | 〔兵容〕第八 | 〔成法〕第九 | |
| 〔三禁〕第十 | 〔本伐〕第十一 | 〔前道〕第十二 | |
| 〔行守〕第十三 | 〔順道〕第十四 | 〔名刑〕第十五 | |
| 《黃帝四經》之《稱》篇 | - | - | - |
| 《黃帝四經》之《道原》篇 | - | - | - |
《黃帝四經》是戰國時期託名黃帝的眾多著作之一,也是研究黃老之學的寶貴資料。本文認為,《黃帝四經》中蘊含了一定的美學思想,但迄今為止尚未見到有人對《黃帝四經》的美學思想加以研究。作者認為,從美學角度對《黃帝四經》展開討論,無論對研究先秦時期的美學理論,還是對建構當今的美學理論體系,都具有重要意義。《黃帝四經》雖然大體上屬於道家學派,但它也雜糅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實際上是兼采百家之作。因此,要研究《黃帝四經》的美學思想,還要弄清它與先秦時期的哪些主要學派有聯繫。本文對《黃帝四經》的美學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的梳理。首先是對《黃帝四經》的某些論述從美學的角度展開分析,然後總結出它主要的美學觀點。其次是把《黃帝四經》置於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下,與先秦儒、道兩家學派的美學思想加以比較。
本文上篇對《黃帝四經》所蘊含的美學思想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分析:一、關於“道”的美學思想。“道”是《黃帝四經》中的最高範疇,一切事物都是從“道”延伸出來的,而“道”本身就是最高、最大的“美”。以此出發,要求文藝能真實客觀地反映自然和社會,使之有利於自然萬物的生長,社會政治的昌明以及人倫道德的和諧。二、在確立了“道”這一美的最高標準之後,《黃帝四經》提出了美的批評尺度——“過極失當”。“過極失當”的原則要求藝術欣賞必須適度,不可過分。三、真實自然的美學原則——“至言不飾”。主張寫文章最關鍵的是要有真實可信的內容,而在形式方面則無需太過華麗和雕琢。四、“虛靜”的審美心態。以虛靜之心去觀照天下萬事萬物,而不受任何具體認識的片面性與局限性的影響。五、剛柔相濟的美學風格——“陰陽剛柔”。
《黃帝四經》對於陽剛與陰柔的各自特性及互相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所作的說明,正符合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的特徵。六、論藝術的作用——“文”與“化”。《黃帝四經》十分重視人文、藝術對社會教化的作用。本文下篇主要是對《黃帝四經》的美學思想與先秦時期儒、道兩家相關的美學思想進行比較。作者認為,《黃帝四經》關於“道”的美學思想與老莊之“道”是基本一致的,而與儒家尊崇道德禮義的美學規定格格不入。但在道的目的性方面,《黃帝四經》與儒家較為一致,而與道家則有所區別。《黃帝四經》中“過極失當”的美學批評尺度,把老莊在享受美與藝術時要求全壽養生和儒家對審美要求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在真實自然的原則上,《黃帝四經》與老莊都以真為最高境界的美,而儒家的真與美都要受到“善”的制約。
《黃帝四經》與老莊都以自然無為為美,以真為表現形式,而儒家則以文飾、有為作為真和美的外在表現形式。《黃帝四經》“虛靜”的審美心態雖然和老莊的“滌除玄覽”、“心齋”、“坐忘”的心理特徵是一致的,但《黃帝四經》的“虛靜”要求既合規律又合目的,而老莊卻是主張無目的、超功利的。《黃帝四經》的“陰陽剛柔”說,從哲學層面來看,與《老子》、《周易》是基本一致的;《黃帝四經》與儒家對“和”的理解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在這方面,兩家形成了互補的理論態勢,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黃帝四經》重視文明教化對社會的作用,與《周易》及儒家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但與老莊忽略文明教化作用的觀點有很大差異。文章在結語部分強調了《黃帝四經》美學思想的現實意義。
《黃帝四經》《老子》《莊子》差別
戰國之時,有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等思想流派,而道家為其中重要一派。然而,戰國道家的思想,並不是統一的。這其中,尤以《黃帝四經》、《莊子》、《老子》思想的差異為具有代表性。
《黃帝四經》《老子》《莊子》為戰國道家著作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黃帝四經》一書,久已失傳,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西漢人每每“黃老”並舉,則《黃帝四經》於黃老學之重要性,當不在被當作老子學說的《道德經》之下。《黃帝四經》不是傳說中的黃帝所著,其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約公元前四世紀左右。(註:參見《考古學報》1975年1期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研究》與2期龍晦《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原》,以及餘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是戰國中期宋國蒙人,曾做過漆園吏,其生活時代大約在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左右。《漢書·藝文志》曰:“《莊子》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包括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當是莊子自著,外、雜篇中多有出自莊子後學之手的著作,但也基本上代表了莊子道家的思想,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
《黃帝四經》《道德經》《莊子》的主要思想存在差別。
《黃帝四經》一書,分為《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經法》主要是講治國必須依靠法制,《十六經》是關於政治、軍事鬥爭的策略問題,《稱》講施政、行法必須權衡度量,區分輕重緩急,《道原》則主要講宇宙觀。其建立學術的出發點是教導君主如何用“道法”統治百姓。
《經法》九節,其一《道法》認為,“道生法”,治國必須依靠法制,強調道及法的重要性。其二《國次》強調刑罰舉措的得當和遵循自然法則,其三《君正》強調收買民心及合民意,要“從其俗”,“用其德”,使“民有得”,然後可以“發號令”,“以刑正”,“民畏敬”,“可以正(征)”。“發號令”是讓民“連為什伍”,“以刑正”是“罪殺不赦”,“可以正(征)”是“民節死”。要用民,必須行德殺、剛柔之道。其四強調君臣各守本分,以主強臣弱生六順,主弱臣強生六逆,六順則大治,六逆則大亂。其五《四度》強調不失本,不失職,不失天,不失人,反對“君臣易立(位)”之“逆”,“賢不宵(肖)並立”之“亂”,“動靜不時”之“逆”,“生殺不當”之“暴”,認為“逆則失本,亂則失職,逆則失天,〖暴〗則失人”,“審知四度,可以聽天下,可以安一國”。其六《論》強調君主“天天”,“重地”,“順四時之度”,察刑名,知情偽。其七《亡論》,主要講亡國之原因,認為“一國而服六危者滅,一國而服三不辜者死,廢令者亡。一國之君而服三壅者,亡地更君。一國而服三凶者,禍反也”。六危指嫡子代父行事,大臣為主,謀臣有異志,聽諸侯之廢置,左右親信比周壅塞,父兄黨朋不聽號令。三不辜指妄殺殺賢,殺服民,刑無罪。三壅指內位勝,外位勝,內外勾結孤立君主:從中令外,從外令中,惑賊交諍;一人主擅主,蔽光重壅。三凶指好兇器,行逆德,縱心欲。其八《論約》強調順天常,審刑名。其九《名理》強調“審其名”,“正道循理”,“虛靜公正”,“重柔”而不重剛。
《黃帝四經》四篇,其內容主要是出於君主統治術總結經驗的目的,因此,其思想以致治術為中心。《黃帝四經》倡導文武並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法術思想,最突出表現《經法》一篇中,而其餘三篇,也進一步發揮這種思想,如《十六經》認為德與刑之間,“先德后刑,順於天,即從天道出發,宣揚德刑統一,以德為主的刑罰觀。
《黃帝四經》倡導虛柔無為之道,《經法》所謂“執道者之觀天下也,無執也,無處也,無為也,無私也”,則是把無為與法術相結合,如此無為,實為有為,所以《十六經》曰:“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形(刑),形(刑)恆自定,是我愈靜;事恆自施,是我無為。”又曰:“卑約主柔。”即以無為而達到無不為,以卑弱守雌以實現以柔克剛之目的。
《黃帝四經》也強調民心之重要,《經法》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在有佴(恥),有佴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則守固單(戰)朕(勝)之道也。……審於行文武之道,則天下賓矣;號令闔於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稱》曰:“宮室過度,上帝所惡。”但這並不能改變其使民聽令,使民親上的目的。其中的柔術陰道,正是其強調道法之意義所在。
《莊子》一書,以內七篇為最重要。其建立學說的出發點是緣於社會現實黑暗,人民應該按照道的法則,即無為的原則混世,以保存生命。自《逍遙遊》至《應帝王》七篇,各有主旨,又互相聯繫,《逍遙遊》主張人通過“無己”,“無功”,“無名”,而達到“無待”的悠閑自得,無拘無束的境界。《齊物論》認為客觀事物是不分彼此,本質上是同一的,而人們關於是非彼此之爭論,皆出於成見執著,所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認為,儒墨名辯之是非、概念的爭論,是沒有認識到對立中的同一性,愛憎出於是非,是非出於界限,界限由於物的形成,而物產生於無物,成虧、愛憎、是非,彼此之對立歸源於虛無,因此,不稱之道,不辯之言,不仁之仁,不謙之廉,不害之勇,以及不用之用,才是真正的道、辯、仁、廉、勇、用。人們之所以不能達到真正的同一,是源於有身有我,因此,“吾喪我”,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則可接近真道。《養生主》強調“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即人處世要把握養生之道,善於權衡善惡名刑之分,不求名,也不致刑,沿著中庸,準確,無富貴名譽、罪惡刑罰的道路,“依乎天理”,“以無厚入有間”,“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人間世》是針對社會現實談人生哲學。“方今之時,僅免於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這是莊子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基本看法。“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這是莊子對個人力量的客觀估計。莊子認為,在亂世,靠一個人的力量要改變社會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順世,通過“心齋”的方式,達到虛心的境界。“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為道之所在,而虛心,即是心齋。“虛”的應用,便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無遷令,無勸成”,不有任何思想和主張,“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德充符》強調人之道德充實,則最為高尚,道德充實的標誌不是外在的形體、名譽、情感,而是內心中能齊同萬物,超越名利情感,是非好惡。《大宗師》強調師法天道,天道為萬物之大宗師,人之修道,應“知天之所為”,“古之真人”,是天道的化身,“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古之真人,忘懷於物,淡情寡慾,不計生死,隨物而變,應時而行,與天合一。要達到古之真人的境界,要超脫生死界線,忘仁義禮樂,最後達到“坐忘”,即“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職”。《應帝王》強調如果人作為帝王而治天下,則應以無為為根本,“立乎不測,游於無有”,而不能靠才能智慧。
概括而言,《逍遙遊》是絕對自由,《齊物論》是一切平等,《養生主》是養生之道,《人間世》是處亂世之情,《德充符》是不言之教,《應帝王》是無為之治,包括了日常修養、處事、為政諸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與黃老之立足於君主不同,莊子的出發點在於普通的個人,是教導普通民眾如何地處世,而能躲避君主政治的迫害。因此,其思想深處,包含著對現實社會的深刻批判,對民眾的受奴役、受迫害地位的深刻同情;而倡導絕對自由,一切平等,自然無為,正是莊子對抗“有為”社會罪惡的方式。莊子通過對“心齋”、“坐忘”、“吾喪我”的描述,使我們清楚地看出了他的“順世”論實際是以順世反抗社會;通過對是非、彼此、愛憎的否定,而表達了對現實價值觀、是非觀、道德觀的否定;莊子之人生哲學,首先是為每一個個人著想,即“為我”,肯定作為一個個人生存於社會不受侵害的權利;其“絕對自由”,是肯定人在思想上具有自由的尊嚴,通過肉體上的忘我,擺脫現實束縛,而達到無束縛。
《莊子》一書,也體現了莊子的理想社會模式,《馬蹄》提到“昔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在這種原始的政治狀態下,人民無所為而充滿了幸福。所以,莊子認為理想的社會應如赫胥氏之世一般:“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胠篋》言“至德之世”,“民結繩而用之,甘而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可以看出,莊子學派之理想雖是保守的、復古的,但此復古體現了對原始素樸、自然而平等、民眾幸福的渴望,就其本質來說,蘊含著積極進步之思想。
《道德經》贊同發展科技成果而不被慾望所控制,即,不贊同通過新技術來獲取利潤,贊同生活被科技所主導。認為如果這樣子,就會導致社會混亂,人們被智者所奴役。上篇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道德經》反對人類虛榮文明,是與主張政治的“無為”相聯繫的。所以,上篇又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己;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己”;下篇云:“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補’”;“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圾?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在作者看來,天下所見之美,必引來惡;眾人所譽之善,必有不善。尚賢,貴難得之貨,慾望,是社會混亂的根源。《道德經》也反對苛民之政。“悶悶”之政是所謂“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察察”之政則“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奸偽”。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道德經》說出了人類追求與治理的根本原因,如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老百姓都是追求活得更好而已的生活而已,多稅就會降低甚至剝奪了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權利,所以老百姓為了活著而不怕死,這樣就容易“犯法”,實屬無奈之舉。《道德經》批判統治者之“有為”,批判智者敢為而盜竽,批判智者誤導老百姓“是賢貴於生”,“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批判以知(智)治國,“古之善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惡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就是讓老百姓淳樸無憂而自在幸福。
戰國道家存在黃老與莊子的不同
《漢書·藝文志》把《黃帝四經》、《莊子》、《道德經》都列入道家,這是因為他們都把“道”看作是其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和最高原則。但除此之外,他們的差異卻是非常大,而且,有時候有根本性的區別。《莊子·天下》評論關尹、老子的學術云:“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無形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苟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進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側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雖未至於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這裡,作者雖然極力推崇關尹、老聃虛懷若谷,淡然神明,無為無實,曲全無福,但認為關老並未達到真正的真理之高度。莊周則是另外一個樣子。《莊子·天下》又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天下》的主旨在於說莊周之學是戰國學術的頂峰,以關尹、老聃“博大真人”而“未至於極”,不尊崇,這說明莊子學說與老子學說,有聯繫也有區別,而且,莊子學說是比老子學說更趨極端的。
《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道家是戰國諸子中重要一派,其學說本來就有“南面”與“放者”之分。《黃帝四經》與《道德經》立論的出發點是君主,所以應是所謂“南面之術”,重法術;莊子之學,是“放者”所為,絕禮學仁義,而任清虛。《黃帝四經》與《道德經》雖主流相同,但《道德經》對現實社會道德的批判,對傳統價值觀的否定,卻是《黃帝四經》民不及。《道德經》的這個特點,使它和《莊子》有了相似的地方。漢初,黃老之學盛行,而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師,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其學博,又諳道論,其雲道兼陰陽、儒、墨、名、法,又隨時變化,是言道家本有陰陽、儒、墨、名、法之內容。其曰道之無為無不為,虛無因循,則涉及治術,參《漢書·藝文志》所云“南面之術”,我們可以肯定地推斷,這裡所謂道家,主要是指黃老之學,而非無為一派的莊子等人。
陳柱《諸子概論》分道家之流派為四種,即有為派,無為而無不為派,無為派,無不為派。有為派包括黃帝、伊尹、太公、鬻熊、管子等人的著作;無為而無不為派為《老子》,無不為即有為,所以黃老之學近似;莊子任天,楊朱縱慾,《戰國策·燕策》所記陳仲子遁世,皆屬無為派,無為派雖與《老子》同有“無為”,但《老子》通過“無為”而達到“無不為”,歸結為有為,莊子則以“無為”為終極目的。“無不為派”是韓非子,已是法家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論莊子之學曰:“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又論老莊申韓之不同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之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檄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註:《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集解》曰:卑卑,“自勉之意也。”)
太史公尊黃老,其以老子為“深遠”,只是一家之言,不足為憑,但區分申不害、韓非子與莊子的差異而認為三人思想“原於道德之意”,即老子思想有自然、名實、法術之論,卻是可供我們參考的。陳柱之言“庄、韓兩家之學皆出於老子。……然庄則持絕對放任主義,韓則持絕對干涉主義,殆如冰炭之不相同焉。”“質而論之,老子之言多兩端,而庄、韓各執其一。”(註:見陳柱《老學八篇》)也就是說,老子學說,兼有干涉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方面,而莊子則去干涉主義,獨任自由主義。由於我們認為《道德經》不得早於《莊子》,所以,我們可以肯定《莊子》思想不是來自《道德經》,但我們不能排除《道德經》的自由主義來自《莊子》的可能性。而《韓非子》的干涉主義,與其說是來自《老子》,毋寧說更接近《黃帝四經》。《道德經》的思想,以“南面之術”為根本,而兼取《黃帝四經》及《莊子》觀點,但主流在《黃帝四經》,因此有“黃老”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