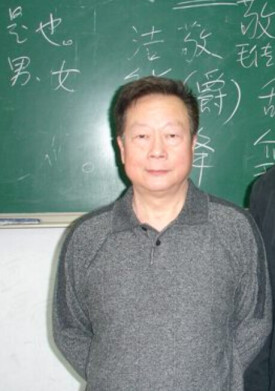共找到6條詞條名為楊天宇的結果 展開
- 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 中國香港男演員
- 主持人
- 陶瓷藝術家
-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 中國第八支駐海地維和警察防暴隊副隊長
楊天宇
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徠楊天宇,男,1943 年12月 -2011年7月,安徽安慶人。
1964年在安慶市一中以安徽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
1968年北大畢業后先生來到河南工作。
1978年先生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南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朱紹侯先生。
楊先生1981年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1992年底調入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2001年系所合併后一直在鄭州大學歷史學院任教。
2011年7月17日凌晨四時三十五分因病去世,享年68歲。
主要側重從古文獻、特別是《三禮》與古史的結合上,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尤其側重於中國古代禮文化的研究。本方向已形成以博士導師楊天宇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年富力強的學術研究群體,已招收和培養過多屆碩士研究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楊天宇教授曾出版學術著作3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獲省部級優秀學術成果獎多項,現正承擔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
出版《周禮譯註》等專著多部,在《文史》、《史學月刊》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近 50 篇,主持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多項,多次獲獎。楊天宇先生是經學史專家,故其秦漢史研究偏重於儒學史、經學史、文化史。先生多年來傾心於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禮學之研究。其所撰《論鄭玄〈三禮注〉》一文,深入探討鄭玄《三禮注》的注經方法、體例及其得失,該文發表在《文史》第21輯。2000年又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鄭玄三禮注研究》,階段性成果已顯示該項研究之周密性與功力之深。唐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提出“禮是鄭學”之說,清人陳澧、今人李雲光(台)於此都有很好的闡釋,然猶未盡也。先生的《略論“禮是鄭學”》(《齊魯學刊》2002年期)一文在此基礎上,深加討究,指出此說原因有三:一因鄭玄禮學著作甚多,特專精於禮學;二因自鄭玄兼注《三禮》,始有所謂《三禮》之學;三因鄭玄能將其禮學付諸實際運用,為朝廷制禮;四因鄭玄能以禮律己,“非禮不動”。不唯如此,該文還發人所未發,指出了“禮是鄭學”的根本原因,即:自鄭玄兼注《三禮》之後,後世之治禮學者皆以鄭氏為宗,而不可舍其書,自魏晉至隋唐皆然。《關於〈周禮〉書名、發現及其在漢代的流傳》(《史學月刊》1999年4期),從文獻學的角度,詳細探討了《周禮》一書的名稱由來、發現及在漢代的流傳情況,指出《周禮》原名《周官》,改名只是在王莽居攝年間的事。確認此書是河間獻王從民間收集而得,獻給朝廷后隨即藏入密府,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書才重新發現。王莽居攝時立學官。東漢時,由於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加上鄭興、鄭眾、賈逵、馬融等到一班大儒的提倡,此書得大行於世。而鄭玄貢獻尤大,他注《三禮》,列《周禮》於《三禮》之首,遂成為東漢古文經學的一面旗幟。《鄭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學學報》2001年5期),在前人的基礎上,簡明概括地敘述了鄭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人論世。在近年關於漢代經學研究中,今古文經學關係問題亦是熱點之一。漢代今古文之爭的性質,學者或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學術宗派之爭,或以為是圍繞增立博士而爭,或以為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這些說法雖有道理,但未將兩漢加以區分。先生的《略論漢代今古文經學的鬥爭與融合》(《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2期)一文則指出兩漢今古文之爭性質絕不相同,即西漢是利祿之爭,東漢是學術道統之爭。所爭並非那麼激烈,僅在《左傳》而已。二者融合,既有政治基礎,即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的;亦有學術基礎,即古文經學家多通人。鄭學的出現標誌著漢代傳統經學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終完成。《鄭玄論著目錄考》(《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2期)一文,則在前人的基礎上較為詳盡地考訂了鄭玄的有關論著。
此外,先生的研究還包括漢代禮制方面,如《略論漢代的三年喪》(《鄭州大學學報》2002年5期),該文首先追述三年喪始於商周,但到春秋戰國時已很少有人實行。接著從漢文帝臨終時所制短喪詔談起,歷述武帝時即有服三年喪的情況,到西漢後期服三年喪的漸多,東漢遂成風氣。概括地指出漢代統治者的政策詔令雖有前後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總地來說卻是持鼓勵、支持的態度。最後探討漢代服三年喪的風氣、統治者所持積極態度的原因在於漢代盛行經學,而東漢統治者特別提倡名教禮法。從而清楚地揭示了“三年喪”這一禮制的淵源、在漢代的變化及其原因。在經學與政治關係方面,我國史學界大多認為,在西漢末年今古文經學的鬥爭中,王莽是古文經學的後台,王莽的篡漢和改制,主要是利用古文經學作為理論武器。楊天宇先生所撰《論王莽與今古文經學》一文(《文史》第53輯),從王莽篡漢與今文經學的關係、王莽改制與今古文經學的關係兩個方面糾正了這一片面性的說法。文章認為王莽篡漢利用了西漢中其以來今文經學所製造的種種理論,如漢運中衰當讓國傳賢易姓受命說、漢為堯后當火德之運說、陰陽災異和符命讖記之說等。而王莽改制的依據大體有三個方面。其一,緣舊制而加以變更;其二,出其心裁;其三,根據經義。以上三方面往往交錯而用之。其根據經義者,或用今文經傳,或用古文經傳,或雜用今古文經傳,而更多的還是依據的今文經傳。所以本文的結論是:今古文經學在王莽新朝享有同等被重視的地位,兩者並不存在“對抗”問題。還有《劉秀與經學》(《史學月刊》1997年3期),論述了劉秀與東漢初年經學恢復的關係及重要意義。文獻學方面,如《論〈禮記〉四十九篇的初蓽確為西漢戴聖所編纂——兼駁洪業所謂“〈小戴記〉非戴聖之書”說》(《孔子研究》1997年1期),該文確證《禮記》初本確為西漢禮學家戴聖編纂,駁正了洪業幾成定論的誤說,即“《小戴記》非戴聖之書”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