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話
南通及所轄縣市方言
南通話流傳於南通市區及通州區西部,南通舊稱通州,地處長江入海口北岸,東臨黃海,南臨長江,西接泰州,與蘇州隔江相望,經濟較為發達。南通大部從前為江口海域,南北朝時始成沙洲,叫壺豆洲(即胡逗洲),南通話是在這個小島上融和了吳方言及海陵方言以及其它方言所形成的一種島語,是毗陵片吳語向泰如片江淮官話的過渡方言。南通方言有廣義及狹義之分,廣義指南通及所轄縣市的各種方言,狹義的單指南通話。
南通市地處長江三角洲,南與滬、蘇、錫、常吳語區隔江相望,北接江淮平原,與泰、鹽、揚、淮比鄰。南通成陸后曾居“流人”,唐宋以來人口流徙,給南通帶來了講各種方言的居民,他們長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際,逐步形成既含有吳語底層成分,又帶有北方方言基本性質的南通話。
除了方言的融合之外,古今語言的演變也是造成南通話特殊性的一個根本性原因。由於南通環境的相對封閉性,現代南通話與中古音有其特殊的對應規律。
由於南北融合,八方人口雜處,現代南通話往往一字多音,有音無字,或字面的意思與字義沒有關係。
南通話的內部差異較小,但與普通話的差異則較大。南通話的聲母只有平舌音,沒有翹舌音,韻母中只有后鼻韻母,沒有前鼻韻母,也沒有前響複合母音。
南通話有7個聲調,其中包括陰入、陽入兩個人聲調。而規律整齊、明顯,所以南通人學講普通話並不困難。
在南通的範圍內,歷史上曾有名叫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東洲、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這些沙洲從西北向東南漸次並接,與大陸相連,便形成了南通這塊平原(即江海平原)。
近2000年內,有三次大的並接。第一次約在南北朝後期到隋唐之際,扶海洲等沙洲與大陸漲接為今如東縣境;第二次在唐末到五代初,胡逗洲與其西北的陸地連接,為今南通市市區和通州區西部;第三次約在北宋初,東布洲等沙洲與大陸連接,位置在今啟東市東部,后又大部份坍沒;第四次在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江口海域中的惠安沙、連升沙等沙洲形成,陸續與北岸並接,為今海門、啟東兩市的南半部分。南通市市區原是胡逗洲。胡逗洲最早見於《梁書》關於“侯景之亂”的記載,南北朝時,東魏大將侯景投降了南方梁朝,後來東魏與梁通好,梁欲以交出侯景為條件換回被東魏俘虜的將領,於是,梁太清二年(548),侯景起兵叛梁。侯景的叛軍攻陷梁都城建康(今南京),向四周擴展勢力。不久,梁朝將領王僧辯、陳霸先聯合向侯景發起進攻,梁承聖元年(552)梁軍收復建康,侯景兵敗向東方逃竄,在滬瀆(今上海西部)乘船準備向外海竄逃。座船離岸后,侯景蒙頭睡覺,這時他的部下羊鵾命水手把船轉向上游,駛向京口(今鎮江)。船行到胡逗洲時侯景醒來,他發現航向不對,立即叫船靠岸。他找來岸上的人詢問情況,岸上的人告訴他,有南兗州刺史兼北台太尉郭元建駐在廣陵(今揚州),侯景想去投奔他,與部下發生了爭執。羊鵾等人擊殺了侯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公元六世紀中期,胡逗洲已得到開發,洲上的居民與西邊的廣陵信息相通。
唐時的胡逗洲,已是一塊位於長江口北側約有1600平方里左右的大沙洲,沙洲上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流人”,他們多數從事鹽業生產,因而洲上設有生產鹽的亭場。北宋初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中有比較明確的記錄。
胡逗洲形成后長江在這裡分流,沙洲與大陸間有一寬闊的泓道。其北岸大致在西起如皋江安,東經白蒲到掘港的一線上,南岸大致在平潮經劉橋鎮到石港一線。泓道直到唐末才漸漸淤塞,北宋初它成為一條東通大海的“小江”,還留有一些小湖,西有車馬湖,東有高陽盪。
胡逗洲與大陸漲連后,便不再是沙洲了。然而原來沙洲上居民的語言比較獨特,即南通話。這種方言流行的區域較小,大致在石港、劉橋一線向南,達南通市區,平潮向東至金沙一帶的範圍內。這種南通話和海門、啟東一帶的語言不同,也與如皋、如東一帶的方言迥異,儼然一個“方言島”。這種方言外地人幾乎聽不懂,那是由於胡逗洲與大陸長期相隔,來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方言。

南通話
大約從公元4世紀起,在長江口黃海上相繼出現了扶海洲、胡逗洲(壺豆洲)、南布洲、布洲、東洲等較大的沙洲。其中扶海洲約在南北朝後期即與江北大陸漲接,這就是今方言天的如東縣地。胡逗洲(壺豆洲)即是今天的南通市市區、郊區及通州市西部地;南布洲約當今通州市金沙鎮以東至三餘鎮五甲苴(jiē)一帶;布洲則約當今啟東市北部呂四港鎮迤南一帶;東洲在布洲以南,其地已坍沒,約當今海門市東南部和啟東市西南部。根據文獻記載,六朝梁元帝承聖元年(公元552年)時,壺豆洲上即有流人煮鹽為業。所謂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這些沙洲,隋時屬海陵;唐初為鹽亭場,屬揚州廣陵郡。唐開元十年(公元722年)設置鹽官,屬揚州海陵縣,隸淮南道。
到了公元8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於軍事上的需要,始在狼山駐軍,狼山成為浙江西道管轄下的一個軍事據點,胡逗洲及附近島嶼也就成為浙江西道常州轄地了。唐乾符二年(公元 875年),於胡逗洲置狼山鎮遏使,設防務機構,屬浙西道節度使節制。由於這些島嶼改屬常州管轄,從這時起,流人便多來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興、無錫、江陰一帶了。他們帶來了 古代常州一帶的吳語,並與原先島上通行的江淮方言接觸、融合,形成了新的具有一定江淮話特色的吳語。公元10世紀初,胡逗洲與南布洲連成一片,始稱靜海洲,整個沙洲的範圍向東擴展到大致今海門市包場鎮一帶。唐末,軍閥姚存制據靜海、東洲(東布洲)二洲,為東洲鎮遏使。姚存制卒,其子廷硅代之。唐亡,姚轉向楊吳,姚廷硅任東洲靜海軍使,長江口上島嶼即成了楊吳之地。大約即在此前後,靜海洲與北岸砂嘴漲接。長江口上島嶼轉屬楊吳后,引起了江南地區吳越國的不安。公元908年、913年和918年,吳越和吳(楊吳)兩國曾4次進行 了爭奪長江口島嶼的戰鬥,這些島嶼最終為吳所據,東洲、靜海洲也就成為淮南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轄地了。
公元937年(吳天祚三年)南唐代吳,立靜海都鎮制置院,姚廷硅子彥洪為東洲靜海都鎮遏使。後周顯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周師克淮南,取南唐長江以北地,姚彥洪眼看在這兒再無立足之地,便帶著家屬、軍士等一萬多人離開靜海投奔吳越去了(《十國春秋》、《資治通鑒·後周紀》)。姚氏為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其軍士亦多吳興子弟,姚氏三代統治長江口上島嶼長達半個世紀,軍士和家屬人數逾萬,因此,古吳興方言必定對當時人數並不多的這些島上的方言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是,吳興與常州兩地毗連,方言大體相 近,因此,島上方言並未發生根本變化。
後周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升靜海都鎮為靜海軍,屬揚州,旋改為通州,析其地為靜海、海門二縣。由於靜海洲與大陸漲接並改屬海陵郡管轄,靜海人與江南人的交往日減,而與江北海陵,尤其是與其毗連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漸頻繁,同時也有大量的海陵人來往於兩地之間,有的甚至定居這裡。海陵,作為這一帶的行政、經濟和文化中心,海陵方言自然也成了這一帶的優勢方言,因而對靜海方言產生了重大的影 響,最終導致了靜海方言由吳語向江淮話的轉化,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南通方言——一 種具有許多吳語特點的江淮官話。而海門島直至公元11世紀中葉(宋慶曆、皇祐間) 始與通州東南漲接,在古代交通相對閉塞的情況下,其居民與島外來往比較少,因而方言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始終保持了吳語的特色。
南通話,即通行於南通市區以及通州區中西部的方言,比較特殊。當代語言學家魯國堯教授認為南通方言是“官話方言中最特殊、最有學術價值的‘’。將南通話定為官話,主要是因為中古全濁塞音、塞擦音在南通話中都變成了清音。換句話說,南通話無全濁聲母。又因為與南通話相鄰的吳語是有全濁聲母的,因此南通話不屬於吳語。既然南通話界於吳語與官話之間,不屬於吳語的南通話,自然就被定為了官話。然而,南通話究竟是否是官話,學術界仍然頗有爭議。
魏建功先生最早注意到南通方言的特殊性。他在1925年發表的《吳歌聲韻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5年第1期)一文中論述江蘇方言區時指出:“南通系:這一所地方的語音甚為特別,既不與其東南方面蘇松太系相同,又不與其西北鎮揚系相同。”。
1956年,張拱貴教授提出了南通方言是江淮官話的主張(《江蘇人怎樣學習普通話》,1956);1960年袁家驊等編撰的《漢語方言概要》也將南通方言歸入江淮官話範疇。
1960年出版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根據50年代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的材料,將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分為4個區,南通方言屬其中第3區。屬於這個區的有泰州、泰縣、泰興、靖江、興化、東台、大豐、海安、如皋、如東、南通等地方言。很顯然,該書將南通方言歸入江淮官話範疇。
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編製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即根據此觀點繪製了有關江淮官話的方言地圖。泰如片的名稱顯然是取自泰州、泰興、泰縣(今姜堰)、如皋、如東的地名首字,這個名稱的缺點顯而易見,它不能確切地反映方言的分佈特點。1988年,南京大學魯國堯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一書中將這一片方言稱之為通泰方言。
美國新澤西州州立大學漢學家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教授發表了題為《南通方言、杭州話跟吳方言的比較》的論文,作者以16條分類準則對南通方言、杭州話跟典型的吳語蘇州話和道地的官話方言河北昌黎方言,以及江淮官話姜堰方言等進行了比較,得出了南通方言是官話方言的結論。儘管大多數語言學家趨向將南通方言列為官話,但在語言學界一直存在著爭論,以致1986年在重慶開會討論《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辭彙集》的編寫方針時,與會的專家對南通方言是否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即官話)發生意見分歧。因為它不符合傳統的官話標準,比方說入聲的存在問題、平仄分流問題。
魯國堯最早提出了通泰方言與贛語、客家話的相似之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中古全濁塞音、塞擦音在通泰、贛、客家話中,不論平仄,都變成了送氣塞音、塞擦音。這與官話的“平送仄不送”有別;2. 入聲分陰陽的通泰、贛、客家話中,陽入調值一般高於陰入調值,這與吳語有別。據此,魯國堯提出通泰、客、贛方言同源的假說。魯國堯也注意到了通泰與徽方言的相似處,他說:“客、贛方言在南方山區連成一片,而通泰方言孤懸於長江以北、運河之東、黃海之濱,相距遙遠而如此一致,不能不引起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再看看贛方言北邊的徽方言,古全濁聲母,大多數地方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都念送氣清音。看來這四個“全送氣”的方言形成了對古老的吳方言與閩方言的包圍圈”。
敖小平全面分析了環吳語地帶各方言的語音相似處,提出通泰方言與徽語的同源可能性。綜合南通的歷史、地理、語音、辭彙等特點,敖小平提出南通方言很有自身特點,她與環吳語地帶方言關係密切,是具有古越語底層的,且又融合了多種方言的一種克里奧爾語(混合語)。
根據《南通方言考》(敖小平,2017),南通話(市區口音)共有聲母39個,韻母33個(不含介韻合母),聲調7個,其中舒聲5個,入聲2個。詳見下列表格:
| 雙唇 | 唇齒 | 齒齦 | 齒齦后 | 齦齶 | 硬齶 | 軟齶 | 聲門 | |
| 塞音 | p(幫) pʰ(旁) | t(端) tʰ(透) | k(街) kʰ(開) | ʔ (安) | ||||
| 鼻音 | m (明) | n (泥) | ŋ(矮) | |||||
| 擦音 | f (非) ʋ(微) | s (審) | ʃ (西) | ɕ (修) | x (海) | |||
| 塞擦音 | t͡s (照) t͡sʰ(草) | tʃ (雞) tʃʰ (欺) | t͡ɕ (專) t͡ɕʰ(穿) | |||||
| 邊音 | l (來) | |||||||
| 半母音 | w (王) | j (影)ɥ (潤) |
註:/p,pʰ,m,t,tʰ,l/ 有齶化變體/pʲ,pʲʰ,mʲ,tʲ,tʲʰ,lʲ/; /tɕ,tɕʰ,ɕ,k,kʰ,x/ 有圓唇變體 /tɕʷ,tɕʷʰ,ɕʷ,kʷ,kʷʰ,xʷ/;/j,ɥ,w,ʋ/可為介音。
南通話共有韻母33個,不包含介韻合母。
| 單母音 | 鼻化母音 | 鼻音韻尾 | 喉化母音(入聲) |
| a 歹 | ɑ̃ 膽 | aŋ 董 | aʔ 不 |
| ɛ 特 | ɛ̃ 等 | ɛʔ 德 | |
| ɔ 打 | ɔʔ 答 | ||
| e 斗 | ẽ 兩 | ||
| ə 倒 | əŋ 領 | əʔ 吃 | |
| o 馬 | õ 黨 | oʔ 福 | |
| i 低 | ĩ 點 | iŋ 影 | iʔ 一 |
| y 油 | ỹ 端 | yŋ 軍 | yʔ 月 |
| ʒ̩ 以 | |||
| ʒ̩ʷ 魚 | |||
| z̩ 子 | |||
| ʋ̩ 五 | |||
| u 餓 | ũ 敢 | uʔ 佮 |
註:/ə/ 有兒化變體 /ɚ/。/uʔ/字發音有城鄉區別。六橋以內的老城區南通話發/uʔ/音的只有佮;而城郊地區有大量/uʔ/音字,如 鴿、屋、合等,此類字的母音在老城區都是/oʔ/
南通話平、去、入分陰陽,古全濁上聲大多併入陽去,陽入調值高於陰入。各聲調具體調值在不同文獻中有些許不同,這裡採用《南通方言考》測算的調值。
| 調類 | 陰平 | 陽平 | 陰上 | 陰去 | 陽去 | 陰入 | 陽入 |
| 調值 | 31 | 35 | 55 | 42 | 313 | 53 | 5 |
| 例字 | 梯 | 提 | 體 | 替 | 地 | 踢 | 迪 |
一般疑問句句法:南通話一般疑問句句法與南京話、蘇州話比較接近,都是再謂語動詞前加上疑問小品詞(particle),或疑問標記。該疑問小品詞的發音為[ku]。因其無實在語義,只表示疑問的句法功能,故無所謂本字,權且用同音字“果”代之。舉例:
| 南通話例句 | 普通話對應翻譯 |
| 老虎果能上樹? | 老虎能上樹嗎? |
| 他果會說南通話? | 他會說南通話嗎? |
| 你果吃韭菜? | 你吃韭菜嗎? |
普通話一般疑問句可有兩種形式,一是重複謂語動詞(如,他會不會說南通話?);二是在句末加“嗎”(如,他會說南通話嗎?)。這兩種形式不存在於南通話中,南通話只能在謂語動詞前加“果”(如,他果會說南通話?)。南通話的這種句法結構或與普通話重複謂語動詞的句法結構比較接近。根據黃正德的分析,一般疑問句作為一個曲折短語(INFL),有一個疑問特徵[+Q]。這個疑問特徵可通過移動並複製謂詞來核查(check),或通過直接加“果/阿/個/可”之類來核查。普通話採用的是第一種核查方法,南通話、蘇州話之類的方言是採用的第二種。
“子,兒”詞綴:南通話“子,兒”詞綴分曲折語素和派生語素兩種。曲折語素“子,兒”或為小稱詞綴(或小稱詞綴的虛化)。比如:狗子,凳子,猴兒,筷兒等。曲折語素“子,兒”的往往成互補分佈,用“子”的地方,往往不能用“兒”。比方說,“狗子”不能說成“狗兒”,“猴兒”不能說成“猴子”。從而可見,南通話曲折語素“子,兒”的分佈與普通話“子,兒”詞綴的分佈是不太一樣的。
南通話的“子,兒”也具備派生功能。通常是將形容詞,動詞變成名詞。比如:痴子,瘋子,蠻子,侉子;這幾個例子中的 痴、瘋、蠻、侉都是形容詞,加上“子”以後變成名詞,表示具有某種特徵的人,比如“痴子”就表示具有“痴”這個特徵的人。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形容詞加“子”以後都是指某一類“人”。然而,也並不是所有單音節形容詞都可以通過加“子”變成名詞。“好子”,“壞子”就不可以說。“矮子”可以說,但是“高子”就不可以說。另外,“子”也可以跟在謂詞短語後面,比如“討飯子(討飯的人)”。“兒”也具有變形容詞為名詞的能力,但是情況和“子”大有不同。比如:彎彎兒,尖尖兒,方方兒,圓圓兒,條條兒。這裡的形容詞必須重複,且形容詞都是只能形容物體形狀的辭彙。加“兒”以後表示具有某種形狀的物體,比如“彎彎兒”表示彎的物體。除了形容詞,“兒”也可以加在動詞後面,變動詞為名詞,其規律和上面說的基本相同。比如:“叫叫兒(哨子)”,“楷楷兒(橡皮)”,“招招兒(帽檐)”,“猜猜兒(謎語)”。這裡,詞根動詞也要重複,然後再加上“兒”。重複動詞詞根也是強制性的,比如猜謎語,就必須說成“猜”。
“進行-持續體”標記“賴下”:普通話的句法,進行和持續這兩個語義需要兩個不同的標記。比如“雪還在下著。”其中“在”表進行,“著”表持續。方言中往往沒那麼複雜。南通話里的“賴下”就兼有進行和持續之意。比如:雪還 賴下落。就表示下雪這個事件正在進行,且會持續下去。故而“賴下”可稱為“進行-持續”體標記(aspect marker)。南通話里沒有“著”這個放在動詞后的標記。南通話不可以說“落著雪”,一定要說“賴下落雪”。這種句法結構也存在與蘇州話和上海話中。
南通地區濱江臨海,處於江淮方言區與吳方言區交錯地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境內各地成陸時間的差異、江海的伸縮、洲陸的漲沉、居民歷史來源的複雜性、行政建置的變化,再加上天災戰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造成了一帶方言種類多樣、方言分佈錯綜複雜、獨特奇異的狀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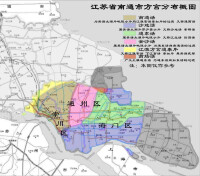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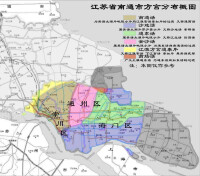
南通話
在語系、語族分佈上,南通地區漢語方言均屬漢藏語系漢語語族;在具體方言大類分佈上,南通地區處於吳語和江淮官話的交匯處,地處東南的海門區、啟東市及由此向北的如東縣、海安市少數臨海地區,講吳語啟海話;地處西北的如皋市與如東縣、海安市的絕大部分地區,講屬於江淮方言如皋話;而南通話則界於啟海話和如皋話之間。使用南通話的包括崇川區北部和通州區的興仁鎮、石港鎮、劉橋鎮、平潮鎮等地的大部分地區。
從性質上講,南通話屬江淮方言。在南通話與啟海話之間,還有一個狹小的過渡地帶——通州區東南與海門接壤的二甲鎮、余西古鎮等地區,講“通東話”,它的聲、韻、調系統已與典型的吳語大相徑庭,而帶有某些南通話的特徵。

南通話
南通方言有其特殊性,它在漢語方言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通過對南通方言歷史演變的研究,可以解讀南通地區的歷史、風俗、地理、文化特點和底蘊,這些現象已引起美國、日本、韓國等一些外國漢語方言學者以及國內一些方言專家的注意。
在南通方言中,南通話最為特殊。南通成陸后曾居“流人”,唐宋以來人口流徙,給南通帶來講各種方言的居民,他們長期共同生活、互相交際,逐步形成既含有吳語底層成分,又帶有北方方言基本性質的南通話。由於南北方言的滲透融合,南通地區的方言異常複雜、特殊。從東南部(啟東、海門)起,經通東向西至南通城區及其周圍地區。
然後,一支由東(興仁)向北(石港),再向如東、海安東部,另一支向西(平潮)向北(劉橋),再向如皋及如東、海安西部,遠及泰、鹽、揚、淮,吳語的影響逐漸減弱,而江淮方言的特徵逐漸明顯。而南通話作為二者的結合點和分歧點,在漢語方言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學術研究意義。它是一種混合了北方方言和吳方言底層成分而與北方方言親緣關係更密切的,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長期發展,形成較為獨特的方言。
2018年1月15日更新
| 作者 | 年份 | 書名 | 出版單位 | 備註 |
| 敖小平 | 2017 | 南通方言考 | 上海辭書出版社 | |
| 江蘇語言資源資料彙編編委會 | 2015 | 江蘇語言資源資料彙編 | 鳳凰出版社 | |
| 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2015 | 南通市志·語言篇 | 中華書局 | |
| 陶國良 | 2007 | 南通方言詞典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
| 史皓元、石汝傑、顧黔 | 2006 | 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
| 鮑明煒、王鈞 | 2002 | 南通地區方言研究 | 江蘇教育出版社 | |
| 顧黔 | 2001 |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 | 南京大學出版社 | |
| Chen, M. Y. | 2000 | Nantong: Stress-foot and p-word In Chen, M.Y. ,Ed.,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Vol. 92,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語料、分析來自敖小平博士論文《南通方言的語音和音系》 |
| 南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2000 | 南通市志·方言卷 |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1998 | 江蘇省志·方言志 | 南京大學出版社 | |
| 孫錦標 | 2000 | 南通方言疏證 | 中華書局 | |
| 管勁丞 | 1983 | 南通方言俚語彙編 | 南通博物苑 | |
| 邵磐世 | 1959 | 南通人學習普通話手冊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
| 蔡觀明 | 1962 | 南通方言疏證訂補 | 未刊 稿本藏南通市圖書館 | |
| 孫錦標 | 1913 | 通俗常言疏證 |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 |
| 作者 | 年份 | 論文名稱 | 所在單位 | 國家 |
| 吉川雅之 | 1999 | 江蘇南通方言的研究 | 京都大學 | 日本 |
Ao, Benjamin Xiaoping (敖小平) | 1993 |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Nantong Chinese (南通方言的語音與音系) |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學) | 美國 |
| 作者 | 年份 | 論文名稱 | 所在單位 |
| 宋佩佩 | 2016 | 啟海話與南通話的語音比較研究 | 上海師範大學 |
| 李文靜 | 2014 | 南通方言語氣副詞研究 | 南京大學 |
| 孫秋香 | 2014 | 南通話“果x”問句探索 | 渤海大學 |
| 瞿晗曄 | 2013 | 金沙方言語音研究 | 南京大學 |
| 沈婷 | 2013 | 南通話修辭研究 | 揚州大學 |
| 陸觀 | 2012 | 南通市區居民語碼轉換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 | 南京林業大學 |
| 張璐 | 2011 | 南通話的音韻 | 蘇州大學 |
| 熊英 | 2010 | An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akers’ Choices–a Case Study of Nantong Dialect (從說話者選擇的角度探討語言瀕危現象–以南通話為例) | 南京大學 |
| 陳信璋 | 2008 | 南通方言音韻研究 | 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新竹) |
| 陳俐 | 2006 | 南通話詞法研究 | 南京師範大學 |
| 張穎煒 | 2005 | 南通話程度副詞研究 | 上海師範大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