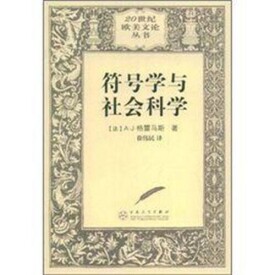奇幻符號學
奇幻符號學
“奇幻符號學”目前尚未被學界正式提出或討論。就目前的現狀而言,國內處於起步階段,而國外尚無較為完整的理論建構,這是一個尚屬前沿的符號學領域。
“什麼是符號?”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很多符號學家認為,符號無法定義。趙毅衡給了符號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15000至20000年前古人就在岩石上留下人、動物等圖形符號,所展示的信息現在還沒有人全部解開。
符號就是人特有的最原始的用於交流且有記錄的人的行為。符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斷地適應人的思想領會,並能留下記錄的非語言有目的的表露。
趙毅衡在1993年就把符號學定義為“關於意義活動的學說”。
沒有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不僅人無法存在,“人化”的世界無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只有用符號才能思想,或者說,思想也是一個產生並且接收符號的過程。因此,認識論、語意學、邏輯學、現象學、解釋學、心理學,都只涉及意義活動的一個方面,而符號學是對意義的全面討論。因此把符號學定義為“意義學”是能夠成立,也有用。
迄今為止,學界尚無“奇幻符號學”的提法及相關術語。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必須先對這個名稱作一界定。
首先,何謂奇幻?要想嚴格而清晰地界定“奇幻”這一類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Mark C. Glassy在試圖界定科幻類型時不得已耍了滑頭。他說:“科幻文學的定義正如同情色文學的定義:你不知道它是什麼,但當你看到它時你就會明白。”儘管西方奇幻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之前,如神話、中世紀文學及浪漫主義文學等,但現代意義的奇幻卻發生於20世紀。現代奇幻作家如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托爾金(J. R. R. Tolkien)、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等都從創作的角度為奇幻做了界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托爾金的觀點,他認為“奇幻文學必須創造一個和現實世界完全無關的另一個世界的真實,這個世界應當涉及或者包含各種‘仙境故事’(fairy-story)中才會存在的事物,例如矮人、女巫、龍、魔法等等。據此,包含幻想事物卻以現實時空為背景的作品以及描寫夢境、運用幻想手法的創作都被排除在了奇幻文學之外。
結構主義批評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為奇幻做了一個近乎苛刻的定義,他認為,“奇幻就是當一個只知道自然法則的人在面臨超自然事件時所體驗到的猶疑(hesitation)。”這裡的“猶疑”指作品中的人物及讀者在面對超自然事件時所產生的徘徊的情緒,“不知道自己所面臨的是現實或是夢境、真相抑或幻覺”。托多洛夫認為,一旦作品中的人物或者讀者在真與幻之間做出了任何選擇,那麼這部作品便滑向了另外兩個不同的類型——怪誕(uncanny)或者奇迹(marvelous)。文學史家及批評家曼勒(C. N. Manlove)認為奇幻是“能夠喚起驚奇(wonder)的,包含大量充實的和不可化約的超自然成分的作品,同時作品中的普通人或者讀者對這些成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熟悉”。拉賓(Eric Rabkin)為奇幻做了比托多洛夫更加包容的定義,他認為“奇幻的一個關鍵的區別性的標誌就在於,由敘述世界的基本法則構築出的圖景會被(人物及現實中的讀者)直接質疑”。由此,他將托多洛夫所認為的奇迹(marvelous)也歸入奇幻一類。
中國奇幻的源頭也可追溯至上古神話、六朝志怪、唐傳奇及明清神魔小說等,而具有現代意義的奇幻創作則體現在20世紀武俠小說的興起,一直發展至今天的“新神話主義”創作。葉舒憲認為中國化奇幻的內涵“最早是融合了神話故事、歷史傳說、武俠情節三大元素而形成的新式現代神幻小說”。進而葉舒憲還提出“新神話主義”的概念,他認為新神話主義“是20世紀末期形成的文化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世紀之交西方文化思想的一種價值動向。它既是現代性的文化工業與文化消費的產物,又在價值觀上體現出反叛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生活,要求回歸和復興神話、巫術、魔幻、童話等原始主義的幻想世界。其作品的形式多樣,包括小說、科幻類的文學作品,以及動漫、影視、電子遊戲等”。韓雲波認為“幻想文學和幻想文化的核心意義,在於創造並展示一個‘第二世界’的別樣時空,並由此表達與現實世界不一樣的理想主義追尋與超越性體驗”。陳奇佳認為,“奇幻小說最吸引人的一個地方,就是故事發生的世界背景是架空的,甚至與這個現實世界沒有一點關係。作者在現實的人類生存世界與人類發展歷史之外,開闢出了一個完全屬於個人虛構的平行時空。這個平行的時空有自己獨立的山川地貌、人文歷史、生物種族、智慧生命、物理法則等等。它們與我們的現實世界沒有什麼關係,既不受現實世界的影響,也不與現實世界有什麼直接聯繫。奇幻小說家在構擬其想象世界的時候,似乎有意與現實世界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消解其作為自然的參照元的影響力”。
縱觀各家對於奇幻的定義,表述不一,但首先都在奇幻與其他類型的幻想之間劃了一道界線,以區別於一般的虛構文學。比如,按照托爾金的定義,施蟄存與徐訏的小說雖然描寫了怪異的景象,如鬼、夜叉等超自然存在,但卻不能歸為奇幻名下,因為故事仍舊發生在現實時空里。而按照托多洛夫的觀點,老舍的《貓城記》或者沈從文的《阿麗絲中國遊記》等也不能算作奇幻,因為現實投射的影子過於濃重,讀者產生的審美感受不在猶疑與驚奇。同時,這些定義也體現出奇幻的核心理念,即重在建構一個異世界,營造出這個想象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疏離感,產生現實與幻境之間若即若離的審美張力與快感。綜合各家觀點,並與奇幻相鄰近的科幻(science fiction)與恐怖(horror)文類相區別,筆者認為可以將奇幻定義為:包括大量實在的、自明地存在於“第二世界”的超自然成分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及讀者在面臨這些超自然事件時會產生驚奇及猶疑的審美感受。加上“自明”,意為不需要解釋,尤其不需要現代科學原理的解釋,以區別於科幻文類;引起“驚奇”和“猶疑”,而非恐怖,以區別於恐怖文類。實際上,奇幻與科幻、恐怖同屬推理文學(speculative fiction)大類,是無法徹底區分的。因此,奇幻下面也存在眾多亞類,如注重架空世界構築的主流奇幻(high fantasy)、與科幻嫁接的科學奇幻(science fantasy)、與恐怖嫁接的黑暗奇幻(dark fantasy)等等。
奇幻符號學,雖然國內外的學者在研究奇幻這一類型時已涉及符號學的原理,但迄今為止並未出現“奇幻符號學”這一術語,也沒有一套系統的理論體系。可以說,這是一個亟待整合和創新的領域。趙毅衡為符號學做的界定是:“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符號學即意義學。”那麼,我們可以將符號學理解為研究意義的發生、傳播及接受的學科。相類似的,我們也可以為奇幻符號學下一定義,即以奇幻文本為研究對象的符號學,主要研究奇幻文本意義的產生、傳播及接受。奇幻符號學意義何在?趙毅衡認為,批評理論從二十世紀初發展到現在已經極為豐富,如今可分為四個支柱體系: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心理分析和形式論。“它們共同的取向,是試圖透過現象看底蘊,找出事物的本質,找出現象的深層規律。”其中,形式論是“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產物,至今已對當代批評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符號學原本是形式論的一個派別,由於其理論視野開闊、可操作性強等特點,在六十年代之後成為形式論的集大成者,被廣泛應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被稱為“文科的數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公分母”。探索奇幻世界架構的規律、虛擬世界與實在世界的關係、虛構的本質、奇幻文學意義的傳播與接受等問題,符號學正是一把利器。而目前對此領域的研究還遠未鋪展開來。國外研究起步較早,但對歐美奇幻文學研究多,極少涉足東亞文化,並且迄今仍未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國內研究剛剛起步,且缺少利用符號學深入探索的理論自覺。我國擁有豐富的奇幻文化資源,當代的奇幻文學創作也方興未艾,此時更加需要理論的支撐與引導,這正是一個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這是一個大問題,可以從多個角度、多個主題切入討論奇幻符號學,可以涵蓋符號學的符形學、符義學、符用學等多個分支。在本文中無法詳細論述,單從奇幻文學的核心問題世界建構入手,提出幾條研究線索。既然奇幻文學創作的核心理念在於異世界的建構,在審美體驗方面注重實在世界與虛構世界的疏離與交疊,那麼從世界建構入手研究奇幻文學,必然能切中它的實質。
意義不在場的時候才需要符號,我們必須探究,是什麼促生了奇幻文學的虛擬世界?這涉及到奇幻文學的認識論意義,時代不同,認識論的意義也不同。如果說遠古的奇幻文學如《山海經》主要緣於人類對於自然的不可知的敬畏,其後在佛家與道家思想的影響下出現了對現實世界的投射與反思,形成《西遊記》、《鏡花緣》等寓言性的寫作,而對於當代奇幻文學如武俠及“新神話主義”創作的態度體現了現代人對世界認識的根本性偏差。啟蒙理性的一個顯著的後果就是經驗世界與超驗世界的斷裂,現代人的認識論框架局限於經驗世界,從而排除一切非經驗性真理。當代奇幻文學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反思理性主義,試圖超越經驗“現實”,恢復人們對超驗世界的意識,以幫助現代人擺脫物質世界的限制,獲得一定意義上的超脫。
在討論可能世界理論時,趙毅衡提出,“虛構世界是心智構成的,是想象力的產物,因此虛構文本再現的世界是是一個‘三界通達’的混雜世界”,即一個由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和實在世界共同構築的世界。討論世界建構,必須釐清三界之間的關係。世界建構(world building)即指擁有一套哲學理念,創造出一個既明顯區別於現實世界但又有現實世界投射的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的過程。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要借用到可能世界和倫理學的理論。文學中的可能世界被視為區分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區分標識,奇幻文學的核心即在於可能世界的建構,成為區別於傳統模仿敘事的鮮明特徵之一。借用可能世界敘事學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探討奇幻文學的虛構本質。此外,必須認識到,無論作家如何虛構,幻想中的世界建構與實在世界的關係必須以倫理關係為立足點。倫理關係是維持物理世界劇變張力的根本,虛構世界即是藉由此錨定於實在世界。
每一個試圖建構一個奇幻世界的作家所必須面臨的一項龐大工程便是為他的世界命名。在一些基本的世界構成要素,如時空、地理、歷史、種族等等,被確定下來之後,一個難題便是如何去指稱它們,使它們在稱謂上便遠離實在世界,鍍上“奇幻”的色彩。一部構築繁複而精細的奇幻著作,甚至使作者感到有必要專門為其再繼續創作一部索引,用以解釋其中的分類與命名,如托爾金的《魔戒》。那麼,究竟這些命名是如何確定的,而讀者又是怎樣去理解的呢?模態邏輯語義學家克里普克(Saul Kripke)在《命名與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書中提出了“歷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論”。他認為一個名稱指稱某個對象,並不取決於這個對象具有某種特殊的識別標記,只是根據對象的某些偶然特徵把指稱對象固定下來,而人們則藉助於某些與這個名稱有關的歷史事實去指稱某個特定的對象。
借用這一理論去探索奇幻世界的命名,我們將會有兩個發現。首先,這些“奇幻”的命名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均有來自歷史和同時代理論思潮的支撐,而越是時間靠後的奇幻作品,歷史的痕迹則越是明顯,比如我們並不難發現《山海經》對於當代奇幻文學在命名方面的影響。其次,如果進一步探究這些命名的分類與含義,我們會發現云云種種的奇幻名稱背後的元語言集合卻有相似之處,或者說,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比如,在中國式奇幻中經常會出現仙境、魔界、凡間與鬼蜮的時空分野,而命名也與這些時空歷史性地呼應。
細節飽和度是構築奇幻世界的核心問題,即如何使讀者感受到並且相信這是一個“世界”。
首先,文本聚合軸“極寬幅”特徵。文本蘊含的細節量是形成飽和度的前提。文本世界必須擁有自己獨立的山川地貌、人文歷史、生物種族、智慧生命、物理法則等等。而幻想的思維特徵則決定了在文本構築的聚合層面上形成“極寬幅”,思之所及,文之所有。
其次,局部細節飽和。細節飽和度是現實世界區別於可能世界的特徵之一。無論怎樣增加可能世界的細節量,永遠無法與現實世界的細節飽和程度相匹敵。但可能世界卻能夠通過局部細節量的渲染與飽和而顯得“真實”。
再次,感受之全域性。如何使讀者感受到一個全域性的世界是奇幻作品成功的關鍵之一,將讀者的意圖定點落實於“世界”的本質是奇幻文學的根本任務。由此,我們便可以解釋,為什麼一部設計繁複、細節密度大的巨著可以構築世界(如《西遊記》),而“一沙一世界”也可以傳達出“世界”的意味。
這是奇幻文學意義得以實現的關鍵,也是奇幻文學獨具魅力之所在。明人評介《西遊記》這部打破中國寫實風格通俗文學創作的著作時有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可見明人已開始了對虛構文學作品之“幻”與“真”的辯證思考。奇幻文學的作者著力建構一個與現實世界疏離的異世界,其作偽意圖是明顯的,而作者偏偏要利用各種手段營造出“虛幻中的真實”,吸引一開始“假戲假看”的讀者進入一個“誠意正解”的格局,所謂“雖然框架是一個虛構的世界,這個世界里卻鑲嵌著一個可信任的正解表意模式”,即“虛構文本必須在文本主體之外,構築另一對文本主體,它們之間能做一個‘事實性’文本的傳達”。作者便藉由此完成了虛構中的述真,讀者(理想讀者)沉浸在這個虛幻的世界里,達到“逼真性”的審美體驗,並在超越日常經驗以及對現實世界的認知中了解到另一層“真實”,實現了此世界與彼世界間的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