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西夏學的結果 展開
- 雜誌名稱
- 歷史學科
西夏學
歷史學科
西夏學(Tangutology)是一門研究西夏文獻和歷史的學科,是20世紀初興起的新興學科。西夏學涵蓋面廣泛,涉及古代黨項與西夏國歷史、地理、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諸多領域。西夏學發展至今,在語文、考古、社會歷史三大基礎性板塊學科的建設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秋,在甘肅武威城內東北隅清應寺封閉已久的碑亭中,學者張澍開掘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斷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標誌著西夏遺物以及文字的發現,從此揭開了研究西夏文物的大潮。
自20世紀初,由於外國探險家在黑城遺址發掘出大量西夏遺書,從而使西夏學研究不僅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也成為國際化的學科。新中國成立后,各院校研究西夏學的現象不斷發展,各類著述不斷問世。
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西夏建立后,先與遼、宋,后與金鼎足而立,必然與周邊政權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保義二年(1227年),西夏被蒙古滅亡,其文物典籍遭受嚴重破壞。元朝修遼宋金史,獨不及西夏,使有關文獻史籍散亡。歷經元、明兩代,黨項這一民族共同體及其所建立的王朝逐漸隱沒,被後世淡忘。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嘉慶十五年(1810年)秋某日,在甘肅武威城內東北隅清應寺封閉已久的碑亭中,武威學者 張澍開掘出西夏崇宗李乾順於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斷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張澍成為第一個識別出西夏文字的學者。另一位清代學者鶴齡則首次釋讀了《妙法蓮花經》的西夏文經名與卷數名。19世紀初,中國學者對西夏歷史的研究以及西夏文字的重新發現,開創了西夏學研究的先河。
20個世紀初,原西夏時期的邊防重鎮黑水城(位於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但卻被俄羅斯、英國的探險家偷運出境,分散到了俄羅斯、英國、法國、日本等地,我國老一輩西夏學學者對這些珍貴文獻無緣一見,因為手頭的資料極為缺乏而難以進行深入、系統、全面的研究。

《番漢合時掌中珠》
除了羅氏父子之外,1917年,戴錫章以前人的編年史書為基礎,撰成《西夏紀》28卷。甘肅臨夏鄧隆(1884-1938)對西夏文感興趣,是一位西夏文研究者,在1929年以前,著有《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西夏譯華嚴經入法界品考釋》、《西夏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考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等。
繼羅氏父子之後,從1930年到1933年,王靜如先生先後發表了《西夏研究》1-3 輯,其主要部分是佛經的對譯考釋,並涉及到黨項與西夏的歷史、語言、國名、佛經雕版、官印等諸多領域,此書因榮獲法國儒蓮獎金而著名於世。1929年秋,北京圖書館購得寧夏發現的西夏文佛經百卷,刊出《西夏文專號》以資紀念,其中收錄國內外西夏學者撰寫的西夏歷史、語言文字、文物考古、文獻目錄、佛經等論著資料約40種。
黑城西夏遺書被劫持國外后,大量資料秘而不宣,加之漢文西夏史料的缺乏,這一時期,中國的西夏學研究暫時處於相對的沉寂狀態,報刊雜誌上只有零星的關於西夏歷史文化的簡短介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20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的西夏研究幾乎是空白,由於民族平等政策的貫徹執行,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注意研究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像四川大學吳天墀先生默默進行著西夏史研究的學者鳳毛麟角。六十年代初,老一輩西夏學家王靜如先生又開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並招收研究生,培養新一代西夏學研究人才。出版了有關西夏的專著,並發表了一些有關西夏歷史的重要文章,如唐嘉弘《關於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楊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金寶祥《西夏的建國和封建化》,胡昭曦《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等,引起了學術界對西夏歷史的關注。1964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聯合組成敦煌西夏資料工作組,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諸窟群的西夏時期的歷史文物遺存進行了全面的考察,確定了近百座屬於西夏時期修鑿和裝鑾的佛教石窟,發現了百餘條西夏時期存留的漢文和西夏文題款。從此舉世聞名的敦煌石窟也成為西夏文物與藝術珍品的寶庫。
總體來說,這一時期學習與研究西夏學的人非常少。七十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1972年至1975年,寧夏博物館對銀川西夏王陵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出土了大批建築構件、金銀飾物、竹木雕刻、絲綢織物以及鎏金銅牛、妙音鳥等珍貴文物;1983年至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漢文文獻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獻。此外,寧夏、甘肅、陝西、內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廟、佛塔、窖藏。還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錢幣、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畫、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發現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李範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濱、吳峰雲)、《西夏文物研究》(陳炳應)、《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李逸友)、《西夏陵》(許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潤澤、於存海、何繼英)、《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彭金章、王建軍)等著作。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獻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國學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開,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同音研究》(李範文)、《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類林研究》(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西夏諺語》(陳炳應)、《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濱、聶鴻音譯)、《宋代西北方音》(李範文)、《夏譯<孫子兵法>研究》(林英津)、《聖立義海研究》(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貞觀玉鏡將研究》(陳炳應),《夏漢字典》(李範文)。其中,《夏漢字典》是我國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學習和研究。

吳天墀
1993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三方達成正式協議,共同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獻,出版后必將會對西夏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大批研究者投身於西夏研究的隊伍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寧夏、四川、甘肅等研究中心,我國台灣省與香港也有專門從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學者,西夏學研究已步入繁榮興盛時期。
到了20世紀七十年代初,認識西夏文的專家,就只剩下兩三個人了。近年來,由於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支持和有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積極努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夏文獻陸續在國內出版,與西夏學有關的出版、研究還被列為國家重點出版計劃和重點研究課題,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很多專家學者過去朝思暮想、可望而不可即的文獻,現在都變成了隨意可讀的普通讀物,而有關高校、科研機構富有成效的系統整理和基礎性研究,又為專家們深入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集中反映西夏學最新研究成果的《西夏學》,已被正式列入核心期刊,西夏學的春天真的來到了。
早在2009年,建在西夏故都的寧夏大學便順勢而為,在學校原有西夏學研究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夏學研究院,承擔起西夏學研究、西夏學人才培養和國際學術交流等多重任務。2010年,他們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聯合,成立了中俄西夏學聯合研究所。而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則成為全國關注的學術品牌和各地學者期待的盛會,對舉辦地的文化事業、學術研究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港台地區也有一些學者從事西夏學研究。1975年香港林旅芝教授自費出版了《西夏史》,全書分為17章,1-12 章,論述西夏興亡;13-16 章,論述西夏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地理、兵制、宗教等;17 章為結論,書後附錄了張澍的《西夏姓氏錄》。是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才為大陸學者所見。還有林瑞翰的《西夏史》論文,羅球慶的《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闕鎬曾《宋夏關係之研究》,廖隆威《北宋與西夏的貿易關係》《宋夏關係中的青白鹽問題》等論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王民信發表了《西夏孫子兵法》《西夏官名雜考》《宋夏金錢外交》《范仲淹與李元昊》《王安石與西夏》《宋與西夏的關係》等一系列關於西夏的論文,並且還發表了評價大陸研究西夏文字專著的文章等。
1883 年,俄國的漢學家伊·比丘林(И·Вичулин)在聖彼得堡出版了《公元前2232-公元1227年西藏和青海的歷史》一書,該書與義大利人馬可·波羅的《遊記》、波斯人拉施德的《史集》及《多桑蒙古史》等著作,皆有關於對西夏故地、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記載。

科茲洛夫
60年代以後,西夏學在蘇聯又得到發展,出現了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索夫洛諾夫(蘇敏)、格列克、卡津、孟列夫、克平、捷倫捷也夫-卡坦斯基、科洛科羅夫、魯勃、列斯尼欽科夫等一批專家學者,並且研究重點也從語言文字轉向對西夏歷史、文化、政治、軍事、經濟、地理、宗教、風俗、服飾等多領域、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克恰洛夫成績最為突出。早在1959年就已發表《西夏國家機構》《中國史料中關於唐古特人的民族學資料》等論文,來北京大學學習后,又完成了《西夏國史綱》一書,對黨項的起源、發展,西夏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西夏的經濟、文化、民族等均有論述,但由於對西夏文文獻與漢文典籍理解的艱難,致使出現諸多誤譯與誤解之處,影響到作者論斷的正確性。
近年來,他對西夏法典、詩歌、諺語、格言、佛經等進行譯著,出版了如《天盛改舊鼎新律令》《俄藏西夏文佛經總目提要》等一批專著。孟列夫是專門從事西夏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的學者,從1957年開始,孟列夫參加整理漢文文獻,並撰寫出《黑水城發現的早期出版物》等論文。又在前人編目的基礎上,對這批黑水城漢文遺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分類、編目以及敘錄,著出《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一書。其中包括佛、道、儒學典籍、文學、歷史著作、文書、曆書、醫書、占卜等書,這些均為研究西夏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法律、文化、藝術、科技以及民族關係的寶貴資料。愛米塔什博物館的薩瑪秀克長期從事西夏繪畫藝術研究,撰寫出《黑水城的發現》《西夏王國的藝術歷史風格上的詮釋》等論文。
日本西夏史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是日本西夏史研究興起和發展時期。早期的西夏史研究主要是對西夏文字的研究。1898年,著名的漢學家白鳥庫吉發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920年-1922年,石濱純太郎發表了《西夏學小記》,后又與聶斯克合著《西夏地藏菩薩本願經》《西夏國名考補正》《西夏語譯大藏經考》 等論文,1956年,又對西夏草書進行研究,撰寫出《西夏語譯呂惠卿孝經考》 。20世紀30年代,日本中島敏發表了《西夏》《西夏對西羌的戰爭》《關於西夏銅錢的製造》《關於西夏鑄錢問題》《西夏政局的變遷與文化的推進》等一系列論文,對西夏的政治、經濟、戰爭、貨幣均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長部和雄的《西夏紀年考》 、宮崎市定的《西夏興起與青白鹽問題》 、小林照道的《關於西夏佛教研究》等,對西夏紀年、貿易、佛教也均有所注意。
第二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至近期,是日本西夏史研究有較大發展時期,湧現出一批從事西夏研究的學者。山本澄子在40 年代研究的基礎上,又發表了《五代宋初黨項族及其西夏建國之關係》,藤枝晃的《李繼遷之興起與東西交通》,松田政一的《關於西夏黑水城的調查》等論文。前田正名非常重視西夏的河西地區,撰寫了《河西史的基礎構造》《吐蕃與河西九曲》《西夏時代避離河西的交通路線》《關於五代宋初的六穀地區構造論考》等一系列論文,並撰寫出專著《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岡崎精郎早在 1947 年就已發表了《唐代黨項的發展》等關於黨項西夏的文章,50年代開始發表了《西夏建國過程之研究》《關於西夏法典》《關於西夏原始信仰》《五代時期夏州政權的發展》《西夏之李元昊與禿髮令》《關於西夏民族信仰》《宋初的二三禁令問題到李繼遷之興起》等一系列論文,其代表作是70年代完成的《唐古忒古代史研究》 ,前田正名為其作序,高度評價了這一研究成果。
韓國學者在研究遼、金史時才涉及對西夏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申采發表了《北宋仁宗時對西夏的政策》和《宋西夏貿易考》等論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金渭顯發表了《契丹對西夏的政策》《西夏與宋契丹之關係(986-1048)》等論文。另外還有林志君的《北宋對外經濟關係與華夷觀——以遼、西夏關係為中心》,安俊光的《對於宋夏戰爭》和《對於宋夏七年戰爭》等論文。
19世紀後半期,外國學者對北京居庸關六體石刻文中的一種民族文字展開了討論,這種文字五百餘年無人辨識,1870年,英國的學者偉烈亞力(A.ylia)考證為“女真小字”。1882年,法國學者德維利亞(Mr.Devieria)根據開封發現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與之不同,提出反駁。1895年,法國學者蓬拿帕特(P.R.Bonaparte)所編的《蒙古金石圖錄》里收錄了居庸關六體石刻文,但是對其中的西夏文仍然不識。直至1898年,德維利亞看到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后,才發表了《唐古特或西夏王國的文字》一文,確定居庸關六體文中的“女真小字”實為西夏文字。1904年,法國駐華使館毛利瑟氏(M.G.Morisse)在中國學者鶴齡譯註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發表了《西夏語言和文字的解讀》。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洲的西夏學研究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1948年,在第21屆國際東方學會上,法蘭西學院石泰安(P.A.Stein)發表了《彌葯與西夏》的論文演講,1955年又在《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EFEO)第4卷上發表了《彌葯與西夏——歷史地理與祖先傳說》,從藏文、西夏文、漢文、英法文等文獻中的有關西夏的資料,進行旁徵博引,探討彌葯與西夏的關係,從而對黨項族源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研究。1961年出版了《漢(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一書,對彌葯族源問題又多有涉及。1966年發表了《有關木雅與西夏的新資料》一文,結合藏文資料對聶斯克選譯的《夏聖根讚歌》進行了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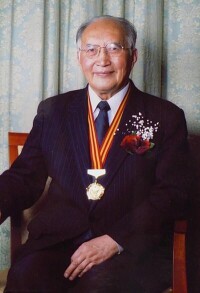
李範文
西夏學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史金波、陳育寧、牛達生、湯曉芳、聶鴻音等老一輩專家學者老當益壯、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杜建錄、孫繼民、李華瑞、彭向前、楊浣、段玉泉等中年學者已經扛起了大梁,成為西夏學研究的中堅,而二三十歲的西夏學碩士、博士隊伍更是不斷壯大、迅速成長,呈現出西夏學後繼有人的喜人景象。尤其可喜的是,一些研究宋史、遼史、金史及研究敦煌學、吐魯番學等相鄰、相近學科的專家,也紛紛加入到西夏學研究的隊伍中來。對西夏的音樂、美術、醫方、天文曆法、西夏文書法,甚至算命學都有人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有些研究則深入到過去很少有人涉足的領域,其研究細緻入微,精深獨到,已入“無人之境”。
在西夏文獻資料出土的地方——阿拉善盟舉辦的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雖然是第五屆了,但沒有絲毫衰落、懈怠的跡象,相反卻顯得生機勃勃。
1996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后更名東方文獻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
到21世紀初,出土文獻整理出版成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等單位相繼推出《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獻》,北方民族大學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獻》《日本藏西夏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也相繼出版。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為西夏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首先,西夏文獻專題研究全面展開。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學聯合為基礎,出版《西夏文獻研究叢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開展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叢書》和多卷本《西夏文物》。寧夏大學組織出版的《西夏研究叢書》,也有不少文獻研究成果,加上沒有納入上述叢書的成果,有數十種之多,如聶鴻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傳>研究》《西夏文獻論稿》《西夏佛經序跋譯註》,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語比較研究》,林英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註釋研究》,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克恰諾夫、聶鴻音《西夏文<孔子和壇記>研究》,孫繼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考古發現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韓小忙《<同音文海寶韻合編>整理與研究》《<同音背隱音義>整理與研究》,杜建錄、史金波《西夏社會文書研究》,孫伯君《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西夏文獻叢考》,杜建錄《黨項西夏文獻研究》(合著)、《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合著)、《黨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獻論集》(主編),胡玉冰《傳統典籍中漢文西夏文獻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楊浣《他者的視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佟建榮《西夏姓氏輯考》《西夏姓名研究》,潘潔《黑水城出土錢糧文書專題研究》,束錫紅《黑水城西夏文獻研究》,杜建錄、波波娃主編《<天盛律令>研究》,段玉泉《西夏<功德寶集偈>跨語言對勘研究》,楊志高《西夏文<經律異相>整理研究》,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胡進杉《西夏佛典探微》等。有的文獻研究比較深入,如利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資料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幾種。
西夏歷史考古和語言文化研究進一步深入。西夏歷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有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西夏美術史》,杜建錄《西夏經濟史》,王天順主編《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干問題探索》,湯曉芳《西夏藝術》,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周偉洲《早期黨項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會》《西夏文化研究》,李範文主編《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書校補》,湯開建《黨項西夏史探微》,李錫厚、白濱、周峰《遼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劉復生、張邦煒、蔡崇榜、王曾瑜《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李華瑞《宋夏史研究》,楊蕤《西夏地理研究》,張迎勝《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楊浣《遼夏關係史》,陳育寧、湯曉芳《西夏藝術史》,魯人勇《西夏地理志》,於光建《神秘的河隴西夏文化》。西夏文物考古方面,寧夏文物考古研究相繼推出《閩寧村西夏墓地》《拜寺溝西夏方塔》《西夏三號陵——地面遺跡發掘報告》《山嘴溝西夏石窟》《西夏六號陵》。此外,牛達生《西夏遺跡》《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錢幣研究》《西夏考古論稿》,陳育寧、湯曉芳、雷潤澤《西夏建築研究》,黎大祥、張振華、黎樹科《武威地區西夏遺址調查與研究》,加上前述多卷本《西夏文物》,較大推動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深入發展。
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張竹梅《西夏語音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教程》、韓小忙《西夏文的造字模式》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龔煌城的西夏語音研究代表國際水平,史金波的《西夏文教程》是國內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極具實用性。
西夏文字數字化方面,繼馬希榮《西夏文字數字化方法及其應用》之後,又有多家文字書版系統問世,隨著聶鴻音、景永時西夏文國際編碼的完成,西夏文的排版系統將更加方便快捷。
西夏學一度成為“絕學”。1972年,周恩來總理到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察時獲悉,全國能辨認西夏文的僅有幾位老人。為此,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當即對學習研究西夏文做出明確指示。如今,昔日幾成“絕學”的西夏學已經變成“熱學”。國內各地相繼成立了研究機構,湧現一批著名西夏學專家,產生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寧夏大學,先是創辦了“西夏語言文字研修班”,接著又成立了西夏學研究中心,去年又成立西夏學研究院。現在,西夏學研究已成為教育部重點學科,得到中央和自治區有關部門的重點扶持。
西夏學研究是中俄兩國共同關注的學術領域。中俄學者對西夏學的合作研究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推出西夏文專號,伊鳳閣、聶歷山等俄羅斯西夏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羅福成等中國學者的文章,一同出現在這期專號中。這一階段主要是兩國學者個人間的聯繫與交往。
中俄學者真正具有實質意義並取得豐碩成果的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將俄藏黑水城文獻陸續公之於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對此記憶猶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常務副院長汝信對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非常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為合作整理出版這批文獻提供了資金支持。經過艱苦的談判,中國學者終於踏上了艱苦而充實的文獻整理之路。
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獻》開始推出。目前仍在陸續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為西夏學成為顯學奠定了文獻基礎。2009年,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學合作研究機構——中俄(俄中)西夏學聯合研究所,合作研究從專家個人、研究單位上升到國家層面,研究內容是在西夏文獻整理出版基礎上的深入研究,研究範圍除俄藏西夏文獻外,還包括中國藏、英藏、日藏、法藏西夏文文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