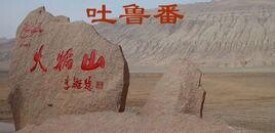西域佛教
西域佛教
佛教沿不同路線向各地傳播過程中,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經歷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受所傳入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倫理觀念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已不復為初傳時“原始佛教”的狀貌,在徠各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域呈現不同的特點。西域是佛教北傳過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傳播史上佔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國佛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上所指之西域,並無一定之範圍,且西域諸國之名稱亦隨時代轉換而屢有改變。佛教史上之西域,系指從印度興起佛教后,由陸路東傳中國所經之地區,大抵即西元前三世紀大月氏統領下之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分、迦濕彌羅、今旁遮普一部分、安息國勢力範圍下之波斯北部、康居國勢力範圍下之下底栗弋(Sagdiana)等。而諸國中,與佛教有關者,蔥嶺以西有月氏(今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亞南部)、犍陀羅(今阿富汗之干達馬克)、罽賓(即迦濕彌羅,今北印度喀什米爾),蔥嶺以東則有於闐、斫句迦(今莎車東南)、龜玆(今庫車)、疏勒(今喀什噶爾)、高昌(今吐魯番)等。其中以犍陀羅與罽賓兩國最重要。
西域佛教之興盛始於西元前二六○年頃,阿育王曾派遣摩訶勒棄多(梵 Maha^rakkhita)、末闡提(梵 Majjha^ntika)至此地傳教。摩訶勒棄多主要佈道於印度西北之希臘殖民地臾那國(Yona),復擴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闡提則在犍陀羅、迦濕彌羅等地布教。佛教於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紀,高昌甚至奉為國教,彼時即西域佛教之鼎盛期。
在此之前,佛教已經由西域東傳我國,而西域諸國古德名僧亦入我國傳譯經典,如安息之安世高、曇無諦、安法賢、安法欽,月支之支婁迦讖、支曜、支謙、法護、支法度、曇摩難提、支道根,康居之康巨、康孟詳、康僧鎧、康僧會、曇諦,龜玆之帛延、帛屍梨密、帛法炬、佛圖澄、蓮華精進,罽賓之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僧伽羅叉、曇摩耶舍、弗若多羅、卑摩羅叉、佛陀耶舍、求那跋摩等。
自西元二世紀至五世紀,西域教派多屬小乘,彼時盛行小乘者有疏勒、罽賓、犍陀羅;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為主流者有安息、康居、龜玆,惟信大乘者為子合(即大唐西域記所載斫句迦,當今蔥嶺以東瓦罕山谷一帶),盛行大乘者另有高昌、於闐等。五世紀以後,犍陀羅因無著(梵 Asam!ga)、世親(梵 Vasubandhu)二大乘學僧之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之趨勢。隨著佛教之流布,佛塔、雕刻、繪畫等佛教藝術亦因而發達,佛像多以泥土、漆灰為原料,佛畫以壁畫為主,樣式則多為融合希臘、羅馬、印度三種精神之犍陀羅系統,此外亦有回鶻式(多於吐魯番附近)、喇嘛式。七世紀以後,中國美術色彩漸濃,遺物多在吐魯番一帶。至於其取材範圍,則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觀音、文殊等菩薩,繪畫以賢愚經、六度集經等之故事為對象。經典之編纂、書寫、翻譯亦極盛行,僅高昌、於闐二地,即有中阿含(優婆利經)、小部經藏(法句經數葉)、般若(大品般若十數葉、金剛般若)、秘密(無量門陀羅尼、大白傘蓋咒)、大積(月藏分、寶幢、日藏分、賢護分)等二十餘種為後人發現。
隋唐之際(七世紀),穆罕默德創回教於大食,以兵力行教,馬蹄所至,佛教盡為所滅,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濕彌羅、犍陀羅、疏勒、於闐、龜玆、高昌等國佛教,先後於佛入滅后七百年至二千一百年(三國至明代)間,為祆教、回教浸淫吞併,西域佛教從此絕跡。
近代各國學者至東土耳其斯坦探險考古之風甚盛,經多次至庫車、和闐、吐魯番、喀喇沙爾、敦煌千佛洞、烏魯木齊、羅布諾爾等地挖掘,遂有佛像、佛畫、經典及其他文化遺物之出土,使西域文物之研究有長足進步。(史記大宛列傳第六十三、唐書西域列傳第一四六、漢西域圖考、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第四十三至第七十三、西域之佛教、中央亞細亞探檢の經過とその成果、西域佛教の研究(羽溪了諦,宗教研究特輯號)、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參見:迦濕彌羅國)3978、“犍馱羅國”5522)p2581
西域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頗為重要,地處東西方交通樞紐的西域不僅在早期佛教傳播過程中起過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汲取諸種民族文化影響,形成極富特色的西域佛教藝術,從石窟的開鑿、寺廟的建立,到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等等,在許多方面都對中國漢地佛教、藏傳佛教產生巨大影響。但作為宗教信仰的佛教本身在西域最終卻走向沒落。
由於缺乏史料記載,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賀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譯者序》中所說:“西域諸國和古代印度一樣,都沒有什麼歷史記載遺留下來,只有中國和古代希臘的文獻中有些記錄,中國正史的外國傳和漢、晉、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遊記,這些正史記載和僧徒記行與近百年來在印度、中亞和新疆一帶新發現的資料和遺物互相參證,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動,才得漸次明了。”
佛教藝術隨著佛教的傳播傳入西域,所到之處的繪畫、雕刻、建築、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明顯受到佛教的影響,並在吸取外來文化的基礎上融合本土特點,經過長時間的演變,逐漸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
中國學術界對西域、中亞等地的佛教藝術研究關注的重點有以下內容:佛教寺廟、石窟建築、佛像、雕刻、壁畫等佛教藝術遺存及其與印度、犍陀羅、希臘、伊朗乃至中國中原等地區諸文化因素的關係。
20世紀早年中國學術界有關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較少,遠遠不及日本學術界。主要成果是譯介日本的兩部研究專著,其一為[日]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24],其二為[日]羽田彥著、錢稻孫譯《西域文明概論》[25]。前者著力從史地角度論述佛教在中亞和土耳其斯坦的傳播與發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內容非常少,是一部關於西域佛教史方面的名著。後者對西域佛教的發展狀況亦有精闢論述。早年中國學術界研究專著有蔣維喬《佛學史綱》[26]、《佛學概論》[27]、《中國佛教史》[28]和黃懺華《中國佛教史》[29],但均以日本人的著作為藍本,少有創穫。
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佛教史研究取得較大進展,作為中國佛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前文提到的重要佛教史論著如任繼愈的《中國佛教史》、呂澄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郭朋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和《隋唐佛教》,以及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30]等著作中,均有相當篇幅論及西域佛教興衰史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藝術,對西域佛教不同於漢地佛教的特點,受域外諸種文化因素影響,以及以獨特狀貌流傳下來的西域佛教藝術均發表各自的見解。
進入90年代,出現了有關西域佛教史研究專著。楊富學《回鶻之佛教》[31],探討了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及其特點,回鶻佛典的翻譯、回鶻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廟的興建、佛教寺院經濟、佛教對回鶻文化的影響等內容。魏長洪《西域佛教史》[32],著重闡述了佛教在西域的傳播與發展,側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內在變動,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時代和民族中的特點及其消滅狀況,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層次的布局和結構。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綜論》[33]一書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傳播及其發展”,主要論述了貴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傳播與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歷史文化狀況,利用中外文獻,對古代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佛教的興衰與發展進行了詳細的考述。
有關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論文,研究角度各異,有側重於佛教傳播的,也有關注佛教自身發展情況的。例如,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鶻人中的傳播》[34],簡要論述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維吾爾人中的傳播、興衰以及回鶻文佛經的保存狀況,該文認為佛教早在貴霜王朝丘就卻在位時期即已傳入南疆和田地區。孟凡人《略論高昌回鶻的佛教》[35],認為高昌回鶻始信佛教當在9世紀晚期至10世紀左右,佛教隨著高昌回鶻的興亡而興衰,並一直延續到15世紀中葉左右,高昌地處東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內地佛教文化影響的同時,還受到其它許多地區的影響。宮靜《五至七世紀中葉西域佛教之變遷》[36],對5至7世紀中葉西域佛教變遷狀況及原因進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佛教在新疆南部傳播路線之管見》[37],就當時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結合文獻,特別是唐代前後來往於中國與印度的佛教徒行記,對唐以前和唐宋時期佛教自印度傳入新疆的路線問題進行闡述。
西域佛教源於印度,因此,在對西域佛教及佛教藝術進行追本溯源的探究過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國學者有關印度佛教史的專著不多見,呂澄的成就最大,著有《印度佛教史略》[78]和《佛教史表》[79]、《印度佛學源流略講》[80]。周叔迦有關印度佛教史的論著見於《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上冊)[81]。論文也不多見,如段晴《戒日王的宗教政策》[82],方廣錩《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幾個問題》[83],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此外,還應提到一部藏文漢譯本印度佛教史,多羅那它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84],本書成書於1603年,作者覺囊巴·多羅那它(1575-1634)為西藏佛教覺囊派大德。此書自問世后一直被推崇為研究印度佛教歷史的權威著作。
關於印度佛教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埃利奧特著、李榮熙譯《印度教與佛教史綱》(第一冊)[85],對印度教與佛教的起源、發展、教義等作了系統的介紹,對印度教與佛教之間的差別也作了客觀的闡述。[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86],對貴霜時期犍陀羅藝術有所涉及,書中提到在貴霜時期蘇羅娑和犍陀羅兩個學派之間已經追跡出來有些交互影響,但犍陀羅的藝術逐漸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傳統,經過犍陀羅傳播到中亞和中國。〔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楊曾文、姚長壽著《印度佛教史概說》[87],探討了印度佛教的產生、傳播、發展、滅亡的歷史,對各歷史階段佛教的特點進行分析。
徠在西域佛教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歷史人物。主要包括由歷朝中國政府和南亞各國之間互派的使臣以及致力於傳教求法的僧侶。其中一些使臣和僧侶經過陸上“絲綢之路”達到其目的地,在古代交通極為不便的狀況下,要耗費很長時間,經歷漫長的旅程。但正是由於時間和行程的漫長,使得這些使臣和僧侶對沿途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地理、民族、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有了較深的了解,他們之中有的留下了撰述,成為後世研究西域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
(一)對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中國和南亞既為近鄰,往來頗為密切。其互派使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漢時期,到唐代達到高峰,宋代以後仍比較頻繁。中國學術界研究較多的使臣有西漢時期的張騫、唐代的王玄策、明代的鄭和。其中張騫雖曾派他的副使到身毒國,但其本人並未到達南亞;明代的鄭和走的是海路,因此與本文相關的中國使臣中,中國學術界著力最多的是王玄策。
王玄策(生卒年不詳),唐朝初年曾作為政府的使節三次出使印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所撰《中天竺行記》為親歷親見之記載,史料價值自不待言,該行記宋以後佚,今見殘本存於唐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書中。
20世紀以來中外學術界對他的生平及史跡給予高度評價。早年研究和翻譯著作有柳詒徵《王玄策事迹》[99],馮承鈞《王玄策事輯》[100],[法]列維著、馮承鈞譯《王玄策使印度記》[101]等。50年代以後,有一些關於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論文,主要有陸慶夫《論王玄策對中印交通的貢獻》[102]和《關於王玄策史跡研究的幾點商榷》[103],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104],陰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爾諸問題》[105]等。
孫修身對王玄策的研究最為全面,著有專著《王玄策事迹鉤沉》[106],該書以時間為序,按照事件分類,對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貢獻進行詳盡的考證、評價。
有關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孫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銘〉的研究》[107],對1990年6月發現於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銘》進行了考釋。林梅村結合考古材料和語言研究成果,對《大唐天竺使出銘》進行校釋,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銘〉校釋》[108]。均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二)對西域高僧鳩摩羅什的研究
東晉十六國時期後秦高僧鳩摩羅什(公元343~413年),生於龜茲,其父為印度人,母為龜茲人,被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譯師”之一,同時也是一位宣揚般若三論的思想家。年少時曾隨其母到罽賓等地學習佛法,後來回到龜茲,成為著名的大乘學者。對於他的生平及貢獻,許多中國佛教史研究的論著都有相當多的篇幅加以評述,如任繼愈《中國佛教史》[109]、郭朋著《隋唐佛教》[110]以及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11]等。研究專著有郭朋《鳩摩羅什評傳》[112]。論文有胡戟《龜茲名僧鳩摩羅什傳》[113],丁明夷著《鳩摩羅什與龜茲佛教藝術》[114]、陳世良《鳩摩羅什年表考略》[115]等。
(三)對法顯、玄奘、義凈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自兩漢時經中亞傳入中國,初始時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東來傳法。魏晉以後,中國內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眾。從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義凈,眾多僧人前赴後繼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風。唐末五代,由於中國內亂以及佛教自身發展狀況,求法之事暫告消歇。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復興,傳教求法一事又盛極一時。九世紀后,佛教在印度漸趨衰微,東來弘法和西行巡禮的僧侶人數日漸減少。對於這些情況,梁啟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116]中曾作過精闢論述,文章對魏晉以降中國西行求法僧侶的動機、經行路線、主要事迹、成就、著述進行考證。梁啟超還撰寫《又佛教與西域》[117]一文,對東漢至隋唐東來傳教的僧人的國籍等情況進行了研究。馬雍亦有《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118],該文結合《高僧傳》中有關資料,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熱潮這一歷史現象進行分析,對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賈、貴族、遊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該時期中原、西域與南亞等地的文化交流狀況。
在眾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顯、玄奘、義凈最為著名,貢獻最大,因此他們也是後世學人關注的重點,中國歷代高僧傳記中都記錄了他們的事迹與行蹤,如〔梁〕慧皎撰《高僧傳》[119]、〔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20]等。今人也有為其作傳者,李山、過常寶主編《歷代高僧傳》[121],何茲全主編《中國歷代名僧》[122],張力、黃修明主編《中國歷代高僧》[123],陳作義著《絲路取經人》[124],馬曼麗、樊保良著《古代開拓家西行足跡》[125]等書中,均將他們作為重點人物進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