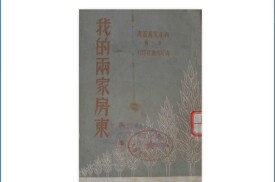我的兩家房東
我的兩家房東
《我的兩家房東》是由康濯編寫的一本小說,主要寫了房東家的閨女金鳳由父母作主,與一個二流子訂了親,后通過政治和文化學習,她提高了覺悟,毅然解除婚約,實現了自由戀愛的願望。金鳳的姐姐有著與金鳳同樣不幸的遭遇,在妹妹的影響下,也走上了同樣的生活道路。
寫於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1946年5月定稿於張家口。小說以1940年晉察冀邊區實行二五減租,開展民主運動,宣傳邊區施政綱領二十條為背景,寫了黨的幹部“我”的兩家房東的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故事,表現出解決區青年男女對自由生活的嚮往與追求,老一代農民擺脫傳統意識桎梏的艱難,以及終將擺脫這種桎梏的歷史趨勢,從而涵蓋了更為深廣的生活層面。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有較鮮明的個性:金鳳的大方與勇決,拴柱的靦腆與執著,金鳳姐姐的憂鬱與深沉,金鳳姐妹的父親陳永年的保守與本分,甚至連小弟弟金鎖的天真與頑皮,都寫得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尤應予以首肯的是,作品較好地寫出了陳永年與金鳳姐姐思想、性格與命運的變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社會解放與人的解放之關係。作家善於通過人物的行為舉止動作表現人物的思想與性格。如反覆寫拴柱對一本字典的心嚮往之,這樣就賦予他與金鳳的戀愛生活以更高層次的內容:他們的戀愛乃是對於一種更新的、更高的生活的追求的一部分,而這又是解放區社會環境給人們提供了實現的可能。而所有這些,又都是以極為親切、樸實的筆法出之,毫無雕琢、做作之處。因而作品也就從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淳樸、清新的藝術風格。
《我的兩家房東》
作者:康濯
“我行李不多!你個幹部,挺忙;冬學又剛開頭,別誤了你的工作!”
他也沒有答應我;他說: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過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著驢,我們就順著河槽走了。
這天,是個初冬好天氣,日頭挺暖和。河槽里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輕輕流著,聲音象敲小銅鑼。道兒上,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我跟栓柱走得很慢,邊走邊談,拴柱連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在我們前面慢慢走著,有時候停下來,伸著鼻子嗅嗅道兒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或是把嘴伸向地邊,啃一兩根枯草,並且,有時候它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好像是等我們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聲,它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談的最多的,是他的學習。他說,我搬了家,他實在不樂意哩!
“往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啦!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
“學習,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再說,這會兒你也不賴了,能自己個捉摸了!”
於是,他又說,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裡去,叫我別忘了他,還得象以前那工夫一樣教你他;他並且又說開了,如今他看《晉察冀日報》還看不下,就又囑託我:
“可別忘了阿,老康,買個小字典……呃,結記著呀!”
“可不會忘。”
“唉!要有個字典,多好啊!”他自己個感嘆起來,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來望我一眼。他們這一灣子的青年們,也不知道在甚麼時俟,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裡,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經過區青救會主任的解說,往後就差不多逢是學習積極分子,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就都希望著買個字典。可是,敵人封鎖了我們,我為他們到處打聽過,怎麼也買不到,連好多機關里也找不到一本舊的;和我一個機關工作的同志,倒都有過字典,可是,他們不是早送給了農村裡來的幹部,就是反“掃蕩”中弄丟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迎面碰上了一頭叫驢,它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不覺不三不四地擠碰起來;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就伸著脖子“喔喔……”嗥叫。拴柱跑上去拉開了牲口,我們又往前走。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甚麼;忽然,拴柱獨自個“吃吃”笑了聲,臉往我肩膀頭上靠了靠,眯著眼問我:
“老康,你真的還沒有對象么?”
“我……我……我甚麼時候騙過你?”我領會了他的話,不自覺地臉上一陣熱,就很快地說。“我捉摸你可准有了吧?”
“沒,沒,可沒哩!”他的臉“唰”地紅了,忙向旁邊避開我,低下腦瓜子笑了笑,機靈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這時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破棉褲脫下了,換了條夾褲,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百團大戰時候他配合八路軍上前線得的一條皮帶,也緊在腰上,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沒有甚麼大事,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啊?他比我還大一歲,今年二十二了哩!照鄉村的習慣,也該著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啊!莫非他真有個甚麼對象,今兒個要去約會么?我胡亂地閃出這麼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准有了對象吧?可不能騙……”
“沒,沒,可沒哩!”他臉上血紅,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擊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說:“快……快……呃,眼看到啦,緊走兩步吧!”
真箇,不大會兒,進上庄村了,我就忙著收拾房子。我從陳永年家院里出來,去牲口上取行李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拴柱忽然那麼忸忸怩怩:他又要給我把行李扛進去,又不動手,等我動手的時候,他可又擠上來幫我扛;他好像是在捉摸著要不要進這個院子似的,還往院里偷望了兩眼,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
房東老太太嚷著:“來了么?”就顛著小腳進了屋子,手裡拿了把笤帚,一骨碌爬上炕,跪著給我掃炕。房東小孩靠著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裡望了兩眼,一下就發現我挎包上拴著的大紅洋瓷茶缸,就跳進來,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膽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鍋旱煙,只有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一會兒又取下頭巾擦擦汗,一會兒叫我一聲,可又沒話……我無意地回眼一望,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
那靠門外站的一個,是我昨天見了的,見我望她,就半低了頭,扯扯衣角,對我輕聲說了句;“搬來了呀?”靠門裡的一個,年歲大些。望我笑笑,還納著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說:
“我……我走…”
“你送他來的么?”
我還沒開口哩!可有誰問拴柱了;是靠門外站的那個婦女,這會兒,她把門裡那個往裡擠了擠,也靠進門裡來了。
“我……我趕集去,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
“你們認識么?”
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個小孩這會兒才轉過身來說:
“他是下庄青救會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說是不是?”
“是就是唄!”那個納底子的婦女隨便說了一句。
老太太掃炕掃完了,翻身下地,拍打著自己的上衣,跟我聊了兩句,就問開拴柱:
“你是下庄的么?下庄哪一家呀?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么?……”
“人家是下庄大幹部哩!青救會主任,又是青抗先隊長!”門口那個年輕婦女,代替拴柱回答她娘;她仰起臉來,可又望著院子里說:“娘,集上捎甚麼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甚麼?”
“人家也趕集去呀!”
“對,我……我得走了……”
拴柱說著,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閃”地一下偷望過去,就支支吾吾走了。當他走到房門口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里,又回頭望了一眼,而那個年輕婦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納底子的婦女這才愣了身旁那個一眼,推著她走了。
趁這個機會,我知道了:這家房東五口人,老頭子五十歲,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歲,小孩叫金鎖,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妹妹叫金鳳。老太婆頭髮灰白了,個子比較高大,臉上也不瘦,黃黃的臉皮裡面還透點紅,象是個精神好、手腳利落、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小孩十一歲,見了我的文具、洗漱用具、大衣等等,都覺得新奇,並且竟敢大膽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裡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嚷著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這物件兒……”
下午,我開會回來,拿了張報紙,坐在門檻上面看。我住的是東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階上面,那兩個婦女都在做針線活。妹妹金鳳,看樣子頂多不過二十掛零,細長個子四方臉,眼珠子黃裡帶黑,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轉動起來,可也“忽悠忽悠”地有神;可惜這山溝里,人家窮,輕易見不著個細布、花布的,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黑布襖褲,褲子邊是補了好幾塊的,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這會兒她還正在補著條小棉褲,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來卻象平三十子年歲了,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可就是眼角邊、額頭上皺紋不少,棉褲褲腳口邊用帶子綁起來了,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她還在納她的底子。我看看報,又好奇地偷望望她們,好幾次可發現金鳳也好像在愉望我;我覺得渾身不舒展,就進屋了。
晚飯後,我忙著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領了些零碎家什,回得家來,天老晚了;我點上燈,打算休息一會。那時節,我們還點的煤油燈,比農民家點的豆油燈亮得多,怕是這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老太太領著金鎖進來了,大閨女還是靠門納底子,金鳳可端了個碗,裡面盛了兩塊黃米棗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邊就翻看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我正慌忙著,老頭子也連連點著頭,嘻嘻哈哈笑進來,用旱煙鍋指點著棗糕說:
“吃……吃吧,同志,沒個好物件。就這上下三五十里,唯獨咱村有棗,吃個稀罕,嘿嘿!”
我推託了半天,就問老頭:
“趕集才回來么?買了些甚麼物件?”
“回來功夫不大!呃,……今兒個糴了幾升子黃米,買了點子布。”
“同志!說起來可是……一家子,三幾年沒穿個新呀,這會兒才買點布,盤算著縫個被子、鞋面啦、襪子啦,誰們衣裳該換的換點,該補的補點唄!唉!這光景可是‘擱淺’著哩!”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一邊打火鐮吸煙,一邊接著老太太的話往下說;
“多撈上兩顆把,也是個不抵!”老太太嘴一翹,眼睛斜愣了丈夫一眼,對我說,“這一家子,就靠這老的受嘛!人沒人手沒手,凈一把子坐著吃的!”
“明年個我就下地!”金鳳搶著說了句。金鎖也爬在娘懷裡說了:
“娘,我也拾糞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沒那個本事!”
“只要一家子齊心干,光景總會好過的!”
我說了這一句,就吃了塊糕。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金鳳忙從口袋裡掏出根紅桿鉛筆來,晃了晃:
“金鎖,看這!”
姐弟倆搶開了鉛筆,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門口靠著的婦女嚷著,叫別誤了我的工作;老頭子才站起來。
“鎖兒!你也有一根嘛,在你娘那針線盤裡,別搶啦!”
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金鳳走在最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叫我給寫上名字,還說叫我往後有工夫教她識字:這麼說了半天才走。我送到屋門口,望望回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覺著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心眼裡高興了。實在說,下庄拴柱那房東,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
往後的日子,我又跟在下庄一樣:白天緊張地工作,誰也不來打攪;黑夜,金鳳、金鎖就短不了三天兩頭地來問個字,或就著我的燈寫寫字。我又跟這村冬學講政治課,跟這村人就慢慢熟識了。有的時候,金鳳還領著些別的婦女來問字,她並且對我說: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喲!要象你在下庄教……教……教拴柱他們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在下庄教拴柱他們?”
“我怎麼不知道呀?”
另外兩個婦女,不知道咬著耳朵叨叨了兩句什麼,大家就嘰嘰喳喳笑開來;金鳳扭著她們打鬧,還罵道:“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有一回,他來的時候,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老太太領著金鎖趕著牲口推碾子去了。他還是皮帶裹腿好裝扮,隨便跟我談了談,問了幾個字,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看;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我好像在哪兒見過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說,一面改,並且讚歎著他的進步。這工夫,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拴柱可又好像滿身長了風疙瘩,周身不舒展起來。
今天,姐姐在做布襪子,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著,還跟往日一樣,不言不語,低頭做活。金鳳是給她爹做棉鞋邦;她可嘻嘻笑著,走近炕桌邊,看拴柱的日記:
“這是你寫的嗎?拴柱?”
“可不!”
“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鳳看他的日記,想用手捂著,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鳳看。拴柱只好用巴掌抹了一下瞼,離開炕邊,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我對金鳳說: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幹部嘛!”
“別說啦,別說啦!”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就問金鳳:
“你學習怎麼樣啦?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看吧!”
“別著急!我這會兒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怕趕不上你?”
“拴柱,我說你怎麼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
我這麼一問,拴柱臉血紅了,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後來,又瞎扯了半天,他又問了問我買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鳳追了上去:
“拴柱!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救會……”
下面的話,聽不清,只好像他們在院子里還嘰咕了半天。金鳳她姐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也往外走。
“我說,你怎麼也不識個字?”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她又嘆息了一聲:
“唉,見天愁楚是不行,沒那個心思……人也老啦!”
她對我笑了笑,就走了。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楚心事啊?她那笑,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似的……說她老么?我搬來以後,還見到過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裡青年婦女們一道,說笑開了的時候,她也是好打好鬧的,不過象二十五六子年歲呀!她……她很象個婦人了,她出嫁了嗎?
那時節,是一九四0年,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大戰,消滅了不少日本鬼子:中國共產黨中央晉察冀分局,還在這年八月十三,公布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冬學的政治課,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雙十綱領”了。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啊!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晚上,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裡來,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她爹也每回來聽,老太太和金鎖也短不了來,連對學習是那麼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偶爾也來聽聽。他們一邊聽,有時候還提出許多問題來;講到深夜,他們好像也不困。有時候金鎖聽著聽著,就趴在娘懷裡睡著了;有時候,他又會站在炕上,抱著我的脖子,一連串問我:“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你見過共產黨么?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逢當這時候,坐在我對面的金鳳,就要瞪著眼橫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她才又靜靜地望著我,眼珠子“忽悠忽悠”地轉著,聽半天,又趴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
這是個平靜的家庭。冬閑時節,女人們做針線,老頭喂餵豬,拾拾糞,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里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做飯、推碾、餵雞。邊區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種的地又減了租,實在說:光景也不賴啊!一個月裡面,他們也吃了三兩頓子白面哩!
可是,憑我的心眼捉摸,這個家庭好像還有點什麼問題:一家子好像還吵過幾回嘴。只是他們並沒有大嚷大鬧,而且又都是在屋子裡嚷說的,我怎麼也鬧不清底細。我問過他家每一個人,大家可都不說什麼,只金鎖說了句:
“姐姐的事唄!”
“姐姐的什麼事?”
“我不知道!”
有一回,我又聽見他們吵了半天,忽然老頭子跑到院子里嚷起來了。我忙跑出去,只見陳永年對著他家北屋,跳著腳,濺著唾沫星子直嚷:
“我……我不管你們這事!你們……你們自已個拿主意吧,我不白操這份心!”
說著,就氣沖沖地往外走去,我問他,他也沒理。北屋裡幹什麼呢?誰抽抽搐搐地不舒展啊?我問金鎖,他說是他大姐啼哭啦!我不好再問,只得回到屋子裡發悶。
不過,他家一會兒也就沒了什麼,好了,又回復平常的日子,我也就不再發急了。
這一天,晌午我給婦女冬學講了“雙十綱領”,晚上,房東們早早地就都來了。我還有工作哩!我說明兒講行么?大閨女卻忽然跟平常不同,笑著說了話:
“就今兒個吧!你講了我們就……”
“講吧,老康同志!”金鳳也催我,我只好講。一看,老頭子沒來,我問了問他是不是要聽?人們都說別管他啦,我就講開了。
今天講的是“雙十綱領”第十四條。我隔三五天講一條,講的日子也不短了!這會兒,已經是臘月初,數九天氣,這山溝里冷起來了,今天早上飛了些雪片,後來日頭也一直沒出來,我覺得渾身涼浸浸的;我把炕桌推開,叫他們一家子都上炕,圍著木炭火爐坐著。房東的大閨女,把手裡的活計擱在大紅柜上,但不上炕,站在炕沿邊,低頭靜聽。老太太的眼一直沒離開我,我說幾句,她就“呵!呵!”念道著;金鳳可有好多問題。今天我講的是關於婦女問題的一條:婦女社會地位啦、婚姻啦、童養媳啦、離婚結婚啦……金鳳就一個勁兒問;“怎麼個才算童養媳啊?為什麼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結婚啊……”她姐姐,也不時抬起頭來,偷偷地望我。
外面忽然颳起一陣大風,“嗚——嗚”地刮著,我的房門沒關嚴實,突地被刮開了,炕桌上的煤油燈火苗也晃了兩下。爬在我大衣裡面睡著了的金鎖,往我身邊更緊地擠了擠,迷胡地哼著:“娘,娘……”我的窗子外面,可好像有個什麼老頭子被風颳得悶咳了兩聲。我忙問是誰,金鳳也突然叫了聲:“爹!”卻沒人答應。房東大閨女關了門,我又說開了。
今天說的時間特別長,金鳳的問題也特別多。他們走了,我實在累了,但還不得不開了個夜車,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胡亂吃了點飯,出去開了個會,回來,房東家已經做午飯了。房東大閨女在北屋外面鍋台邊拉風箱,屋子裡,老太太好像又跟誰在嘀咕什麼。只聽見大閨女忽然把風箱把手一推,停下來,對屋裡嚷:
“娘!你那腦筋別那麼磨化不開呀!眼看要憋死我了,又還要把金鳳往死里送么……你,你也看看這世道!”
屋裡說了些什麼,我沒聽見。我這兩天工作忙一些,也沒心思留心他們的事了。
我們機關里整整開了三天幹部會。會完了,我鬆了口氣;吃過早飯,趁天氣好,約了幾個同志,去村南球場上打球。就在那道口上,忽然看見陳永年老頭子騎著牲口往南去。我好像覺著這幾天他心眼裡老不痛快似的,而且差不多好幾天沒跟他說話了!這會兒,就走上去問了問他:
“上哪去?”
“嘿嘿,看望個親戚!”
看他那模樣,還是不怎麼舒展。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打了會子球,回到家裡,剛進院,房東大閨女就望著我笑;金鳳忙扯著她姐姐的衣角,打她姐姐,她姐姐可還對我笑,我也不自覺地笑起來,問是怎麼回事,金鳳可低著頭跑進屋裡去了。金鎖問我:“你們這幾天吃什麼飯啊?”他大姐也問我:“明兒你們不吃好的嗎?”我說:“這些天盡吃小米!”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又問這?我還是不知道。房東大閨女這幾天不同得多,老是詭詭譎譎地對我笑;而金鳳,見了我就低著頭緊著溜走了。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問字了,也不學習了,連冬學上課的時候,我望她一眼,她就臉紅:這才真是個悶葫蘆!
第二天,我見全鳳捉了只母雞在殺,又見她家蒸白面饅頭:這出了什麼事?而且,這一天金鳳更是見了我就紅著臉跑了,她姐姐還是望著我笑。我憋悶得實在透不過氣來。下午,老太太忽然拖我上她家吃飯去,我嚇得拚命推辭,她可硬拖,金鎖也幫她拖。我說:
“那麼著,我要受批評喲!”
“批評!你挨揍也得去!特地為你的,有個正經事哩!”
我紅著臉,滿肚子憋悶,上了北屋。屋裡,炕桌擦得凈凈的,筷子擺好了,還放了酒盅,金鎖提了壺熱酒過來,老太太就給我滿酒。我慌亂得話也說不出,可忽然聽到窗子外面鍋台旁邊,兩個女人細聲地爭吵起來了:“你端嘛!”“我不!”“你不端拉倒!又不是我的事情!”“吃吃吃”一陣不出聲的笑,象是金鳳她姐。又聽見象金鳳的聲音:“我求求你!”“求我幹什麼?求人家吧!‘吃吃吃’……”“你個死鬼!”於是金鳳腦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端了一大盆菜和饅頭,進來了;她拚命把臉背轉向我,放下盆,臉血紅地就跑了,只聽見外面又細聲地吵笑起來。
老太太硬逼著我喝了盅酒,吃了個雞腿子,才把金鎖嚷出去,對我說開了話:
“那黑夜你不是說過么,老康?這會兒,什麼婦女尋婆家,也興自個兒出主意?兩口子鬧不好,也興休了……呃,你看我又忘了,是……是興離婚么?唉!就為的這麼個事!你……老康,你不知道我是好命苦喲!”
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對面,上半身伸向我,說不兩句,就緊著扯衣角擦眼睛;剛擦完,我見她的眼淚又“撲簌撲簌”往外涌。她狠狠地閉了下眼睛,就更俯身向我說:
“我那大閨女,十六上給了人家,到如今八年啦!她丈夫比她大十歲,從過門那工夫起,公婆制的她沒日沒夜地受,事變啦,還是個打她哩!飯也不叫吃!唉……別說她整天愁楚得不行,我也是說起來就心眼痛哩!閨女,閨女也是我的肉啊!”
老太太又啼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可吃了一驚:那個女人還只有二十四歲!我問了:
“她什麼工夫回來的?”
“打年時秋里就回了,不去了,婆家年時來接過一回,往後就音訊全無,聽說她男人還……唉,還瞞著人鬧了個壞女人哩!可怎麼會想到她?她也發誓不回啦!婆家又在敵區的!”
“那就離婚唄!條件可是不差甚呀!”
我心裡頭早被這些情由和老太太的啼哭鬧得發急的不行,老太太可又說:
“老康,不,先說二閨女吧!大閨女鬧下個這,二閨女差不大點也要鬧下個這!金鳳嘛,今年個十九羅,十四上就許給人家了呀!男的比她大七歲,聽說這會兒不進步,頭秋里鬧選舉那工夫,還被人們鬥爭來哩!那人嘛我也見過,呃……你,你吃吧,老康!”
她又給我滿上酒,還夾了一大塊雞肉:
“人沒人相沒相的,不務莊稼活,也是好尋個人拉個胡話,吃吃喝喝。聽說也胡鬧壞女人哩!頭九月里,也不知道他趕哪兒見著我金鳳一面,就催親了,說是今年個冬里要人過門!金鳳死不樂意,她姐也不贊成,我就一個勁兒拖唄:拖到這會兒,男家說過年開春准要娶啦!你說,老康,這,這可怎麼著?唉,我這命也是……”
“那可以退婚嘛!”
“你說怎麼個?”
“不只是說定了么?這會兒,金鳳自己個不願意。男的年歲又大那麼些,要是男的真箇不進步,那也興退婚,也興把這許給人家的約毀了呀!”
“那也興么?”
“可興哩!”
老太太眼一睜,噓了口白氣,象放下塊大石頭似的,又忙叫我喝酒。我喝了兩口,也鬆了鬆勁,朝門口望望,見門檻上坐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大閨女,半扇門板擋了,看不怎麼真。忽然,我又發現我背後的紙窗外面,好像有個什麼影子在偷聽,就忙回過頭望,於是那個人影子趕緊避開了;我又回過來給老太太說話,可好像覺得窗外的影子又閃回來了。我想起了那天黑夜,為什麼我講到離婚的時候,金鳳她姐直愣愣地看著我。而“雙十綱領”上是沒有提到退婚這件事的,我也忘了說;金鳳那黑夜直到走的時候,還好像有個什麼問題要開口問可又沒開口的……
“老康,我家計議著就先跟金鳳辦了這事,回頭再說我大閨女的。那離婚,不是那條領上說興的嗎?自打那黑夜,我大閨女可高興了哩!她那個,慢著點子吧!唉!那黑夜,你看,你又沒說金鳳這也行的!鬧得咱們家好吵鬧了一場!”
老太太抿著嘴,好像責備我,可又笑了。
“你想:結了婚還興離,沒結婚的就不興退嗎?”
“咱們這死腦筋嘛!唉……說是說吧,我可還是腦筋活泛著點,我老頭子可就是個不哩!這不是,爭吵得他沒法,他出門去打聽金鳳男家那人才去了哩!呃,等他回吧!”
“行!沒問題!只要有條件,找村裡、區里說說,就辦了。”
院里,兩個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鬧開了。金鎖進屋來,他娘抱他上抗吃飯,我就硬下炕走了。我走到院里,金鳳她姐拍著巴掌笑起來;我叫她們吃飯去,金鳳臉血紅的溜過我身邊,就緊著跑進了北屋。她姐對我笑了笑,追著她妹子嚷:
“哈,興啦,興啦,興啦……”
往後,他們一家好像都高興了些,只是陳永年老頭子回家來以後,還是不聲不響,好幾天沒跟我說話;我只見他每天在街里,不是蹲在這個角落跟幾個老人們講說什麼,就是蹲在那個角落跟村幹部講說什麼。不多日子以後,村幹部們又跟我說過一回金鳳的事,並且告訴我:金鳳那男人著實不進步,還許有問題哩!又過了幾天,我從村幹部那裡打聽到,區里已經批准金鳳解除婚約了。我回到家裡,又問了問金鳳他姐,她也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她並且說:等開了春,她也要辦離婚了哩!
想不到這麼一件小事,也叫我高興得不行,我並且也不顧金鳳的害躁勁,就找她開玩笑了。這麼一來,金鳳倒變得一點也不害臊了,又是認字又是學習的,並且白天也短不了一個人就跑到我屋子裡來,有時候是學習,有時候可隨便來鬧一鬧。我覺得這不很好,又沒恰當的話說,就支支吾吾地說過幾句;這一來,金鳳她姐就沖著我笑了:
“喲!老康同志,你也害臊咧?”
“你是領導我們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你也封建嗎?”
我不覺也紅了臉。好在這麼一說,往後金鳳白天也不來了,晚上來,也總是叫上她娘、她弟弟,或是她姐,或是別的婦女們同來,這倒是好了。
日子過得快,天下了兩場雪,颳了兩迴風,舊曆年節不覺就到了。這天上午,我正工作,忽然,拴柱跑來了。他大約有二十來天子沒來過了吧!今兒個還是皮帶裹腳打扮,腦袋上並且添了頂自己做的黑布棉軍帽,手上還提了個什麼小包包。
“沒啥物件,老康,這二十個雞蛋給你過年吃!”
我真要罵他!又送什麼東西啊!他把日記本交給我看,一眼見到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剛印好的“秧歌舞劇本”,就拿去了:
“哈!正說是沒娛樂材料哩!這可好了!”
我工作正忙,就說今天沒時間看他的日記。他說不吃緊,過兩天他再來拿。房門外,是誰來了,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說開了話:是金鳳!兩個人細聲細氣地說什麼啊?後來還同到我屋子裡,兩個人靠大紅櫃談著。可惜我埋頭寫字去了,一句也沒聽。
過了年,拴柱來得更勤,差不多三五天、七八天總得來一回。每回來,總是趁我晌午休息的時候,一進院子就叫我,我走出去,叫他送來,他又不肯進來;他總是在院里把日記給了我,或是講說個什麼事,就急急地走了。後來,我並且發現:白天,金鳳姐妹倆總坐在北屋台階上作針線的;每回拴柱來了,金鳳馬上就進北屋去了。他倆好多日子沒打過招呼、說過話的;我可迷糊不清了!到底又是怎麼回事?村裡面可是謠傳開來,說金鳳和拴柱自由咧,講愛情咧……我問金鳳她姐,她只說,
“他們早就好嘛!這些日子,不知道怎麼個的,我問金鳳,她也不說。你問問拴柱吧!”
拴柱也不跟我說什麼,當我問到這,他只紅著臉,笑笑,叫我往後看。
往後。村裡面謠言更厲害,村幹部和我們機關的同志還問起我來了。我知道什麼啊?我只知道:拴柱還是不斷來找我,問學習什麼的,也不進我住的屋子,也沒見他跟金鳳說過半句話!他一來,金鳳又趕緊上北屋去了。再說別的嘛,只是我發現:這些日子金鳳也短不了出去。有一回,金鎖忽然從外面急急地跑進來,大聲嚷著:
“啊啊……二姐跟拴柱上棗樹林里去了啊,啊……”
“嚷什麼哩?”老頭子向金鎖一瞪眼。金鎖又說:
“我見來著麻!”
“你見,你見……你個狗日的!”
老頭子踩著腳,就跑進北屋,亂罵開了。我拉過金鎖問,也沒問出個什麼情由。只是村裡謠言還很重,老頭子陳永年脾氣好像更大了:好多日子也沒跟我說過什麼話,還短不了隨便罵家裡人。但是,金鳳來了,他可不罵金鳳,只氣沖衝出去了。
天氣暖和起來,開春了!楊花飄落著,棗樹冒出了細嫩細嫩的小綠葉,也開出了水綠水綠的小花朵朵,村裡人們送糞下地的都動起來了。這天后晌,我吃過晚飯,也背了個鐵鍬,去村西地里,給咱們機關租的菜園子翻地。傍黑,我回來的時候,一個同志找我談談問題,我們就在地邊一棵槐樹下坐著,對面不遠,大道那邊,日頭的餘光正照在我們住的院子門口。那門口外面,一大群婦女擠著坐著,在趕做軍鞋,吱吱喳喳地鬧個不止。忽然我見拴柱背著個鍬,從大道北頭走來,我記起了他還有一畝山藥地在上庄北溝里。正在這當口,我房東家門口的婦女怕也是發覺了他,都趕緊擠著扯著,沒有一個說話的,而且慢慢地一個個都把小板床往大門裡搬,都偷偷溜到門裡坐去了。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的,那麼不順當地走著,慢慢地,一步一個模樣。門外面只剩下金鳳一個人了,她好像啥也不知道,楞楞地回頭一望,就趕緊埋下腦瓜子,抿緊嘴做活。我撇開了身邊那個同志,望著前面,見拴柱一點也沒看見我,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腳步:直到他走過那個大門口好遠,要拐彎了,才回過頭朝門口望了望,又走兩步,又停下來回頭望;他停了好多回,也望了好多回;而大門口這邊,我明明看見:金鳳從埋著的腦瓜子下面,硬翻過眼珠子,“忽悠忽悠”地也直往前面望哩!
這天晚上,我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下庄找拴柱去了。
拴柱還沒起來,他娘、他哥、他嫂迎著我,一邊給我端飯,一邊說:
“他這幾天也不知道怎麼鬧的!一句話也不說,身子骨老是不精神。說他有病嗎,他說沒,見天吃過飯就下地里悶干!”
“不要緊,我給他說說就行的。”
我拉拴柱起來,吃過飯,就跟他一道下地。我們坐在地邊上,我問他:
“怎麼個的?乾脆利落說說吧!”
他可一句話也不說。我動員了好久,他還是悶著個腦瓜子,我急了,跳起來嚷著:
“你怎麼個落後了啊?你還是個主要幹部哩!”
他這才對我笑笑,拉我坐下,說了一句:
“乾脆說吧,我早就想請你幫個忙哩!”
“那還用說?一定幫忙嘛!你說吧!”
“我跟金鳳早就好羅!我倆早就說合定了的哩!”
“那怎麼不公開?”
“笨人嘛!躁的不行,誰也不知道怎麼說,也不知道對誰們說!”
“這會子你們怎麼老不說話了呀?”
“嘿……說得才多哩!”
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笑開了。我問他,他說,他每回上我那裡去,就是去約會金鳳的:他們都在棗樹林僻靜角落裡說話。他每回到了我住的院子里,金鳳就回北屋去,用縫衣裳的針給他作記號,要是針在窗子靠東第五個格子的窗紙上通三下,就是三天以後相會,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後;在第七個格子上通三下,就是前晌,通五下,就是後晌。他這麼說著,我可揍了他一拳頭,仰著脖子大笑;他臉上一陣血紅,馬上把頭埋在兩個巴掌里,也“吃吃”笑。我跟他開了個玩笑:
“你們沒胡來么?”
“可不敢!只象你們男女同志見面那樣,握過手!”
我又揍了他一拳,他臊的不行,就做活去了。我向他保證一定成功,就回到他家。他娘、他哥聽了我的解說,都沒有什麼意見。回到上庄,我跟房東老太太和金鳳她姐說了,他們也說行。最不好辦的,就是陳永年老頭子了。晚上,我把他約來,很耐心地跟他談了談。他二話沒說,直聽到我說完,才開口:
“這事吧,我也不反對,反正……老康,我對你實說:咱們這老骨頭,別看老無用啦,可這心眼倒挺硬,這死腦筋也輕易磨化不開的。嘿嘿,”他對我笑了笑,吸了口煙,“咱們這腦筋,比年輕人這新式腦筋可離著遠點子哩!我跟我那些個老夥計們說叨說叨再看吧!你說行不?哈哈……”
下鄉時候,我還老惦記著這件事。好在,二十來天很快過去,我急急往回走。道兒上,在山北村大集上,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從保定來的“學生袖珍小字典”,我馬上買了。我很可惜:為什麼這小字典只有一本啊!回得家來,金鳳見了這,聽說是小字典,就搶過去了。我急得不行,我說那是拴柱叫我買了一年多的啊!她可硬不給我,只問我多少錢;我一氣,就不搭理她了。
兩天以後,我彙報完了工作,村幹部告給我:拴柱和金鳳的事成功了!兩家都同意,區里也同意,正式訂了婚。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高興地就直叫金鳳。金鳳跟她娘推碾子去了,她姐出來告給了我;我馬上問她:
“金鳳他倆訂了婚么?”
“訂了。我也離婚了哩!”
我歡喜得跳起來。她又說:
“他們前兒個換了東西。拴柱給她的是兩條毛巾、兩雙襪子,還有本本、鉛筆的。她給拴柱的是搶了你的那本小書,一對千層底鞋、一雙納了底子的襪子,也有本本、鉛筆。”
“你們瞎叨叨什麼哩?”金鳳跑進來了。我大聲笑著,拱著手給她作揖,她臉上一陣血紅。她姐可從口袋裡掏出條新白毛巾,晃了晃,給我送過來,對她妹子說:
“你這毛巾還不該送老康一條?我見老康回了,就拿了一條哩!怎麼個?行吧?”
“那可是該著的哩!”她娘一進來,也就這麼說。金鳳從她姐姐手裡搶走了毛巾,斜溜了我一眼,說:
“他有哩!后響拴柱來,白毛巾一條,還有我納了底子的襪子也給他哩!那毛巾,比我這還好啊!”
金鎖也回了。大家笑著,他就一邊跳,一邊伸著脖子叫:“呵,呵!”陳永年老頭子一走進院,見了這情由,也一邊笑著,一邊跺著腳,嚷著:“嗨,嗨……”不好意思似地朝我們這邊望望,緊著往北屋走去了。
1946年5月23日夜改作於張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