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附會
文心雕龍·附會
《附會》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三篇,主要是論述整個作品的統籌兼顧問題。所謂“附會”,分而言之,“附”是對表現形式方面的處理,“會”是對內容方面的處理。但這兩個方面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本篇強調的是“統文理”,所以,雖有“附辭會義”之說,並未提出分別的要求或論述。

文心雕龍·附會
第二部分論“附會”的方法以及應注意的複雜情況。劉勰要求作者從大處著眼,有全局觀點。在處理創作的具體問題時,應根據不同情況而分別對待;但在考慮全篇時,就不能只注意到枝節問題而顧此失彼。在寫作過程中,作者既不應輕率,也不必遲疑,只要掌握了寫作的基本道理,就如彈琴駕車,“並駕齊驅”,而又運用自如。
第三部分論“附會”的作用。劉勰舉漢代倪寬和三國鍾會的故事,生動地論證了“附會”的重要性,也說明了是否善於“附會”的巨大區別。最後提出,必須寫好一篇作品的結尾,使之“首尾相援”,才能達到“附會”的理想地步。

文心雕龍·附會
(一)
何謂“附會”1?謂總文理2,統首尾,定與奪3,合涯際4,彌綸一篇5,使雜而不越者也6。若築室之須基構7,裁衣之待縫緝矣8。夫才量學文9,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10,事義為骨髓11,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12;然後品藻玄黃13,摛振金玉14,獻可替否15,以裁厥中16:斯綴思之恆數也17。凡大體文章18,類多枝派19;整派者依源20,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辭會義21,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22,貞百慮於一致23。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24;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25。扶陽而出條26,順陰而藏跡27;首尾周密,表裡一體28: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發而易貌29,射者儀毫而失牆30;銳精細巧31,必疏體統32。故宜詘寸以信尺33,枉尺以直尋34,棄偏善之巧35,學具美之績36:此命篇之經略也37。
〔譯文〕

文心雕龍·附會
〔註釋〕
1附:指文辭方面的安排。會:指內容方面的處理。
2文理:這二字在本書中一般指寫文章的道理,此處據上下文意,應指文章的條理。
3與奪:即取捨。
4涯際:指文章的各個部分。
5彌綸:綜合組織的意思。彌:彌縫。綸:經綸。
6越:逾越,這裡指文章層次的互相侵越。
7基:建築的基礎。構:結構。
8緝:縫得細密。
9才量:王利器校作“才童”。才童指有才華的青年。譯文據“才童”。
10神明:指人身最主要的部分,如神經中樞。
11事義:文章中講到的事情及其意義,也就是寫作時所用的素材。骨髓:《太平御覽》卷五八五引作“骨鯁”。《辨騷》篇所說“骨鯁所樹,肌膚所附”,和此處“骨鯁”、“肌膚”並用正同。
12宮商:五音中的兩種,常用以代表五音,這裡指文章的音節。
13品藻:品味評量。玄:黑赤色。
14摛(chī痴)振:發動。金玉:指鍾磐一類的樂器。《原道》:“必金聲而玉振。”
15獻可:選用合適的東西。獻:進。替否:丟掉不合適的東西。替:棄去。
16裁:判斷。厥:其。中:恰當。
17綴思:即構思。數:方法。
18大體:這裡有大概的意思。
19派:水道的支流。
20整:和下句“理”字意同,都是整理的意思。
21附辭會義:劉逵《三都賦序》:“傅辭會義,抑多精緻。”(《晉書·左思傳》)傅同附。
22塗:同途,途徑。《周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23貞:正,使之正。
24乖:不合。
25棼(fén焚):紛亂。
26扶:沿著。陽:日光。條:小枝。
27陰:暗處。崔駰《達旨》:“故能扶陽而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後漢書·崔駰傳》)
28表裡:指事物的兩個方面,這裡指作品的內容(“里”)和形式(“表”)。
29易:改變。
30儀:審視。毫:毛髮。《淮南子·說林訓》:“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高誘註:“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耐(能)中。事各有宜。”劉勰的用意與此解略異。
31銳精:集中精力,注意推敲。
32疏:忽視。體統:主體,總體。

文心雕龍·附會
35偏善:指片面的、無關全局的小巧。
36具:即俱,有完備的意思,和上句“偏”字相對。績:功績。
37命篇:寫作成篇。經略:計謀,這裡指寫作的巧妙。
(二)
夫文變多方1,意見浮雜;約則義孤2,博則辭叛3;率故多尤4,需為事賊5。且才分不同6,思緒各異7;或制首以通尾8,或尺接以寸附9;然通制者蓋寡10,接附者甚眾11。若統緒失宗12,辭味必亂;義脈不流13,則偏枯文體14。夫能懸識腠理15,然後節文自會16,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17。是以駟牡異力18,而六轡如琴19;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20:馭文之法21,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22;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譯文〕
作品的變化沒有一定,作家的心意和見解也比較複雜;如果說的太簡單,內容就容易單薄;如果講的太繁多,文辭便沒有條理;寫得潦草,毛病便多;但過分遲疑,也反而有害。且各人的才華不同,思路也不一樣;有的能從起頭連貫到尾,有的則是枝枝節節地拼湊;可惜能夠首尾貫通的作者很少,而逐句拼湊的作者卻較多。如果文章沒有重心,辭句的意味必將雜亂;如果內容的脈絡不通暢,整篇作品就板滯而不靈活。必須洞悉寫作的道理,才能做到音節和文采自然會合,就像膠可粘合木材,豆可配合脾臟一樣。所以,四匹馬用力不同,但在一個會駕車的人手裡,六條韁繩可以像琴弦的諧和;不同的車輪向前進行,而車輻都統屬於車轂。駕馭寫作的方法,也與此相似。或取或舍,決定於作者的內心;或多或少,都掌握在作者的手裡。只要控制住總的韁繩,步調便可一致了。
〔註釋〕
1多方:《太平御覽》卷五八五作“無方”,與《通變》篇“變文之數無方”用法相同,譯文據“無方”。方:常。
2約:簡單。
3叛:亂。
4率:草率。尤:過失。
5需:遲疑。賊:害。《左傳·哀公十四年》:“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註:“言需疑則害事。”
6分(fèn憤):本分。才分:指各人寫作才能的特點。
7緒:端緒。
8首、尾:指一篇作品的始末。
9尺、寸:指一篇作品的一段、一句。
10通制:即上句“制首以通尾”的意思。
11接附:即上句“尺接以寸附”的意思。
12失宗:指文章缺乏重心,主次不分。
13義脈:以人體的氣脈喻文章內容的脈絡。流:流通,流暢。
14偏枯:病名,即半身不遂。《黃帝內經素問·風論》:“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偏枯。”這裡用以喻作品的脈絡阻塞。
15懸:高遠。腠(còu湊)理:肌肉的紋理,這裡藉以指寫作的道理。《黃帝內經素問·風論》:“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
16節文:指音節和文采,即第一段所說“品藻玄黃,摛振金玉”兩個方面。

文心雕龍·附會
18駟(sì四):一車四馬。牡(mǔ母):指雄性的馬。
19轡(pèi配):馬韁繩。如琴:和諧如奏琴。琴聲由若干弦組成,但能彈奏得很和諧。
20轂(gǔ古):車輪的中心圓木。輻(fú扶):車輪上車軸和車輪相連接的輻條。
21馭文:指寫作。馭:駕御。《詩經·小雅·車舝(xiá轄)》:“四牡騑騑(fēi非),六轡如琴。”鄭箋:“其御群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22修短:指多寫或少寫。修:長。
(三)
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1,拙會者同音如胡越2。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3。昔張湯擬奏而再卻4,虞松草表而屢譴5,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6,鍾會易字7,而漢武嘆奇8,晉景稱善者9,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10,譬乘舟之振楫11;會詞切理12,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13,寄深寫遠14。若首唱榮華15,而媵句憔悴16,則遺勢郁湮17,餘風不暢18,此《周易》所謂“臀無膚19,其行次且”也20。惟首尾相援21,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譯文〕
所以一個善於安排文辭的人,就能把不相干的事物聯繫得像肝和膽一般密切;但是一個不善於安排內容的人,卻會把本來相聯繫的事物寫得像胡和越那麼互不相干。有時修改一段文章比寫全篇還艱難,換一個字比改寫一句還麻煩,這是已有經驗證明的了。如西漢時張湯寫了奏章,卻一再被退回;三國時虞松寫了章表,卻幾次受到斥責:那是因為講的道理和事情都不夠明確,文辭和意旨也不協調。後來倪寬替張湯作了改寫,鍾會代虞松改了幾個字,於是漢武帝劉徹對張湯所改的特別讚歎,晉景王司馬師對鍾會的改動也很滿意:那是因為道理說得恰當,事情寫得清楚,文思敏銳而文句妥善。由此看來,就知道是否善於“附會”,在寫作上相差那麼遙遠!至於推敲文句,好比乘船時划槳;用文辭配合內容,就像拉著韁繩來揮動鞭子。必須通篇都安排得成功,才能表達得深而且遠。如果開端寫得很好,而後面卻差得太遠,那麼作品收尾的文勢便將窒塞,作品的感染力也得不到充分的發揮。這就如《周易·夬卦》中說的:“臀部沒有皮肉,走路就不快。”只有全篇首尾呼應,關於文辭和內容的安排,才可說是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註釋〕

文心雕龍·附會
2同音:和諧的音節,這裡比喻關係密切的事物。胡:指北方。越:指南方。《比興》篇曾說:“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3已然:過去已是如此。下文即舉具體例證說明。
4張湯:漢武帝時的廷尉(最高司法官)。擬:起草。卻:退。《漢書·倪寬傳》:“時張湯為廷尉,……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5虞松:三國魏的中書令(掌管機密文書的長官)。譴:譴責,批評。《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引《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於顏色。會(鍾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
6倪寬:張湯的僚屬。更:改。
7鍾會:三國時魏的司徒(最高行政首長之一)。易字:換了幾個字。
8漢武:漢武帝劉徹。
9晉景:晉景王司馬師。
10絕筆斷章:指在字句上決定取捨。絕、斷:都是裁決的意思。
11楫(jí吉):划船的槳。
12切:切合。理:作品中講的道理,這裡泛指內容。
13克:能。底:及。
14寄:寄託。寫:抒寫。
15首唱:指一篇的開端。榮華:草木的花,這裡指文章的開頭寫得較好。
16媵(yìng映):陪嫁的人或物。這裡指作品的結尾部分。憔悴:和上句“榮華”相反,指枯萎。《淮南子·說林訓》:“有榮華者,必有憔悴。”
17遺:和下句的“余”略同,都指作品的結尾。郁湮(yān煙):阻塞。
18風:指作品對讀者的教育和感染的力量。
19臀(tún囤):人或動物身體後部兩股上端與腰相連的部分。
20次且(zījū資居):同“趑趄”,行走困難。這裡所引兩句,是《周易·夬(guài怪)卦》中的原話。
21首尾相援:前後互相照應。
(四)
贊曰:篇統間關1,情數稠疊2。原始要終3,疏條布葉4;道味相附5,懸緒自接。如樂之和6,心聲克協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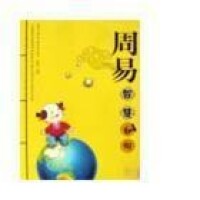
文心雕龍·附會
總之,篇章的全面安排是不容易的,內容的種類也十分繁雜。作者必須從頭到尾,把一枝一葉都布置得很恰當;只要內容能布置妥帖,思緒自然可連貫起來。就像樂曲必須和諧一樣,作者內心的話也都要配合得協調。
〔註釋〕
2情數:指內容多種多樣。《神思》:“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稠(chóu綢)疊:繁多,複雜。稠:多而密。
3原:追溯。要(yāo邀):約會,這裡有聯繫的意思。《周易·繫辭下》:“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4疏:疏通。
5道味:指作品中體現的道理、意味。
6如樂之和:《左傳·襄公十一年》:“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7心聲:表達思想的語言,揚雄《法言·問神》:“故言,心聲也。”

文心雕龍·附會
4.1一、同中之異
紀昀側重首尾一貫。紀昀的開始的眉批:“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即後來所謂章法也。”紀昀其他批註還有三處,在劉勰談到“絕筆斷章”的要求后,紀昀作了最為重要的眉批:“此言收束亦不可苟。詩家以結句為難,即是此意。”②看來,紀昀的側重點在首尾一貫,其中又非凡強調結尾的重要性。作品結尾經常是作品有機整體性的表現。
黃侃所側重的是命意修辭的一貫。他說:“《晉書·文苑·左思傳》載劉逵《三都賦》曰:‘傅辭會義,亦多精緻。’彥和此篇,亦有附辭會義之言,正本淵林,然則附會之說舊矣。循玩斯文,和《熔裁》、《章句》二篇所說相備,然《熔裁》篇但言定術,至於定術以後,用何道以聯屬眾辭,則未暇晰言也。《章句》篇致意安章,至於章安以還,用何理以斠量乖順,亦未申說也。二篇各有‘首尾圓合’、‘首尾一體’之言,又有‘綱領昭暢’、‘內義脈注’之論,而總文理定收尾之術,必宜更有專篇以備言之,此《附會》篇所以作也。附會者,總命意修辭為一貫,而兼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功績者也。”黃侃所強調的是命意修辭要一以貫之之義。所以黃侃還非凡指出“源”和“干”的重要,強調劉勰的“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的原則。
劉永濟則側重於“全篇一意”之義。他說:“附會二字,蓋出《漢書·爰盎傳贊》‘雖不好學,亦善附會’,張晏《注》曰:‘因宜附著會合之。’亦見劉逵《蜀都吳都賦注序》。彼文曰:‘傅會辭義,抑多精緻。’其義即今所謂謀篇命意之法。為文之道,百義而一意,全篇而眾辭。辭散不相附,則章節顛倒,而文失其序;義紛而不相會,則旨趣黯黮,而言乖其則;蓋百義所以申一意,眾辭所以成全篇也。”④劉永濟所強調的是“百義一意”。只有一意貫穿全篇,這才是謀篇命意的根本道理。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三家,都沒有注重到劉勰《附會》篇中“雜而不越”這個重要的詞。突出這個詞的是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王元化說:“雖然前人已經提出了附會的新問題,可是藝術構思的根本任務究竟是什麼呢?他們並未加以論述,劉勰是首先對這個新問題作了明確探析的理論家。《附會篇》云:‘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和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這裡所提出的‘雜而不越’一語,就是有關怎樣處理藝術結構新問題的概括說明。案:‘雜而不越’這句話見於《周易》。《繫辭下》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韓康伯《注》:‘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逾越。’焦循《易章句》也說,‘雜’謂‘物相雜’,‘不越’謂‘不逾其度’。韓氏、焦氏的註疏都認為這句話是在說明《易》象萬物變化之理,一方面萬事萬物變動不居,另方面萬事萬物的變化又都不能超出天尊地卑的限度。劉勰把這句話用於文學領域以說明藝術結構新問題,顯然已捨去了《繫辭下》的本義。根據《附會篇》來看,‘雜’是指藝術作品的部分而言,‘不越’是指不超出藝術作品的整體一致性而言。‘雜而不越’的意思就是說藝術作品的各個部分必須適應一定目的而配合一致。儘管藝術作品的各部分、各細節在表面上千差萬別,彼此不同,可是實際上,它們都應該滲透著共同的目的性,為表現共同的內容主旨自然而然地結合為一個整體,使表面不一致的各部分、各細節,顯示了目的方面和主旨方面的一致性……在藝術結構新問題中,‘雜而不越’的這個命題首先在於說明藝術作品是單一(劉勰又稱之為‘約’)和雜多(劉勰又稱之為‘博’)的統一。從單一的方面說,藝術作品必須首尾一貫,表裡一致。在這一點上,藝術和理論有某些相似之處。理論要求邏輯推理的一貫性,使所有的論點聯接為一條不能拆開的鏈鎖,一環扣一環地向前發展,以說明某個基本思想原則。藝術也同樣要求形象細節的一貫性,使所有的描寫圍繞著共同的主旨,奔赴同一個目標,而不答應越出題外的駢拇枝指存在……從雜多方面來說,藝術作品必須具有複雜性和變化性,通過豐富多彩的形式去表現豐富多彩的意蘊。藝術要求有生動、豐滿的表現,以顯示藝術形象在不同情況下可能產生的多種變化……劉勰使用‘雜’這個字來表明藝術作品的雜多性,還可以舉《詮賦篇》為證。《詮賦篇》說:‘文雖雜而有質,色雖揉而有本’。在這裡,‘雜’、‘揉’二字同義,都是代表雜多的意思。顯然,劉勰是把‘雜’作為肯定意義提出來的,以和單調、貧乏、枯窘相對立。”⑤王元化的論述既符合劉勰的思想,也布滿新意。非凡是他提出劉勰在強調結構藝術中的一貫性的原則的同時,也肯定劉勰對“雜”的肯定,“雜而不越”是要在單一和雜多之間達成統一,這一點同樣是很重要的。王元化的論述超越前面三家之處也正在這裡。本文將沿著上面四家的讀解,作進一步的補充和發揮。
4.2二、“雜而不越”說的美學內涵

文心雕龍·附會
(一)要把文學作品理解為生命的形式,可簡稱為“生命的形式”原則。劉勰認為解決好文學創作中的謀篇布局的結構藝術,首先要把文學作品理解為生命的形式。這一點王元化也提到了,但沒有展開來講。這裡我想做一些發揮。劉勰在《附會》篇寫道:
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這裡所說的情志、事義、辭采、宮商是文學作品的基本層面,和此相對應的比喻則是“神明”、“骨髓”、“肌膚”、“聲氣”,而這些都是人的生命體的一部分。劉勰在這裡用了這個隱喻,顯然不是偶然的。他就是認為作品和有生命的人一樣,有靈魂、有骨髓、有肌膚、有聲氣。而且具體指出“情志”是靈魂,事情及其意義是骨髓,辭采是肌膚,音律是聲氣。作品就是生命的形式,對於生命來說,神明、骨髓、肌膚、聲氣是有機組合,它們密切相關,缺一不可;對於作品來說,情志、事義、辭采和音律也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有機整體性是生命的根本特徵。作為“雜而不越”就是要追求這種有機整體性。所謂“總文理,統首尾,定和奪,合涯際,彌綸一篇”都要從生命有機整體性特徵出發來要求。
劉勰用人的生命體來比喻文學作品並不是從《附會》篇開始的,許多篇都有。比較突出的如《辨騷》篇對《離騷》的描述:“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詞。……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和並能矣。”這裡不但用屬於人的身體的詞語“骨鯁”、“肌膚”來形容作品,更用“驚采絕艷”這種形容女色的詞來形容作品。又,《體性》篇的“贊”,其中說:“辭為膚根,志實骨髓”,認為作品的“辭”如同人的肌膚,而作品所表現的“志”則是人的“骨髓”。又,《風骨》篇說:“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這裡用了“骨”、“骸”、“形”、“氣”,都是人的生命體的某一部分。非凡是“氣”,按照徐復觀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的理解,指的是“生命的力”。又,討論對偶新問題的《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又,《練字》篇寫道:“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又,《詮賦》篇:“及靈均唱騷,始觀聲貌。”這些例子,涉及人體的外形、體貌、聲貌、肌膚、手指、骨髓、骨骸、氣息、感情等由外而內各個部分。以上幾例說明《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的確是比較自覺地把文學作品看成是“生命的形式”。劉勰的“生命的形式”的觀念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受揚雄的影響,揚雄曾把文章比喻為女色,說:“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揚雄這裡所說的“書”即是文學。劉勰可能很看重揚雄的觀點,而加以借鑒,此其一。可能受東漢以來流行的人物品鑒風氣的影響。人物品鑒從漢代開始,到了魏晉六朝此風興盛起來。假如說東漢的人物品藻更重從人物外貌看人的道德修養方面的程度的話,那麼到了魏晉時期的人物品鑒就更重通過查看相貌看人物的才華能力,而到南北朝時期,由於士大夫在混亂的社會境遇中,更追求生命的自由,其時的人物品鑒也隨之變化,轉而更看重人的內在的風韻、神明、骨氣等,如《世說新語·品藻》寫道:“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而《晉書·王羲之傳》亦載:“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世說新語·容止》:“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諸許也。’”《世說新語·輕詆》:“舊目韓康伯,捋肘無風骨。”《世說新語·賞譽》:“王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這僅是一些例子。人物品鑒的思維不能不延伸到文學理論和批評上面,於是在文論中借用人的生命體的一些詞語,進一步把文學理解為像有生命的人一樣也就很自然了。劉勰的《文心雕龍》把文學理解為生命的形式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其二。另外,文學的生命化也和當時“文學的自覺”密切相關。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氣為主”之後,文學就和人的個性特徵聯繫在一起。劉勰在《風骨》篇引了曹丕的論點並作了改造,這說明劉勰對“氣”十分重視。“氣”有多重理解,但把“氣”理解為生命的力是最為平易和恰當的。按照這種理解,文學就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現,劉勰把文學本身視為生命體也就順理成章,此其三。既然文學作品是一種生命體,是鮮活的,那麼每一個作者在布局謀篇的時候,就不能不充分考慮到作品作為生命的種種特徵。這樣,劉勰除了指出“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外,在《附會》篇中,還頻頻用了其他一些以生命隱喻文學的詞,如“畫者謹發而易貌”的“發”、“貌”,“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的“味”、“脈”,“夫能懸識腠理”的“腠理”,“善附者異旨如肝膽”的“肝膽”,“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的“媵”、“憔悴”……《附會》篇幾乎把稱呼人體及其功效的詞語,都盡量地加以使用,這顯然和劉勰的文學生命觀有密切聯繫。

文心雕龍·附會
(二)整體優先原則。這是“雜而不越”說十分重要的規定。劉勰提出要重視文章的整體,不能只在細部玩弄技巧。《附會》有云:
夫畫者謹發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大意是說,繪畫者一味描繪毛髮,而所描繪的形貌就會失真。射箭者只見毫毛,而不見整堵的牆,就會因小失大。所以寧可委屈一寸而保證一尺的伸直,寧可委屈一尺而保證一丈的伸直,寧可放棄局部的細巧,也要學會整體完美的功夫,這才是謀篇布局的概要。這裡,劉勰實際上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整體是制約局部的,而局部只能是整體中的局部。尺、寸和尋哪個更重要,當然是尋制約著尺,尺制約著寸,整體無論怎樣是大於部分之和的。一寸一寸的累積,而不顧整體的要求這是不符合作品布局謀篇的道理的。換句話說,就作品的整體看,“寸”只有在“尺”中才能獲自得義,而“尺”只有在“尋”中才能獲自得義,細部只能在整體中才能獲自得義。我們不能說孤立的這一“寸”多麼美,這一“寸”的美,只有在尺中、在尋中在整體關係中,才能顯出美質。因此,整體優先的原則就非凡的重要。在這裡我們似乎又聞到了現代理論的氣息。因為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思想,含有現代結構主義的基本精神。西方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流行結構主義的基本宗旨是什麼?就是關係大於關係項。整體的結構關係大於個別的結構單位,個別的結構單位只有納入整體結構中去才會獲自得義。
在上個世紀結構主義流行以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思想,早已運用於作品的探析中。例如文學結構主義的大師法國學者羅蘭·巴爾特在《敘事作品探析導論》中,就在“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和“關係大於關係項”的原則下,對敘事作品的句子和話語作了探析,他首先說:“大家知道,語言學探究到句子為止。語言學認為這是它有權過問的最大單位。確實,句子是一個序次而非序列,所以不可能只是組成句子的詞的總和。”這段話有兩層意思,第一,語言學的探究單位,到句子為止,超過句子就是修辭學的事情了;第二,句子只是序次,而不是序列,所以不能說句子是組成句子的詞的總和。這第二層尤其重要,作者告訴我們一個句子並非句子中詞的序列的總和,句子的構成在於詞和詞之間的關係中。他繼續說:“話語雖然是獨立的探究客體,但要從語言學出發加以探究。假如說,必須先給任務龐大、材料無計其數的探析制定一個工作的前提,那麼,最理智的辦法是假定句子和話語之間有同源關係。”這意思是,句子和繁複的話語之間有同源關係,因此,我們在探析話語的時候,可以把一篇話語,當作一個大句子來探析。或者說,話語是大句子,句子是小話語,它們的結構關係是相似的,可以作出相似的探析。他最後強調在語言的“描述層”句子的探析,說:“大家知道,在語言學上,一個句子可以進行多層次的(語音的,音位學的,語法的,上下文的)描述。這些層次處於一種等級關係中,因為,雖說每個層次有自己的單位和相關單位,迫使我們分別單獨對其進行描述,但每個層次獨自產生不了意義,某一層次的任何單位只有結合到高一級層次里去才具有意義。”這裡提出單位和層次的關係和層次等級的觀念,深得結構主義的精神。這意思和劉勰的“寸”、“尺”、“尋”之間的關係極為相似。“寸”、“尺”、“尋”是一種層次等級。首先“寸”只是細部,只是一個小單位或小單位關係,是產生不了意義的,或產生不了整個話語系統(例如一首詩)的意義。“夜雨剪春韭”是一個句子,是“寸”,它只是告訴讀者在夜裡下雨了,有人去剪春韭,但為什麼要在夜裡去剪,不在白天剪?為什麼是剪春韭而不收割別的東西?這是在一首詩中還是在一篇散文中?我們不得而知。這時候假如躍上一個層級,由“寸”到“尺”,那麼其意義就進了一步,如“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我們發現這是一個詩句,因為這裡有對偶關係,“夜雨”對“新炊”,“剪”對“間”,“春韭”對“黃粱”,而且平仄關係也像詩,意思也像詩,但這個小話語(劉勰所說的“尺”),在哪個大話語(劉勰所說的“尋”)中呢?詩的整體話語是什麼意思呢?意義仍然不清楚。我們只有把“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這個等級再躍上一層,放到杜甫的《贈衛八處士》這首詩的整體話語中,那麼作為“尺”的單位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的意義才全部顯示出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和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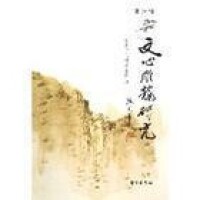
文心雕龍·附會
(三)“依源循干”原則。這是“雜而不越”的又一個基本原則。劉勰《附會》篇說: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
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腠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劉勰提出“依源循干”原則是是有針對性的,那就是當時流行的作品有的為了追求詞句的華麗,結果是統緒失宗,辭味混亂。有的作品雖然寫得“簡約”,但因布局謀篇不當,出現了“義孤”。不論是繁雜的傾向(“失宗”),還是簡陋的傾向(“義孤”),都具有一個通病,那就是“義脈不通”。劉勰對文學作品的理想是“雜而不越”,即既要“博”,又要“約”,把“博”和“約”兩者統一起來,達到“乘一總萬,舉要治繁”(《總術》)的目標。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雜而不越”的結構藝術的理想呢?劉勰提出了“依源尋干”的原則。劉勰的“依源尋干”,總的看,就是“一致性”的原則,即作品的主旨要一致,所以說“務總綱領”。作品的“綱領”是什麼,當然是情志之主旨。但假如把作品主旨的一致,理解為一種單調、乾癟、貧乏的東西,也是不行的。劉勰認為關鍵之點是明確“源”和“干”的新問題。一條河流只有一個主要的源頭,儘管支流眾多;一棵樹只有一個主幹,儘管枝葉繁茂。所以假如作品的支流無序和枝葉混亂的話,那麼“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多”是可以的,但要歸於“一”。一定要做到雖有萬條路,但最後的終點只有一條主幹線。雖有各種情志,但最終要情志趨於一個方向。“一”和“多”看起來是矛盾的,但一定要達到矛盾的統一。劉勰用“夫能懸識腠理,然後節文自會”云云來描述他的結構藝術的理想。
4.3三、“雜而不越”的文化蘊含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疏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文心雕龍·附會
張岱年對於“和而不同”作了這樣的解釋:“和,本指歌唱的相互應和。《說文》:‘和,相應也。’引申而指不同事物相互一致的關係。春秋時代,有所謂和同之辯。《國語·齊語》記載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云:‘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也。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雜已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立百體……於是先王聘後於異性,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已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史伯提出的‘和’的界說是:‘以他平他謂之和’,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產生新事物,故云‘和實生物’;假如只是相同事物重複相加,那就還是原來事物,不可能產生新事物。故云‘同則不繼’。史伯有關和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至今仍閃耀著聰明的光輝。”我們說劉勰的“雜而不越”的思想的文化蘊含在“和而不同”思想中,就在於劉勰在作品結構面對繁複和扼要、博多和簡約、源頭和支派、根乾和枝葉的悖立的時候,沒有一味選擇扼要、簡約、源頭、根干,而排斥繁複、博多、支派、枝葉。劉勰力圖讓“雜多”和“單一”聚合在一起,設法達到平衡,達到和諧。所以我們可以說劉勰的“雜而不越”說是古老的“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在作品結構藝術思想上面的投射。劉勰的思想也是深刻的,至今仍然閃爍著詩性的聰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