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題韜
著名象棋理論家
賈題韜(1909-1995),男,號玄非,法名定密,山西洪洞人,畢業於山西大學法學院,著名象棋理論家。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賈題韜曾組織學生游擊隊參戰抗日,任第二戰區中校秘書;因病移居成都,在光華、金陵、成華、華西等大學執教,教授邏輯學與道家哲學。民國三十年(1941),賈題韜所著《象棋指歸》出版,後來被新加坡象棋學會列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1950年,賈題韜被聘為高級顧問,隨解放軍入藏,任西藏宗教事務委員兼佛協副秘書長,在拉薩創辦醫院為藏胞施針治病;1979年後,歷任四川省佛協副會長、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等。賈題韜應請在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等處講授佛學,於成都文殊院講《壇經》等,並召集成都學術界人士創建四川禪學會、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所,研究佛學,講解撰述。他雅好象棋,有中國"無冕棋王"之譽。其講稿整理為《壇經講座》、《論開悟》、《佛教與氣功》等,輯為《賈題韜佛學論著》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從學者有馮學成、嚴永奎、門世海等,其中馮學成撰有《生活中的大圓滿》、《棒喝截流》等書弘揚禪宗。1995年1月8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6歲。
清宣統元年(1909年)賈題韜出身於山西省洪洞縣趙城一個富農家庭。少年時期在故鄉讀小學。
十三歲(1922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學。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不久,流風所及,學校民主風潮迭起,上課不正規,文娛體育活動卻很活躍,學生尤熱衷於象棋鬥技。賈題韜聰穎好學,課餘亦喜對弈。
民國十四年(1925年)11月,山西省青年象棋比賽在太原舉行。不滿十六歲的高中一年級學生賈題韜是上百名青年選手中最年幼者。他斬關奪隘,以全勝戰績榮獲冠軍,名震華北。

賈題韜著作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賈題韜畢業,留校任教,講授邏輯學,后又兼任山西省教育廳秘書。由於教學關係,他開始研究法相唯識學方面的著作,逐漸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念佛吃素,專修凈土。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法師(1879—1967年)蒞臨太原弘法,講授《菩提道次第論》及西藏佛教中觀學說。二十六歲的賈題韜每會必到,風雨無阻。雖然他本著法相唯識的觀點,對法師所講的頗有懷疑;但對法師持戒精嚴的高風卓節十分景仰,遂皈依之。此後,他一直醉心於法相唯識的研究,旁及禪凈諸宗和西藏密宗。先生治學自具見地,不苟同於人,惟對歐陽竟無大師(1871—1943后)十分崇拜。
賈題韜自幼體弱多病,研習法相唯識既久,頗感名相繁瑣,無益身心受用。其時校中有一專治禪學的教授名陳夢桐,勸他讀《楞嚴經》。當其誦至“七處征心”一段,恍然若有所悟。告之於陳,陳又令讀明代瞿汝稷撰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的《指月錄》。該書為儒者談禪之作,既是禪宗歷代傳法機緣的記載,亦能啟發人的智慧。當賈題韜讀至書末《徑山宗杲語要》時,深感句句親切,不啻耳提面命,如醍醐灌頂,甘露滋心,積疑頓釋,慶快平生。自此始知有宗門向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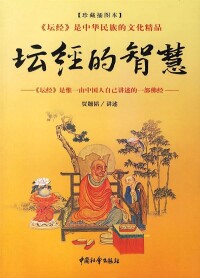
賈題韜著作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2月,賈題韜因病弱之軀無法適應抗日前線的緊張戰鬥生活,不得已西遷至大後方成都,先後在蜀華中學(今成都十四中)、成都縣中(今成都七中)、華陽縣中(今成都人民南路中學)、石室中學(今成都四中)任教。當時能海法師住持成都南郊近慈寺,賈題韜遂隨法師研習《大威德生圓次第》,並於寺中得便閱讀唯識、天台、華嚴諸宗典籍,然終以禪宗為主。
抗日戰爭時期,藏傳佛教中觀學說和密宗傳入內地,風靡一時,以唯識為不了義。內地不少唯識學者也不自信,從而附益其說。賈題韜年輕氣盛,對成都所謂“中觀家”破唯識頗不服氣,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屢屢跟他們辯論,從而贏得了“唯識家”的稱號。

賈題韜先生的全家合影

賈題韜(右)
在中國佛教史(尤其是禪宗中)上,棋藝高手可謂英才輩出,代不乏人。大家熟知的“棋逢敵手”這一成語,就來源於晚唐一位名叫釋尚顏的僧人懷念好友陸龜蒙處士詩中的一句——“事厄傷心否,棋逢敵手無?”(見《唐詩紀事·卷七十七》稍後,趙宋僧人釋普濟所撰《五燈會元·卷十九·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一文中,亦有“棋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工”之句。唐宋時期,棋風大盛,上至宮庭朱門,下至僧道俗人,一時皆受波及。棋道貴“活法”,禪門參“活句”,二者雖殊途,志趣卻同歸。弈棋相鬥在於“智”,往返詰難亦在於“智”。一局象棋大戰彷彿是一堂佛家的辯論法會,無論是善戰,還是善辯,都是意志和智慧相結合的一場競賽,勝負的關鍵全在於“靈巧”和“達識”。所以,棋也好,禪也好,唯有憑藉明眼人的悟性,依靠智慧和意志的力量,方能立於不敗之地。的確,面對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門,又有多少人不識自性!因此,明心悟通之理,並不只限於佛門,亦適用於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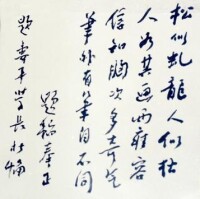
賈題韜書法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賈題韜與袁煥仙(1887—1966年,當今佛教大德南懷瑾之師)、朱之洪(1871—1951年,辛亥革命元老,歷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但懋辛(1886—1965年,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川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蕭靜軒(生卒年不詳,四川大竹縣人)、傅真吾諸居士共建“維摩精舍”。其宗旨一曰:“整理禪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為整體之系統。”二曰:“比較(禪宗)與其它(佛教)宗派之異同,以明禪宗教外別傳之特點。”三曰:“結合中西學術思想,提高禪宗之學術地位及其實用價值。”其內部分工為:袁煥仙負責法部,傅真吾負責財部,賈題韜負責學部。精舍成立數年,嗜法味者頗不乏人。最後因經費不足,內部意見不一致而告終。

賈題韜在布達拉宮前的照片

《象棋殘局新論》
1979年,先生回到成都,時已七十矣。次年12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代表會議上,先生被選為理事。
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協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在成都舉行,賈老當選為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
1982年1月,先生所作《禪悅》一詩在中國佛教協會主辦的《法音》雜誌上發表。詩云:
“撞著鼻頭一事無,悟來已自費功夫。
恆沙分別知多少,描盡風流總不如。
無端拈得龜毛新,驀向刀山解翻身。
慚愧年來煙水遍,孤明原自未離人。
牛也驢兮萬劫孤,幾人探得驪龍珠。
拈花略露風規在,若計歸程猶半途。
泥牛海底載珠還,草料隨分護惜看。
鞭策雖雲少不得,歸家早在未生前。”
1995年1月8日,這位禪門大師在成都病逝,享年八十六歲。縱觀賈老的一生,1980至1994年這十四年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可惜天不假年,當其事業達到巔峰階段的時候,竟溘然長逝,令人凄愴!揮淚成文,用誌哀思。
| 時間 | 名稱 | 出版社 |
| 《象棋指歸》 | ||
| 《正理一諦論》(與密悟格西,藏傳佛教典籍) | ||
| 《辨了不了義論》(與密悟格西,藏傳佛教典籍) | ||
| 《入中論》(與密悟格西,藏傳佛教典籍) | ||
| 1987年 | 《禪悅》(發表於《法音》雜誌) | |
| 《象棋論壇》 | ||
| 《象棋殘局新論 》 | ||
| 1987年1月 | 《詠曇花》 | 《法音》雜誌 |
| 1983年6月 | 《佛教與氣功》 | 四川省佛教協會 |
| 1993年9月 | 《佛教與氣功》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1993年9月 | 《論開悟》《壇經縱橫談》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83年6月,賈老被選為第五屆四川省政協常委。
1987年3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代表會議上,賈老當選為常務理事。4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廣濟寺成立,賈老被聘為高級研究員。同時,他還被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聘為理事。6月,四川省佛教協會第四屆代表會議在成都文殊院舉行,賈老當選為副會長。
1988年6月,賈老被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賈題韜先生塑像
先生雖學涉百家,煙塵參訪,而其為人,則隨緣不變,一歸禪宗。蓋非徒事文字知解,實於生活中有所體驗而身體力行者也。
1985年至1986年,位於北京法源寺的中國佛學院邀請賈老演講《論開悟》,凡十五講。這次學術講演十分成功,在佛學院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學生們普遍反映:賈老居士知識淵博,見解精闢,觀點新穎,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每次演講,能容一百多人的教室座無虛席。校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氣功專家及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也經常慕名前來聽講,有的人甚至每場必到。講演完畢,京華轟動。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邀請賈老留京擔任佛學院副院長,賈老婉言謝辭。
賈老說:“禪宗在中國佛教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可以說,中國佛教的特色就是禪宗,沒有禪宗就沒有中國佛教。”“我認為釋迦牟尼佛本人就是一位大禪師。他六年苦行,菩提樹下四十多天的靜坐思維,無不是在參禪。最後,他所得的‘道’也是從參究開悟而得到的。釋迦牟尼佛從出家到成道的經曆本身就是一部禪宗史。”“禪宗有一大特點,就是提倡讓人大膽地懷疑。所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這是禪宗不同於佛教其它各宗派以至其它各宗教的地方。宗教信仰應當允許懷疑,由懷疑而產生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這種精神唯禪宗所獨具。我本人就是先對佛教懷疑,通過研究唯識、中觀,才對禪宗產生興趣和信仰的。”“現在有些人把禪宗說得毫無價值,甚至說了許多不公允的話。這是沒人深入研究教理,沒有對禪宗作全面深入探討而產生的誤解。禪宗是佛教的心髓。禪宗在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1986年秋,應邀來中國佛學院講學,值曇花將放,傳印法師(現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豫川注)為余移一株至寢窗,以資飽賞。賦句:
傳師送到曇枝鮮,花意人情兩躍然。每憾累看看不足,今宵再驗未開前。
徘徊窗下覘花開,徐徐香飛浮碧苔。笑似黃梅傳法日,會心獨解夜中來。
夜半正明洞上風,玄關金鎖若為通。誰知百尺竿頭事,別有曇花下語同。
千金一刻為人留,共勉因緣大事秋。坐對優曇憶懸記,花開念佛到花收。”
賈老擅長絕句,詩才頗高,所作深蘊禪意。如上所引,僅以詠曇花為題,範圍狹窄,一般人至多能寫出二、三首絕句;而賈老竟能一氣呵成四首,且琅琅上口,韻味深長,足見其才華超群。
先生說法時,曾舉拈花公案云:“此為禪宗之絕妙話頭,脫卸了語言文字的樊籠。其表現方式一反呆板教條之灌輸,上升為藝術化。佛以拈花為鞭影,迦葉一笑便奔空絕逸,實為啟人心靈之美妙圖境,非宗教條框所能範圍。禪宗化宗教氣氛為藝術光芒。若能理會禪宗師友見面之種種活潑言動,推拉棒喝之機智,偈頌詩歌等文彩,皆瀰漫拈花微笑之氣氛。如於法身覷透,當人直驗得釋迦佛之心髓,浩浩三藏,千經萬論,無量妙義,全歸於一花一笑。不得正法眼之人,如何能有如此手眼,如此智慧?從道德、智慧、藝術方面講,此公案具有極大的代表性。禪宗沿此路線建立,併發揚光大。佛所拈之花,亦由禪宗一代一代傳接至今,仍清新鮮艷。學人能明此公案底蘊,試拈一花,或破顏一笑么?”
“除佛教外,一切宗教俱為有神論。禪宗之外,一切宗教,包括佛教內各大宗派,都認為教主言行,一字一句不可更改。唯禪宗從懷疑入手,不但不立神,佛亦不立。所謂‘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無此懷疑精神,則不能學禪宗。開悟是從懷疑中開悟,老師傳授弟子,乃燃其懷疑之火;弟子接受老師傳承,即突破所設立的懷疑之關。疑情奮起時,無佛無師,無經無論,無禪無我,一切分別相不立。至此,莫怕落空,空的只是語言文字所系之世諦,只有在這個空中方可見到真諦,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何為禪宗之悟?是涅盤,菩提,絕對之本體,即體驗‘絕對’。我們能否居於絕對之外?若居其外,則形成相對,而非絕對;若居其中,剛我即絕對,當下便是,不隔纖毫。現前一念廓周法界。我即於絕對之中,則以絕對融絕對,以自我觀自我。轉身便是,有何難哉!人類活動之起動基點,即當前一念。此一念豈在絕對之外?此一念即為絕對。絕對者,非時空可限也,故可頓悟成佛。”
從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賈老在成都文殊院開講《六祖壇經》達五十餘會,從現代科學文化的角度,對佛教教義和禪宗理論作了重大的發揮。蜀中善知識雲集聆誨,獲益匪淺。1988年至1989年,八十高齡的賈老又邀集四川學術界名流成立“四川禪學研究會”。在兩年多的時間內,賈老為弘揚禪學,廢寢忘食,心力交瘁,竟致積勞成疾。
1990年6月至7月,賈老應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妙湛法師(1909—1995年)之邀,至廈門南普陀寺講授佛學。聽眾深沾法乳之恩,盛讚賈老講解技巧熟練,內容非富多彩,邏輯嚴密,有條不紊,深入淺出,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令人信服。
賈老對於禪宗內部、禪與佛教、禪與密宗、禪與儒教、禪與道教,乃至禪與當代科學文化等種種問題、種種矛盾皆有精闢論述,見解獨到,卓爾不群,不落前人窠臼,在當今佛學界聲望甚高。
賈老說法時,曾舉“三法印”云:“大乘、小乘、顯教、密教、中觀、唯識,俱為佛教。佛所說教,出於菩提樹下一悟。說法四十九年,開示悟入,亦為此一悟。故學佛學法之人,徹法源底,亦為此一悟。然此悟,又非分別思維之概念活動也。概念的本質、作用自發地與三法印相反。諸行無常,而概念則具常一之要求,否則思維無法開展。諸法無我,而概念則把事物固定起來,方可成為概念之本質,作建立各種法則與關係之根據。涅盤寂靜則更是超越語言的,而概念活動則要求對任何事物都應以語言來表述清楚。須知概念乃是思維之手段,僅為思想之外殼,而非事物之實際,然又為人類生活、工作所必需。而於絕對超越,一般經驗所不及處,概念思維活動不得不止步。涅盤乃絕對,概念必先相對,以相對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絕對之涅盤。故龍樹之《中論》即用破之方法,對各種概念立論一一破斥。在禪宗,進而變為棒喝。禪宗‘不立文字’即基於此。然不立文字非後世狂禪妄掃經論者所知也。‘不立’者,不即不離也。概念活動之當下一念亦為涅盤,知之乎?”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經禪宗一倡,許多人就認為,學禪宗,就不必學教了。此乃極錯誤之看法。不通教,焉能通宗!教外別傳系指數不能盡其意,即單靠教還不能完全解決宇宙人生之根本問題,有待於教外別傳。禪宗脫卸尋常框架,撥轉向上關捩,便當人情識難以湊泊。奇奇怪怪之處,於人之生活實際處點斷命脈,猛省回頭。禪宗之方法,乃活潑潑的啟發教育,所指示的乃為教下精華,最吃緊、最精彩之處。非語言思維所能盡,而以心印心成為最絕妙的親身傳授。”
賈老深知語言文字思維之障於道,常云:“眾生無始以來之實執,名言習氣極難捨棄。如教下為破眾生之我執,立一法門曰‘人無我’,眾生即執此‘人無我’為實。教下立‘法無我’,眾生即執此‘法無我’為實。教下為破此執,立‘亦有亦空’,眾生亦為執實。教下又立,‘非有非空’“不有不空”、“真空妙有”等等,眾生亦競而執之。在語言形式上,貌似層層深入,玄之又玄;不知其仍在語言思維、概念活動的圈子裡原地踏步,於實際身心性命何曾稍措手腳,若不於心靈深處徹底掀翻,則語言文字之障,就永無顯露底蘊出頭之日。知此,則知祖師們何以變說教為棒喝機鋒之良苦用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