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曙輝
益陽市人民防空工作辦公室副主任
黃曙輝,男,1960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現任益陽市人民防空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處級),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攝影家協會會員、益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散文、報告文學和詩歌創作,報告文學《槍魂》、《中國牌專家》等作品曾經在全國和全省獲過一等獎,出版過詩集《荒原深處》、散文集《四季情緣》、報告文學集《槍魂》《先鋒之歌》等。

黃曙輝
黃曙輝大學畢業后,先後當過教師、宣傳部門和組織部門幹部,2000年擔任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委常委、組織部長,2003年擔任湖南省南縣縣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2006年擔任益陽市環保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正處),2011年擔任益陽市人防辦副主任、副書記。近年來,黃曙輝工作之餘致力於詩歌創作,發表了大量的詩歌作品,在社會上產生可廣泛的影響。《湖南日報》、《湖南作家》《作家天地》《文學風》《天津詩人》《民族日報》《益陽日報》等眾多報刊發表過對他的專訪和詩歌評論。
三中全會以後過來的人都知道那時候文學對於中國政治的影響,所以黃曙輝從大學開始就像當時許多大學生一樣也對文學十分狂熱。那時候,大學學報發表的第一學生論文《試論新詩歌的散文美》就是他寫的。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軍工企業工作,後來便沒有機會繼續做學問,不然也可以象他的那些同學一樣去當個大學教授什麼的。黃曙輝十五歲開始寫詩,後來也嘗試寫小說和散文、報告文學之類,但直到90年代初才開始產生一點影響。有報告文學、散文《槍魂》、《“中國牌”專家》、《船之夢》、《越過四季》等一批作品在全國全省各類評獎中獲獎。出版過幾本理論著作,發行量卻不小。那時候,黃曙輝對於理論研究很感興趣,300多篇心理學、美學、人才科學、管理科學方面的論文被《行為科學》、《中國管理科學》等報刊雜誌發表。文學方面,現在出版過散文集《四季情緣》,報告文學集《槍魂》《先鋒之歌》等,今年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厚達560頁的詩集《荒原深處》,獲得廣泛好評,引起了詩歌界和評論界的重視。
散文集《四季情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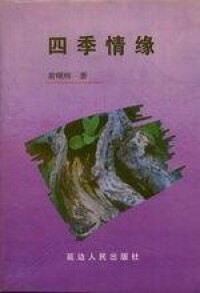
黃曙輝
詩集《荒原深處》

黃曙輝
黃曙輝是一個激情洋溢的人,對於詩歌有著與生俱來的喜歡。他教過書,做過宣傳工作,在組織部門幹了十多年,當過組織部長、紀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現在是一個堅定的綠色環保主義者。但是,他在從政的同時一直對詩歌創作保持極大的熱情。最近幾年來,詩歌創作出現了井噴的勢頭,連續在《文藝報》《人民日報》《中國詩人》《詩潮》《星星》《詩歌月刊》,《文學界》《散文詩》《天津文學》《上海詩人》等眾多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組詩。有評論家甚至說,2009年是詩歌界的“黃曙輝年”。最近,湖南的報紙和刊物《湖南日報》《當代商報》《三湘人物周刊》等一批報刊連續對他的詩歌創作給予了高度關注和評價。黃曙輝詩風豪放,受美國詩人惠特曼、智利詩人聶魯達等人的影響較大,總體來說屬於豪放派詩人,但是近期的創作呈現了多樣化的風格,更加深刻厚實,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情和無奈。
鶴舞盛世:古老城市的性靈書寫
――益陽詩壇“三劍客”印象記
聶茂
序曲:劍之美彰顯城市骨力
我堅信每一座城市都蘊含著綿延的詩意。益陽歷史悠久,人文鼎盛,“背靠雪峰觀湖浩,半成山色半成湖。”益陽詩壇三劍客——郭輝、馮明德、黃曙輝就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用各自的靈氣、才氣、智慧和感悟抒寫著對故土深沉的愛。
益陽別稱為“銀城”,《禹貢》記載著“唯金三品”,銀與金、銅並列其中,但銀沒有金的奪目華彩,沒有銅的深沉古樸,它有的是明月般的明亮、俊朗。益陽市花是紅紅火火、吉祥富貴的刺桐花,“穠英斗火欺朱槿,棲鶴驚飛翅憂燼”,刺桐花似火紅辣椒,樹上有刺,在防守中炫耀著。也許是銀的內斂、柔和、淡雅、柔韌的質感,以及刺桐花炫耀與防守兼具的特徵,造就了益陽三劍客的作品在含蓄中張揚,在明輝下暗香的文風質感。
劍,是一種古兵器,更代表一種文化。劍,觀之寒澈,舞之輕盈,出鞘鑒日月,入鞘藏風雷。劍客,藏則如路人甲乙,寄情酒肆,聲色內斂;露則豪氣沖雲干,狂放不羈,詩仙李白當屬此類。古人常謂人劍合一是至高境界,如今益陽詩壇的三劍客也痴心不改,孜孜以求,漸入創作佳境。
一座城市沒有文化無異於一座空城,一丘沙漠。劍之美能夠彰顯城市的骨力。益陽之所以能從中國城市的星座中獨發異彩,與周谷城、周立波、周揚“三周”有關,而延續他們文化血脈的除散文家葉夢、小說家劉春來、裴建平外,益陽詩壇三劍客以群體的力量令人刮目。三位詩人懷著對文字的敬畏與摯愛、懷著對詩歌的推崇與堅守、懷著對時代的責任與謳歌,以心馭筆、以筆寄情、以情抒懷,在湖南乃至中國文壇,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
郭 輝:長劍善舞 半仕半詩半書生
郭輝的詩像白樺林一樣乾淨、純粹,散發著春日剛剛翻耕過的泥土氣息,他深切地熱愛著“永遠的鄉土”,在這片鄉土上“吮吸愛的芬芳”,眷戀著桃花江畔“美人窩的風情”。鄉土、美人,偉大浪漫主義詩人屈原筆下的“香草美人”,始終都是詩人抒情感懷的原動力。從郭輝的文字中,我能看到蚯蚓在泥土中跋涉,花草在一場及時雨後的伸展,女人在鄉村小調中扭動曼妙的身段……他筆下的鄉土意象是粗麻布質地,厚重、深沉,古樸中透著清新。
說郭輝長劍善舞是比較恰當的,他以詩名世,卻在小說、散文創作中也有不俗的表現。他有著繁瑣的行政工作,卻並沒有給創作戴上了腳鐐。市文聯主席和市作協主席的身份,讓他有了“領頭雁”的壓力,卻也讓他化壓力為動力,從一個人在鄉土之上的獨舞,變為一群人在城市之上的群舞。
我與他有同窗之誼,這種友誼換來的是恆久思想的交融與理解,早在1989年,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就讀時,在時代暴雨的背景上,雕刻著我倆難以忘懷的溫馨記憶。現在,他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詩者自由,詩人的眼睛看到的是通透與純粹,是文字深處恆動的人性,詩人是由人性的光輝來觸摸他的世界。
郭輝親切地寫道:“冬初老倌的眼涼了,心涼了,血涼了/他不相信外面會沒有人穿草鞋,他要去城裡看看了。”與其說時間在冬初老倌的記憶中停止了,不如說時代的快節奏和轉型期間的價值取向讓他有些難以適應。詩人溫情呼喚的其實是對逝去歲月的美好回憶,是一抹潮濕的文化鄉愁。在詩中,郭輝表現得有如一個鄉下未見過世面的野小子,自由揮發著無意間闖入了城裡“大詩界”的種種驚喜、悲苦、興奮、惆悵,他把帶著一種野草泥土味兒的情愫淡淡地印入到了詩里;“無意中,把一根竹竿插進土裡,過了些日子,竟長出幾片綠葉來/山地,確實是很肥呢。”
是啊,正是肥美的鄉土孕育了郭輝的詩情,結出了累累碩果。郭輝的根在鄉土,如他所言,他的血液里流淌著無法去掉的土腥味,曾經毫不起眼的菜園,已然成為他無法忘卻的詩園。
郭輝善思考,會讀書,現在從事行政工作,而我則在中南大學三尺講台上執教,當年的豪情藏進了酒窖,越釀越香。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不再是純粹的詩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不同的人生經歷給予我們不同的風景,但無論在哪裡,無論做什麼工作,只要心中有詩,自然就能“春暖花開”。我期待郭輝筆下的新鮮鄉土能夠更加青翠欲滴,生機勃勃!
馮明德:仗劍直擊 意氣風發著鴻文
這些年,馮明德做了很多的事情,但也可以說,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將一份小小的詩歌雜誌打磨成全國聞名的散文詩創作集散地。他把一個在省會城市都難以做的事情,他不知疲倦地做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作為《散文詩》雜誌的掌門人和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馮明德長得乾瘦乾瘦的,看上去很“藝術”,很“前衛”,頗有些披頭士放蕩不羈的風範,而身板卻像風中的竹竿一樣令人擔心。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做事很執著,很大氣,很豪邁。他倡導《散文詩》的辦刊宗旨,力求內容和形式完美的統一,讓刊物真正做到高度的“凈”和“清”。在他的執著努力下,《散文詩》被詩壇譽為“生活的一方凈土,心靈的一泓清泉”。他定位《散文詩》的個性是“精品化、大眾化、禮品化”的純文學。他是竹,寧折不彎,在純文學舉步維艱的今天,硬是為《散文詩》開創了一片新天地。
我跟明德兄交往頗久,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在湖南日報做記者的時候,當時就採訪過他的前任鄒岳漢先生和他,得知他們曾干過將雜誌放在板車上一個一個書攤去推銷的苦活兒,從中深切地感受到在一個地市級做一份純文學雜誌的艱難與不易。也就是從那時起,明德兄的辛勞和詩人意氣就像他布難苦難的臉一樣,深深地印進了我的腦海。
明德兄說,散文詩,是穿著散文的外衣,蘊藏的是詩的靈與肉。如果說散文詩滴著的是散文的淚,更多的則是淌著詩的血。有朋友說他人生最大的收穫是:幹了一件自己喜歡乾的事。此話委實不假。
如果說,明德兄行走江湖,仗劍直擊的是他的編輯家身份的話,那麼,當他搖身一變而為皇泯時,他創作的詩歌則如洪鐘大呂,主題宏大,題旨深遠,令人感佩。他的文與自由奔放的散文詩融為一體。例如,《七隻笛孔洞穿的一支歌》,就是一部帶有史詩色彩的長篇散文詩,是生命與靈魂的交響曲。全書以抒情的筆調進行詩化的敘事,貫穿著一種悲壯純美的高貴情操,超越了個人感情悲戚的局限,提升了人類追溯生命本源、文化和歷史根脈的那種堅韌、昂奮。
作為明德兄的又一力作,他寫出了氣勢恢宏的史詩般巨制《國歌》,文本所表現出來的歷史片斷,以及音樂、散文、詩歌、不羈、抗爭、破碎的畫面和危難的時刻,不時叩擊著讀者的心扉,撞擊著我的靈魂,讓我久久疼痛,欲罷不能。
黃曙輝:佩劍漫步 荒原深處有人家
黃曙輝的詩集《荒原深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自嘲自己是個樸實而可笑的幻想主義者。敢於自嘲的人一定很自信,也一定有自信的資本。但曙輝很低調,雖說身在官場,卻沒有沾染官場的虛偽、客套和善變。曙輝愛詩,不為臉上貼金,也不為名利謀,當然更不為稻粱謀。他愛詩,沒有功利,純粹因為喜歡,因為不舍。
正如曙輝在《荒原深處》自序中寫到的那樣:“一般來說,詩人不關心準確性,並且常常被當作模糊的精靈。因此他們的文字必須從他們那裡盜走,並且使之進入一種命運,這種命運使得它們‘值得’被思考。”這表明了他模糊意象的詩歌語言風格,他用看似隨機組合的語言片斷,組合成一種凌駕於現實之上的幻化命運——那是他對生命與生活的“拾”與“詩”。
我喜歡曙輝這樣的《穿著那雙土布鞋也走不出故鄉的夢》詩:“甚至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總是在故鄉的小路上走來走去/在城裡過了一些時間 我不要找/很多的理由 回到故鄉 其實/故鄉的小路早已被水泥覆蓋/小路上那一塊塊青色的石板/如遺失的文物 不知去向”。換言之,無論身在何處,無論身居何職,詩人始終沉醉於故園的那片泥土,和散落在泥土中的純樸、善良與唱詞。
曙輝原是執教鞭的,因而多了一份書生氣。於官場而言,這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曙輝似乎無意改變自己的個性。他默默地寫,執拗地寫,發狠地寫,彷彿只有寫作能夠釋放他的快意,只有寫作能夠伸展他的腰板,只有寫作能夠“意淫”他的夢想。我說曙輝荒原深處有人家,是指他在詩歌的荒原不停地跋涉,艱難地前行,而遠在深處的“人家”,終能在雨後的夜晚點亮油燈,炊煙裊裊,等待疲憊的遊子歸來。這溫馨的“人家”將註定會給痴情的追求者以熱烈的回報。
在我與他為數不多的交往中,他的誠摯,他的才情,他的刻苦,深深地打動了我。有人問我,為什麼喜歡一個並不出名的詩人的作品?我的回答很乾脆:曙輝的詩歌既有著惠特曼式的高昂,又著埃利蒂斯式的意象密集,還有著聶魯達式的硬朗,這是我從一開始就喜歡他詩歌的原因。曙輝現在也許還不很出名,可這又有什麼緊呢?這個佩劍漫步的詩人,說不定就有一首詩能將你的靈與肉刺得連痛都叫不出聲來呢!
尾曲:詩之靈充盈資江秀美
從序曲中的《劍之美彰顯城市骨力》到尾曲中的《詩之靈充盈著資江秀美》,這是一種創作苦旅,更是一種文化傳承;是創造的開始,更是審美的輪迴;是一首詩的終結,更是另一首詩的開始。
益陽詩壇三劍客,並不是一個詩歌社團,也沒有明確的詩歌主張與集體追求。說到底,是我將他們拉到一起的。但我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過於孟浪,更不是“硬扭”的結果。因為,在生活中,這三人不僅年歲相當不多,經歷、背景、追求和喜好等也有許多共同之處。尤其重要的是,同飲資江水,同居益陽城,他們便有了統一的摹仿對象――那就是養育他們的同一方水土。也許是詩人敏感而細膩的共性,他們不約而同地摹仿著益陽山水的靈動,摹仿前輩先賢的思慮,摹仿父老鄉親的樸實與狡黠,摹仿山鄉桃腳漢子的粗獷與桃花江畔沐浴女子的柔美,摹仿一隻鶴的靜默獨舞與一群雀的喧囂熱烈,以及一群山坡羊的安逸午後——總之,在這個雜糅的世界,值得人們摹仿的事物太多了,智慧在摹仿中進化,思想在摹仿中裂變。這種裂變的根本點還是源於對故土母本的“摹仿”,源於益陽“半成山”的壯美,源於“半成湖”的秀美。
在摹仿中超越,在超越中創新,他們的詩歌凸顯了內在的張力,摹仿增加了歷史的黏度與廣度,摹仿賦予了文化以氣味與質感,通過摹仿,三位詩人把益陽從古體詩詞的意境之美,引入到了現代詩歌的意象之奇,是漸進,也是一種巨變。
我欣喜地看到,已取得矚目成就的益陽詩壇三劍客並未停楫棄劍,他們正乘資水之舟,以詩為帆,以歌為槳,踏浪而行。他們在行吟中上下求索,一座城的意象符號,借一方山水註釋著詩人的完美世界——那串夢中不敗的故園刺桐花,開得正艷。
黃曙輝:與詩同行,猛烈噴發情感的火山
本報記者/朱斌城 攝影/龔永忠
人物簡介
黃曙輝,1960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現任益陽市環保局副局長兼黨組副書記(正處級)。自稱為“樸實而可笑的幻想主義者”,出版過散文集《四季情緣》、報告文學《槍魂》、詩集《荒原深處》等著作,詩歌主要發表於《文藝報》《人民日報》《中國詩人》《詩潮》《文學界》《散文詩》《上海詩人》《中國朗誦詩》《中國作家》《詩歌月刊》《星星》《天津文學》《安徽文學》《湖南作家》《文學風》等刊物。
人生·回歸詩歌
1960年出生的黃曙輝成長於物質貧乏年代,學漆匠、吹笛拉二胡等手藝,苦為生計勞作,除了毛主席語錄外無書可讀。偶然間看到一本註釋版的《宋詞一百首》,是他與詩歌的初次照面;15歲時在縣裡的刊物上發表了一首四句話的民歌體詩歌《我是小小氣象員》,是他詩歌創作的處女作;就讀公社高中期間,教語文的黃劍輝老師講授袁水拍的諷刺詩、馬雅科夫斯基的“樓梯詩”,是他第一次淺淺地接觸詩歌的廣闊世界。儘管18歲前從未真正走出過大山,黃曙輝心裡卻有夢想:要通過寫作改變命運。
1978年,邊教書邊複習的黃曙輝考上大學。鄉親們在公路上攔住了一輛拖煤車,他才得以坐在煤堆上走出大山上大學。進入大學,詩人蕭漢初等名師的系統講授,吳友雲、諸戈文、周軍軍、陳健君等一班同學幾乎通宵達旦地為詩瘋狂,大學圖書館里豐富的文學藏書,讓黃曙輝真正走進詩歌藝術大師的斑斕世界:莎士比亞、海涅、聶魯達、惠特曼、屈原、李白、郭沫若……天道酬勤,他終於成了學校歷史上第一個在學報發表論文的學生,論文名叫《試論新詩的散文美》。從此,黃曙輝開始寫作生涯,除詩歌創作屢見發表外,還先後出過散文集《四季情緣》、報告文學《槍魂》等。
因公務繁忙,黃曙輝曾停止詩歌創作十多年。2006年從南縣調回益陽市直單位工作相對輕鬆后,在詩壇沉寂多年的黃曙輝進入其創作的井噴期,“據他的夫人諶如介紹,曙輝每天至少寫一首詩,曾經還創下過一天十首的紀錄。果然,短短三兩年時間,曙輝的詩作就排炮、連珠炮一般轟上了《中國詩人》《詩歌月刊》《詩潮》《中國作家》《文學界》。不服不行。在一個飯局上,詩人郭輝就借著酒勁大發感慨:2009,詩歌的‘曙輝年”呀’”(摘自裴建平《激情和詞語編織的詩意人生》)。他新近出版的詩集《荒原深處》所收錄的470餘首詩,絕大多數便為近三年所作,顯現著詩歌這座情感火山猛烈噴發時所獨有的動人心魄!除了其一貫堅持的詩歌的整體性風格以外,這些詩歌也彰顯著表達方式的多樣性,既有現代派氣息濃郁的,也有平白如話的,有書卷氣濃的,也有類似民歌體的;同時,隱喻、反諷、象徵、誇張、通感、鋪陳等修飾手法在其敘事和抒情里都“有意無意地要跳了出來”!
身居官場,面朝詩歌式微的俗世,詩人黃曙輝無疑是孤獨的,然而,他也是積極入世的:他積極面對手頭的環保工作,狂愛攝影,對旅遊樂此不彼,開博客開得精彩以至於被文友們戲稱為“博導”,好友聚會時必定會肆意高歌,這種真性情和多彩生活狀態無形之中同其詩歌創作形成了一種有益的互動,他的詩歌是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靈魂的。
詩歌·吟唱人生
《三湘人物周刊》:評論界戲言,“青年寫詩,中年寫小說,晚年寫散文”,而您的詩歌創作軌跡卻顯得極為不同:您很早就開始熱愛詩歌並早有創作,中途因涉入官場而中斷10多年,近三年來卻彷彿“重出江湖”般佳作頻出,甚至“一天曾經創下過一天十首的紀錄”,這種高產與高質的能量從何而來?
黃曙輝:我覺得寫詩歌是不分年齡界限的,那種把寫詩歌人為地劃分年齡的做法並不科學。詩歌是一個人骨子裡的東西,是一個人對於美的東西的存儲,有時候也是積壓在內心深處需要噴發的火山。我從政時間長,那其實是一種很好的經歷,讓我對於社會深層的東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看問題的視野和一般的詩人有了較大區別,能夠從更高的更開闊的角度看問題。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寫的東西肯定至少在思想性方面要比一般的詩人或者自己年輕的時候寫的東西要深刻些。馬克思說:憤怒出詩人。我長期從政,看到了很多很好的東西,也看到了人性里最骯髒的東西,所以,有時候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自然會如同火山噴發一樣,讓一些積存在情感深處的東西噴發出來。10多年裡沒有發表詩作,不代表心靈深處沒有吟唱。而且,年輕的時候考慮發表的成分多,真正寫屬於自己的東西少;現在不同了,我不是特別考慮發表的事情,所以,只想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三湘人物周刊》:在詩集《荒原深處》的自序中您談到,“也由於詩歌,它讓我的天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面前,詩歌其實是很尷尬的”,這種打擊、尷尬分別指的是什麼?面對這些尷尬,您“並不後悔”並堅持“與詩同行”,做到這種人生境界與態度,僅僅因為詩歌是“最好的療傷藥物”嗎?
黃曙輝: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但目前似乎人們的功利思想越來越重。我說的打擊與尷尬,那是因為在官場許多人不懂詩,許多領導你別看他在台上發言講得頭頭是道,其實並沒有文化。所以,我生活在官場,我寫詩,在某些人看來就屬於另類,覺得沒有意義。假如你去參加一個行政會議,你帶本詩歌去看,別人一定會覺得好笑。所以,這樣的尷尬作為一個政界人士來說,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悶和無奈……詩歌藝術其實是一種最美的藝術,它能凈化人的靈魂,讓人們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保持內心的一方凈土,因而能更好地看待社會與人生,積極地生活,樂觀地生活,它勝過一切的藥物。所以,對於真善美的謳歌,對於假醜惡的討伐,絕對一直是我詩歌裡面不斷體現的東西。比如,在詩集《荒原深處》中的“春天寂靜無語”這一輯,我表面上主要寫環保題材,實際上也是對於某些無良官員與違法排污企業老闆的痛斥,詩歌是我釋放苦悶的閥門。我不屬於那種城府很深的人,路見不平,我必拔刀相助。我曾經寫過一首詩歌《劍舞長空》,表達的就是我內心的理想。我有時侯也故意迴避一些重大題材,但是有時候卻無法不全身心介入,比如汶川地震之後,我一個月無法寫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直到一個月之後才寫了《中國萬歲》,寫完之後大哭了一場,彷彿全身虛脫了一樣。
《三湘人物周刊》:故鄉是一個早已經被無數詩人青睞過的主題,而您的詩歌中卻樂此不彼的反覆出現水稻、小麥、土豆、蘆花、向日葵、溪流、田園、母親、父親、姐姐等詩歌意象,在《荒原深處》里,故鄉的詩歌部分被放到詩集的第一輯,故鄉在您心中的分量為何如此之重?此外,在您近期創作的《深入骨髓的痛讓我食盡人間草藥》組詩中,連牙痛、藥罐、蝸牛這類事物都可以入詩且讀來饒有情趣,它們是如何走進您的詩裡面的?
黃曙輝:故鄉是一個人最初成長的地方,無疑,故鄉的一切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一生。沒有故鄉的人是可憐的,就像精神沒有著陸的地方!生活中處處都是詩,但是很多東西放在詩里都是一種隱喻,不完全是表面的那些具象的東西。把一些最常見的詞語賦予完全不同也更豐富的含義,表達完全不同的感覺,那裡面就有了幽默的成分,這也是我詩歌創作的一種追求。
《三湘人物周刊》:您曾說過,“我相信詩歌是情感的火山,只有猛烈的噴發,才會產生動人心魄的效果”,您的創作追求的是“一首詩歌的整體效果”、“一種大氣的風格”,這種追求來源於什麼?
黃曙輝:世界需要大視野,需要大氣魄,人類共有的東西其實就是自然和美,以及愛,等等。我的詩歌單篇看,可能不屬於那種格言警句類的東西,我追求整體效果,就像長江大河,它能蕩滌一切,包容一切。我在我的詩集《荒原深處》的序言里說過,我的詩歌不是盆景,不是根雕,而是自由生長的樹木和野草,所以有時候我刻意打破一些詩歌寫作的條條框框,讓那些經過嚴格詩歌寫作訓練的詩人吐血。那種玩文字遊戲的做法不是我詩歌寫作追求的目標。
《三湘人物周刊》:關於您的詩歌創作,評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部分詩“有些失於節制”,應該在構思、意境營造、語境提煉上再下一些功夫,使之更精到些,精細些,精美些,精鍊些……這種“更精到些”的要求對您的整體詩歌風格而言,是否是一種多餘甚至有損你的詩歌風格?您今後的詩歌創作會如何實現提升?
黃曙輝:精雕細琢不是我的風格所在,我喜歡粗礫的東西,就像雕塑,刀砍斧劈,故意留下刀痕,而不是打磨得精細發亮。我只要離開自己那種大氣和不拘小節,自己都感覺到有些做作,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特色。但是,有人愛吃粗糧,有人愛吃細軟的食品,這都應該允許。別人對我的這個評價,其實也還是有許多有道理的地方,所以我近期的寫作稍微注意了一下,我覺得注意一下詩歌語言的精鍊還是有必要的。對於我個人的詩歌發展方向問題,其實是我很苦悶的事情,一直沒有完全想好。不過,不論怎樣變,我都不會寫那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我指的是,如果寫出來的東西連我們寫詩歌的人都看不懂、不喜歡,普通讀者會更不喜歡的。
《三湘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詩歌創作的整體生存環境?對於散文詩的創作,你曾提出一個觀點: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靈魂,在您看來,這個“三貼近”對於散文詩發展而言有著極為特別的意義?
黃曙輝:從整體上看,現在許多詩人的詩歌作品,技術上非常棒,語言也非常好,但就是難以產生影響,我覺得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詩人過於小我,不關心社會現實。這是最危險的。藝術有一個共同特點,必須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古人說“文以載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些絕對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與真理。一段時間以來,我看到散文詩創作出現了追求表面華麗的東西,遠離生活,這當然讓我納悶,感覺不可取,這也是我一貫的入世思想的體現。中國的詩歌從詩經以降,凡是能影響社會、被人廣為傳誦的,一定都是很好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作品。我還記得自己發表的第一篇詩作《我是小小氣象員》,採用的民歌體形式,只有四句話:我是小小氣象員,毛主席叫我來管天,不怕風吹和雨打,再苦再累心裡甜。那時候我在農村,沒有天氣預報,農民種地看天氣,都是完全依靠傳統的一些習慣看天氣,所以對於天氣預報居然很關注。我一開始就比較注意用詩歌反映現實生活,不喜歡無病呻吟。我最近的一些詩歌,尤其注意寫人性隱密的東西,對於時間、人性等等方面一直在進行觀察與研究。我想,等到我下一部詩集出版的時候,一定會比現在這本作品更好一些吧,希望不會讓喜歡我的讀者失望。
(原載湖南日報報業集團《三湘人物周刊》2010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