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耕路
劉耕路
劉耕路,男,本名劉景祿,著名學者,紅學家。

劉耕路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永恆話題。西方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的說法,據說原是歌德的話。在中國,《紅樓夢》也是說不盡的,已經說了二百多年,今後還要說下去。既然如此,我何妨在這篇自序中,再說說有關話題,或許對理解《紅樓夢》及其詩詞小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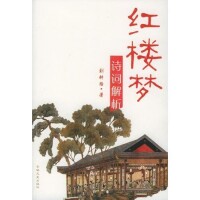
劉耕路作品
中國古典小說有所謂“四大名著”之說,指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實際上這四部著作的成書過程以及在類型和內涵上,均存在很大差異,價值也不相等,應該辨明。
《三國演義》署名作者是羅貫中,實際上“三國”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在民間流傳,到宋代通過藝人的表演說唱更為流行。羅貫中是在民間傳說及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的基礎上,又參考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史料,寫成了《三國志通俗演義》。
《西遊記》是在唐代以來民間傳說的唐僧取經故事以及宋元以來有關的話本、雜劇的基礎上創作而成。據學者考證,孫悟空的形象源於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西遊記》取材的《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去印度取經后寫的回憶錄,因此孫悟空的形象源於印度就不奇怪了。
準確地說,上述三部作品是經幾個朝代、許許多多人的集體創作,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只是最後完成者。
《紅樓夢》則完全不同,它一無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樓,是曹雪芹一個人的、獨出心裁的天才創作。魯迅先生說過:“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據我思考,《紅樓夢》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大突破。
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到描繪真實生活情態的突破。《三國演義》大到“赤壁鏖兵”,寫得大開大合;小到“蔣干盜書”,寫得綿密入微。《水滸傳》大到“三打祝家莊”,寫得機關迭出;小到“宋江殺惜”,寫得曲折有致。《西遊記》寫妖魔鬼怪,磨難百出,吸引著任何年齡的讀者。人們讀這些小說,無不被其故事情節所吸引,為“欲知後事如何”而廢寢忘食。
在《紅樓夢》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這裡沒有什麼曲折離奇的情節,大如“秦可卿出喪”、“賈元妃省親”之類,小如“良宵花解語”、“靜日玉生香”之類,生活是什麼樣就寫成什麼樣,恰如作者說的“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 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勝。
第二,由彰顯社會倫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從其形成伊始,就是倫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無所不在。以《三國演義》來說,劉備的“仁”,關羽的“義”,趙雲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為社會樹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詐”,周瑜的“褊狹”,劉禪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員”的意味。
《紅樓夢》則正如空空道人所說,“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這些異樣女子即是大觀園群芳,她們或貴或賤,或剛或柔,或傲或謙,或敏或訥,都稟性善良,天真爛漫,整日簪花鬥草,吟詩作賦,對即將到來的家族敗落的厄運毫無覺察,保持著人的生活的“原生態”。
第三,由演繹類型化模式,到塑造個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敘述的是英雄傳奇故事,著意刻畫的是橫空出世的傳奇英雄。如關羽是忠義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錯誤和缺陷,“漢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聖”孔子並列的“武聖”,無比崇高。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東風之類的情節已經使他成為呼風喚雨的神人,讀者對他須仰視才可見。武松、魯達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幾乎完美無缺,和普通人有距離,因而可敬而不可親。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滅怪,威風凜凜一路殺往西天,當然更是英雄。
相反,讀《紅樓夢》時,我們就像回到現實世界。養尊處優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貴,但寬容和善,喜歡劉姥姥,和這個農村窮老太婆很談得來,並不相距十萬八千里。王熙鳳這個桀驁不馴、有權有勢、令榮寧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輕貴婦,我們似乎也不陌生,彷彿在哪裡見過。釵、黛、湘等貴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個個性情鮮明,在讀者眼中仍是常人。至於像焦大那樣喝大酒、吹大牛,以當奴才驕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隨便都可找出來,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著墨不多的他都寫得那麼活靈活現。正如魯迅所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的“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評價,是對《紅樓夢》為中國小說創作開創之新局面的準確肯定。
《紅樓夢》敘述的是中國社會的真故事,刻畫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物。鳳姐、寶釵一流的人物,在我們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見的,但趙雲、武松一類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裡去找?
《紅樓夢》的最動人之處即在於這些人物的遭際和命運。

劉耕路教授
第五回里《紅樓夢引子》是這樣唱的: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在不可抗拒的命運面前,難以抑制的悲憤、惋惜、眷戀、悵惘而又無可奈何的情懷溢於言表。在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招待賈寶玉的茶名叫“千紅一窟(哭)”,酒名叫“萬艷同杯(悲)”,《紅樓夢》要說什麼,還用解釋嗎?
始於《易經》的中國傳統“否泰交替”的樸素辯證法觀念,在曹雪芹的世界觀中佔有重要位置,也是他解釋和批判社會現實的思想武器。在《紅樓夢》第十三回里,作者借秦可卿臨死給王熙鳳託夢,說出一個重要道理:
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
她還說,“否極泰來,榮辱自古周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子孫不肖、後繼無人,是榮寧二府的根本性悲劇。《紅樓夢》寫到賈家五代人,恰如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說的,“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代創業,第二代守業,第三代開始墮落,第四代無惡不作,第五代連作惡都低能了。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這個傳統世家、百年望族破敗的命運已是無可挽回了。
相對於腐敗的男性貴族生活和外部的惡濁世界,與外界隔絕的大觀園倒是一塊純凈的天地。作者在這裡用了大量的筆墨描寫了一大群不同檔次、不同類型的聰慧、美麗、純潔、善良的女孩子,描繪了她們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美好生活,就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樓夢》是一首女兒們的頌歌。但她們都沒有好命運,隨著大家族的破敗,火炎昆崗,玉石俱焚,與家族一齊歸於毀滅,就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又是一首女兒們的輓歌。
悲劇,是以極其嚴肅的態度探索人在自然和社會中的位置與作用,提出人生處境的種種問題。《紅樓夢》就是要探索人生的意義和人的命運問題,提出一連串問號,雖沒有答案,但足可令人思索和玩味。魯迅說得更直截了當:“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大觀園的最後結局不是恰恰如此嗎?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悲劇可分三類:人為的悲劇、偶然的悲劇、必然的悲劇。這第三類“必然的悲劇”是指由於種種社會關係交互作用必然導致的凄慘結果,《紅樓夢》即屬於這一類。
曹雪芹在其短暫且浮沉不定的一生中,深刻地體驗到命運的無情和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他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在動,都在變,都在向其對立面轉化,所以借丫鬟小紅之口說出了“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這樣的“悟道”之語。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塊大石上,從頭到尾讀完《石頭記》,發現“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竊以為這裡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頭對話時又提出:“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雲無朝代年紀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藉此套者,反倒新奇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
作者有意隱去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因為書中蘊含的主旨和審美對象,即“事體情理”,無代無之,無地無之,超越時間,也超越空間,是永恆的存在。這個主旨不容易領會到,所以作者才有“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的喟嘆。《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是不會有這樣的擔心的。《三國演義》開頭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楊升庵詞)的感慨,同類的感喟在歷代詠史詩中並不少見,詞雖然精彩,但不算新鮮。
曹雪芹的擔心並不多餘,現在還有某些所謂“揭秘”式的紅樓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時空,還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實在是對《紅樓夢》藝術生命的扼殺。
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對《石頭記》有一句評論:“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情詩詞倒還全備。”我們都知道,全部紅樓大部分筆墨寫的就是“家庭閨閣瑣事”,這裡把“閑情詩詞”和它並列,可見並非“閑情”,而是在書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也是在第一回里,落魄書生賈雨村在甄士隱書房,面對中秋朗月思念丫鬟嬌杏,口佔一首五言律,即“未卜三生願”那首。脂硯齋在甲戌本《紅樓夢》這首詩下有一條雙行夾批:“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有傳詩之意。”深知《紅樓夢》寫作就裡的脂硯齋的這句話,應該引起我們特別重視,即作家不只是讓你讀他寫的故事,還要你欣賞他的詩作。在第二回開首“詩曰”之下,還有一則脂批:“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明確指出並肯定了曹雪芹出眾的詩才。
“偉大作家曹雪芹”,這話經常掛在大家嘴邊;“傑出詩人曹雪芹”,大家恐怕還說不習慣,至少現在如此,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曹雪芹沒有專門的詩集傳世,在《紅樓夢》之外甚至沒有一首完整的詩流傳下來,但他的朋友們留下的筆墨卻反覆說到他和詩的關係。曹雪芹移居到京城西山後,結識了村塾先生張宜泉,常聚會於蒲牖蓬窗,成為詩文摯友。張宜泉在《題芹溪居士》的小注中說“其人工詩善畫”,其詩句“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為之作了註腳。這位村塾先生在另一首詩《懷曹芹溪》說:“何當常聚會,促膝話新詩”,看來討論新詩創作是他們快樂的生活內容。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更有“愛君詩筆有奇氣”、“知君詩膽昔如鐵”、“牛鬼遺文悲李賀”等詩句讚許其非凡的詩才。敦誠在《佩刀質酒歌》中,對曹雪芹有這樣的描繪:“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不僅詩酒佯狂的形態呼之欲出,還透露出雪芹拙重、鋒利的詩歌創作風格。
《紅樓夢》及其全部詩詞韻語,都是特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註釋。
曹雪芹出生於一個顯貴的官僚世家,其祖父曹寅曾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等官職,為人風雅,喜交名士,為江南文壇領袖,主編過《全唐詩》,還有《楝亭詩抄》等著作傳世。在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文化氛圍的家庭里,曹雪芹少年時代受到過最為良好的教育,再加他本人的天分,成為文化奇才。
就其蘊含的所有文化因素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以稱為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史學思想、文學思想等等,在書中隨處都有體現。傳統文化的各種表現樣式,包括詩、詞、曲、賦、歌、贊、誄、偈、匾額、對聯、尺牘、謎語、笑話、酒令、參禪、測字、占卜、醫藥以及詩話、文評、畫論、琴理,在《紅樓夢》中應有盡有,無所不備。《紅樓夢》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迹。
為了理解和欣賞書中大量的詩詞韻語,也不妨效法書中的香菱,學學詩詞格律,看看《平水韻》,讀讀詩話詞話,這樣才能判別優劣,並領略《紅樓夢》詩詞韻語的精深微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