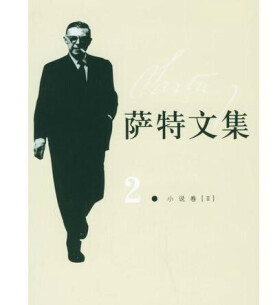存在主義文學
二十世紀流行於歐美的文學流派
存在主義文學是20世紀30年代末在法國興起的以宣傳存在主義哲學為目的的文學流派。隨著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在歐美各國的廣泛傳播而對各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存在主義文學代表人物為法國的薩特和加繆。薩特繼1936年發表哲學著作《想象》后,1938年發表了劇本《厭惡》,通過文學形象表達了他對人生和“存在”的看法。他認為“存在”即“自我”與客觀現實永遠都是對立的,不可能統一,客觀事物和社會總是與人作對,處處威脅著自我,認為“他人就是我的地獄”,恐懼、孤獨、失望、被遺棄等等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1942年加繆的具有同樣傾向的小說《局外人》問世,引起很大反響。評論界認為薩特和加繆的小說代表著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存在主義文學的誕生。
在藝術上,存在主義文學寓高度哲理性於文學作品之中,而不求情節的複雜性和曲折性,著重對主人公的精神狀態展開哲理性分析。在小說、戲劇、散文等方面存在主義都有許多有影響的作品。
存在主義文學是二十世紀流行於歐美的一種文藝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義哲學在文學上的反映。存在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流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主要表現在戰後的法國文學中,從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達到了高潮。存在主義文學是現代派文學中聲勢最大、風靡全球的一種文學潮流。
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是丹麥人克爾凱戈爾。

存在主義文學

存在主義文學

存在主義文學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另一大將。他並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作家,但他的作品瀰漫著濃厚的存在主義氣息。他的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1945年)、《誤會》(1944年)以及散文集《西敘福斯的神話》等,都揭露了荒誕世界里的荒誕人生:現實世界無非是一個一無可為的荒誕世界,人的存在也是如此,人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意義都喪失了著落,人的存在還有何意義。
小說描寫一個擺脫了資產階級陳規陋習羈絆的女性,是存在主義文學中的新人物。
此外,雷蒙·蓋蘭、莫里斯·梅洛·蓬蒂、班雅曼·豐達納等作家也深受薩特的存在主義理論和作品的影響,他們的作品顯示了存在主義的風格,是存在主義的邊緣作家。
存在主義的旗幟也飄到了歐美乃至東方一些國家的文學界。秘魯的巴爾加斯·略薩,日本的安部公房和開高健,印度的尼勒默爾·沃爾馬等都具有明顯的存在主義傾向;義大利的莫拉維亞、美國的諾曼·梅勒和索爾·貝洛等創作中亦可辨出存在主義的蹤跡。
從60年代起,存在主義作家已經失勢。到了70年代,存在主義作為一支文學流派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了。
存在主義的先驅者是丹麥人克爾凱戈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存在主義在德國開始流行,它的主要代表是海德格爾陽雅斯貝爾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存在主義在法國思想界佔據重要地位,一些作家通過文藝作品進行宣傳,擴大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六十年代后,存在主義思潮被其他新的流派所代替,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就是存在主義文學的變種。
克爾凱戈爾生於1813年,從小受到父親的嚴格管教,並且遺傳了父親的宗教憂鬱症。
由於得了憂鬱症,他覺得自己必須解除婚約。但此舉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產階級的諒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受人唾棄和恥笑的對象。後來他逐漸也厭棄人也、恥笑世人,並因此而逐漸成為後來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敵”。
他在晚年時,對於社會更是大肆批評。他說:“整個歐洲正走向破產的地步。”他認為他生活在一個完全缺乏熱情和奉獻的時代。他對丹麥路德派教會得了無生氣尤其感到不滿,並對所謂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無情的抨擊。對於克爾凱戈爾而言,基督教對人的影響是如此之大,而且是無法用理性解釋的。因此一個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種“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種程度”的態度。耶穌要不就是真的在復活節復活,要不就是沒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復活,如果他真的為我們而死的話,那麼這件事實在深奧難解,勢必會影響我們整個生命。
對克爾凱戈爾而言,活在‘宗教階段’就等於是信奉基督。不過對於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物。盛行於20世紀的存在主義就是受到這位丹麥哲學家的啟發。
存在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作家有:法國的讓一保爾·薩特(1905~1980),阿爾貝·加繆(1913·1960),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等。薩特是存在主義的集大成者。阿爾貝·加繆的代表作《局外人》(1942),描寫莫爾索對一切都無所謂,甚至對死刑都等閑視之的生活經歷。以他的冷漠、局外人生活態度,表現世界存在的荒謬性,及其人物對世界秩序的精神不安與絕望心理。《鼠疫》(1947)是加繆的頂峰之作。通過鼠疫流行中人們的不同態度,表現重大的人生哲理。成功塑造了里厄醫生這樣一個與鼠疫,即與法西斯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正面人物形象,展示世界存在的荒謬與罪惡,人類充滿危機和無盡的災難,只有選擇正義才是人類生存的唯一出路。波伏瓦的代表作品有《女客人》(1943)、《大人先生們》(1954)。其他具有明顯存在主義傾向的作家有:美國的諾曼·梅勒(1923~2007)、索爾·貝婁(1915~2005),法國的雷蒙·蓋夫(1905~1954)、莫里斯·梅爾洛—蓬蒂(1908~1961),英國的戈爾丁(1911~199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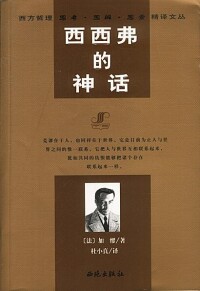
存在主義文學
西蒙娜·德·波伏瓦,二十世紀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性之一,存在主義學者、文學家,19歲時,她發表了一項個人“獨立宣言”,宣稱“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志”。波娃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烈的好奇心。西蒙·波娃一生寫了許多作品。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稱她為“法國和全世界的最傑出作家”;另一位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則在一次講演中說:“她介入文學,代表了某種思想運動,在一個時期標誌著我們社會的特點。她的無可置疑的才華,使她成為一個在法國文學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讓-保羅·薩特的終身伴侶。又譯做西蒙·波娃。全名為西蒙·露茜-厄爾奈斯丁-瑪麗-波特朗·德·波伏娃,出生於巴黎,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929年通過考試,和薩特同時獲得哲學教師資格,並從此成為薩特的終身伴侶。
波伏娃出身於比較守舊的富裕家庭,但她從小就拒絕父母對她事業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她和薩特相識后,兩人有共同的對書本的愛好,有共同的志向,成為共同生活的伴侶,但終生沒有履行結婚手續,並互相尊重對方與其他人的性關係,但兩人建立在互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礎上的愛情非常強烈,薩特去世后波伏娃寫了《永別的儀式》,是對和薩特共同生活的最後日子的痛苦回憶,流露出強烈的愛情。
波伏娃將存在主義哲學和現實道德結合在一起,寫過多部小說和論文,她的小說《達官貴人》獲得了法國最高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小說的主題在於說明知識分子不能為革命和真理同時服務,兩位主人公的革命目的和方法雖然不同,但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都失敗而犧牲了。此外她還寫過多部小說如《女賓》,《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名士風流》以及論文《建立一種模稜兩可的倫理學》,《存在主義理論與各民族的智慧》,《皮魯斯與斯內阿斯》等,提出道德規範與存在主義理論之間的關係,她一直被人們視為是第二薩特。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別》,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別,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徵都是社會造成的。男性亦然。這是她這本書的最重要的觀點。她在書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度是男人重新獲取權力,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認為婦女真正的解放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並向中性化過渡。她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極度暢銷,對造成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波伏娃去世后,和薩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
存在主義思想家的觀點並不完全相同,法國的存在主義基本上分成兩大派別:一是以西蒙娜·魏爾和加布里埃爾·馬賽爾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義;二是以讓·保羅·薩特、阿爾培·加繆、德·博瓦爾為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從文學的社會影響上說,薩特(1905-1980)和加繆(1913-1960)最為重要,他們都是法國的文學家。尤其是薩特,他是存在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人的前景》、《辯證理性批判》等,奠定了這種文學的理論基礎。
主觀意識決定存在的意義,但承認有獨立於意識的存在
“如果現象的存在不轉化為存在的現象,而我們又只有通過考察這種存在的現象才能對存在說點什麼,那麼,首先就應該建立那種使存在的現象和現象的存在統一的確定關係。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上所說的一切都直接受到對存在的現象的揭示性的直觀的啟示,建立二者之間的這種關係可能就容易得多了。倘若不把存在看成揭示的條件,而是把存在看成能以概念來確定的顯現,我們一開始就值得了,單靠認識不能為存在提供理由,就是說,現象的存在不能還原為存在的現象。總之,在安瑟倫和笛卡爾所謂本體論證明意義上存在的現象才是“本體論的”。它是對存在的呼喚。作為現象,它要求一種超現象的基礎。存在的現象要求存在的超現象性。這並不意味著存在是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我們已經看到現象不可能掩藏存在),也不意味著現象是一種返回到獨特的存在的顯象(現象只作為顯象存在,就是說,現象在存在的基礎上表達自身)。言下之意,雖然現象的存在與現象外延相同,卻不能歸為現象條件——這種條件只就其自身揭示而言才存在——因此,現象的存在超出了人們對它的認識,並為這種認識提供基礎。”
沒有任何普遍的道德準則能指點應當怎樣做:世界上沒有任何的天降標誌。天主教徒會說:“啊,可是標誌是有的!”很好嘛;但是儘管有,不管是什麼情形,總還得我自己去理解這些標誌。
人的價值高於一切,並自由選擇價值
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價值高於一切。個人與社會是對立的,但也是可交流,互相不能脫離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來的,客觀事物和社會總是在與人作對,時時威脅著“自我”。薩特在他的劇本《禁閉》中有一句存在主義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獄。”但存在主義並不是只顧自己一己之私,而主張對世界承擔責任,對社會“介入”。所以薩特說:“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是什麼呢?是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質;通過自由承擔責任,任何人在體現一種人類類型時,也體現了自己”。
貶低藝術的認識作用
存在主義者否定藝術的認識作用,認為藝術作品不能反映現實,只能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人的心靈的衝動,給人以“享樂”和感受的能力,使人的“非理性的感覺清晰、明確起來”。他們認為,藝術家的目的是創造自己的世界,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藝術地再現客觀世界。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存在主義文學的主要內容往往是描寫荒謬世界中個人的孤獨、失望以及無限恐懼的陰暗心理,但也激勵人們改變這些。
悲觀而積極的處世態度
存在主義文學乍看起來,都一種“悲”。但這不意味著對社會乃至一切絕望,陷入悲觀主義、虛無主義,而是積極應對,不論是海德格爾向荷爾德林那樣”詩意的棲居“,還是薩特的”介入“世界。他們重視過程,過程就是自己賦予的意義,而非結果,因為沒有什麼實在的結果,結果都是平等而荒謬的:"人的所有活動都是等價值的——因為這些活動都企圖犧牲人以使自因湧現——人的所有活動原則上都是註定要失敗的。於是沉迷與孤獨或駕馭人民到頭來都是一樣。如果這些活動之一戰勝了另一個,那不是由於它的實在目的,而是由於這活動擁有的對它的理想的目標的意識的程度;並且,在這種情況下,沉醉於孤獨的人的寂靜主義將戰勝人民的駕馭者的徒勞繁忙。"說:我首先應當承擔責任,然後按照我的承擔責任行事,根據那個古已有之的公式:“從事一項工作但不必存在什麼希望。”這也不等於說我不應參加政黨,而只是說我不應當存在幻想,只應當儘力而為。
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有薩特的小說《噁心》、哲理劇《禁閉》和加繆的小說《局外人》等。
存在主義文學主張哲理探索和文學創作相結合,以表現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為己任。這些作品大多數處理的是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題材,重思想,輕形式,強調邏輯思維和哲學思辨。
人並無先天本質
存在主義作家反對按照人物類型和性格去描寫人和人的命運。他們認為,人並無先天本質,只有生活在具體的環境中,依靠個人的行為來造就自我,演繹自己的本質。小說家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新鮮多樣的環境,讓人物去超越自己生存的環境,選擇做什麼樣的人。因此,人物的典型化被退居次要的地位。
三位一體
在文學創作中,存在主義作家提倡 作者、人物和讀者的三位一體觀。認為作家不能撇開讀者來寫小說,作者的觀點不應該是先驗的,還必須通過讀者去檢驗;只有當小說展現在讀者面前時,在小說人物的活動過程中,作者和讀者才共同發現人物的真面貌。這種三位一體的觀點,對歐美青年一代作家影響很大,後來,也為其他文藝思潮流派所運用。
中國早期對法國存在主義文學的譯介,可以上溯到1943年,在《明日文藝》上發表了展之翻譯的薩特的《房間》。不久,作家荒蕪和詩人戴望舒也翻譯了薩特的《牆》。40年代,存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文學的面貌出現,而且不是由哲學家,而是由法國文學研究家和現代作家來完成的。當時盛澄華、羅大岡、吳達元、陳石湘等人,發表了多篇文章,使得1947和1948兩年,成為中國早期對存在主義文學介紹最為集中的時期。解放后,1955年9月,薩特與波伏瓦作為“進步作家”應邀來華進行訪問。《譯文》雜誌為此發表了羅大岡對《涅克拉索夫》的評論和其翻譯的名劇《麗瑟》(即《恭順的妓女》)。到了60年代,由於政治因素,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在中國受到批判,但還是有一些存在主義作品被翻譯過來,文學方面,有孟安翻譯的加繆的《局外人》和鄭永慧翻譯的薩特的《厭惡及其他》。
改革開放以後,1978年先是《世界文學》發表了施康強翻譯的加繆的《不貞的妻子》,接著《外國文藝》發表了林青翻譯的薩特的《骯髒的手》,這是進入新時期后中國讀者接觸存在主義文學最早的兩部譯作。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當時正值中國強調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使得許多外國文學期刊競相介紹存在主義作品,出版界也緊緊跟上。1980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鼠疫》;到80年代中期“薩特熱”繼續升溫,僅1985年出版的就有:《薩特戲劇集》,《加繆中短篇小說集》,《局外人》,《西緒福斯神話》和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等,使這一年成為出版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的一個高潮。進入90年代后,存在主義作品繼續以“合集”或“文集”的形式出版,如秦天、玲子主編的《薩特文集》(三卷),丁世忠、沈志明譯的《自由之路》三部曲,李瑜青、凡人主編的薩特“文集”(一卷),沈志明、艾珉主編的七卷本《薩特文集》,郭宏安主編的《加繆文集》,柳鳴九、沈志明主編的《加繆全集》。還有《西蒙·波娃回憶錄》四卷等。由於LesMots是薩特獲諾貝爾獎的作品(儘管他拒絕了這份來自官方的榮譽),在中國至少出現了五個版本和四種譯名:《文字生涯》(有沈志明和鄭永慧的譯本)、《薩特自述》、《詞語》和《我的自傳:文字的誘惑》。此外,薩特的著名長篇文論《什麼是文學?》也出現在《現代西方文論選》(伍蠡甫)、《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袁可嘉)和《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朱立元)等多種研究資料叢書中。加繆曾因名著《鼠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該作品表現了面對災難、人們積極團結戰鬥的精神,因而在2003年春我國出現“非典”時再度熱銷,成為“瘟疫流行時期的希望之光”和“拯救心靈的最佳讀本”。
存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反映在文學上則又可謂一種文學流派。他認為,“存在先於本質”,“世界是荒誕的”,強調“人在存在中可以自由選擇”;它對傳統文學的“反映論”提出質疑,主張文學“介入”時代,反對順從主義,張揚新的人道主義。這些文學理念,為中國新時期文藝提供了理論資源,豐富了人們對文學觀念的理解和探索;而當年出現的“薩特熱”,正好適應了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由於經受了“文革”的毒害,對傳統價值和信仰產生動搖、迷茫,以致出現精神空虛。“存在就是合理的”,“理想太空虛,存在才可靠”等思想,當時不僅在青年中頗有市場,甚至對一些中國作家也產生了影響。
中國新時期對法國存在主義的評介,最有影響的當屬柳鳴九先生。早在1978年11月,他就在廣州“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上作了《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的學術發言,從理論、創作和社會活動三個層面,肯定了薩特的進步思想。在1980年接著發表的《給薩特以歷史地位》中,對薩特再次給予了肯定。他編選的《薩特研究》一書,為學界獻出了全面而豐富的研究資料,也為廣大讀者了解薩特提供了多種維度。此外,羅大岡、施康強、馮漢津和郭宏安等人,還有哲學界的一些學者,也都對存在主義的評介做出了貢獻。如施康強發表了《薩特的存在主義釋義》等文,郭宏安則是研究加繆的專家,他在1982至1989年間,曾在《讀書》上發表了四篇評論加繆的《局外人》等作品的文章。
當年對存在主義思潮的傳入也出現過爭議。以柳鳴九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薩特譴責種族主義,同情被壓迫的黑人,其進步性應予以肯定;而以歐力同、馮漢津為代表另一些學者,認為它宣揚頹廢觀,故予以否定。雙方後來達成的基本共識,還是對薩特文學思想的進步傾向予以認同。這場論爭,對促進存在主義文學在中國的研究,起到了開拓和深化的作用。從70年代末以後,中國對存在主義文學的研究,越來越走向深入。如鄭克魯的綜合研究、張容研究加繆、楊昌龍研究薩特、江龍研究薩特戲劇等,都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