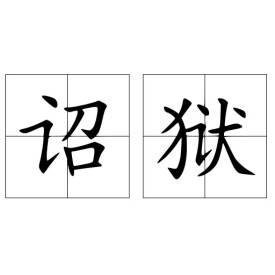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詔獄的結果 展開
- 詞語解析
-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圖書
詔獄
詞語解析
詔獄,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級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系獄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監獄,意為此監獄的罪犯都是由皇帝親自下詔書定罪。如明代的錦衣衛就是詔獄的一種,稱之為:“明之自創,不衷古制”。“詔獄”作為古代中國特有的“刑政”稱謂,在考察皇帝詔旨與國家獄政的關係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要理解“詔獄”,需先講清楚“獄”的含意。《金文詁林》說道,“稽之經傳,獄字恆指獄訟為言,不必指繫囚之地。”也就是說,“獄”並非只有牢獄之意,也可用來指法律案件。但單單講明“獄”的本意及引申意義,仍不足以說明“詔獄”的特殊性:其不同於一般之“獄”,關鍵在於“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詔獄”制度與皇帝制度的確立密切相連。秦王政令群臣議立名號時,臣下建言:天子自稱為“朕”,“命為‘制’,令為‘詔’”。裴駰《集解》引蔡邕《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詔”作為有特定含義、為皇帝所專用的字眼,實際上也有表明皇權尊嚴的神聖性和象徵性的意義。

詔獄

詔獄
“詔獄”興起的原由,兩漢典籍缺載。不過,《宋史·刑法志》中的記載,對我們認識問題或不無裨益:“本以糾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見。”時代相隔久遠,宋元時期的判定是否適用於兩漢呢?筆者傾向於贊同。實際上,漢代就有類似意義的話語出現。東漢順帝時,大司農李固就當時選舉人才中出現的弊病上書奏言。順帝接納其建議,“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後漢書·李固傳》)。從詔旨內容中可以看出:“詔獄”用以糾察為非作歹的官吏。這一點也應是“詔獄”特性所在,即糾察、懲治的對象與行為的特殊。比如,“詔獄”作為打擊諸侯王的重要手段,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餘悸,江都王劉建就有“我為王,詔獄歲至”(《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劉建傳》)的怨言。又如,“詔獄”多牽涉朝廷要人,文帝時的周勃、成帝時的王商,二人雖曾貴為丞相,但均受“詔獄”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獄吏之貴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的感嘆。
作為溢於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詔獄”制度合理髮揮作用的前提,並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願,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於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慾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所以,宋人張方平在《樂全集》中痛言漢、唐兩代之衰,“詔獄”之弊為亂政之首:
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移於下而人主受制於臣,而刑罰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樂全集·詔獄之弊》)。但人主大權獨攬就能避免“詔獄”之禍嗎?
明代的錦衣衛擁有自己的監獄,稱詔獄,或是“錦衣獄”,由北鎮撫司署理,可直接拷掠刑訊,取旨行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無權過問,獄中“水火不入,疫癘之氣充斥囹圄”,詔獄的刑法極其殘酷,刑具有拶指、上夾棍、剝皮、舌、斷脊、墮指、刺心、琵琶等十八種,史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嘉靖時刑科都給事中劉濟有謂:“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
萬曆年間,臨江知府錢若賡被明神宗朱翊鈞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終不得釋,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直到熹宗朱由校即位后才將他釋放。瞿式耜曾道:“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言:“恂一代秕政,為古今所無者。”顧大武的《詔獄慘言》也曾描寫楊漣在內的“六君子”在鎮撫司內被錦衣衛指揮僉事許顯純嚴刑拷問的慘狀。
從某種情況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禍,是皇帝制度衍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沒有有效約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時代,當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日漸膨脹時,權力的濫用是必然的事。皇帝並非生就精明能幹,權力被臣下竊取也是在所難免,而皇權也並非始終正義無私,也可徇私而行。那麼,徇私而行的權力,又如何能使合理、公正的國家運作機制建立?所以,與其指責佞幸所造成的“詔獄”之禍,倒不如切實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
作為溢於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詔獄”制度合理髮揮作用的前提,並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願,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於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慾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所以,宋人張方平在《樂全集》中痛言漢、唐兩代之衰,“詔獄”之弊為亂政之首: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移於下而人主受制於臣,而刑罰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樂全集·詔獄之弊》)。但人主大權獨攬就能避免“詔獄”之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