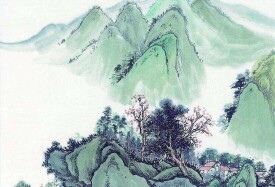答謝民師推官書
北宋蘇軾的散文
《答謝民師推官書》是蘇軾所寫的一篇書信體文論,作者用生動簡潔、舒展自如的筆墨,稱讚了謝民師的詩文,並藉此總結了自己的創作經驗。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雲流水”、“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篇書信是蘇軾文學創作基本觀點的表述。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景,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兩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1、奉違:指與對方告別。奉:敬詞。違:別離。
2、亟(qì):屢次。辱:委屈,謙詞。
3、具審:完全了解。審:明白。
4、受性:秉性,秉賦。剛簡:剛強質直。
5、學迂:學問迂闊。材下:才幹低下。
6、坐廢:因事貶職。累年:好幾年。蘇軾於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被放逐惠州,紹聖四年改謫儋州,元符三年,始內調,前後達七年。
7、復齒縉(jìn)紳:再列入士大夫階層。
8、還海北:這是指徽宗繼位,蘇軾遇赦,自海南島貶所渡海北還的事。
9、左右:本指左右侍從的人,這裡是對人的尊稱。雅:素常,指舊交情。
10、見臨:來訪。
11、傾蓋如故:一見如故。傾蓋:《孔子家語》記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並車對語,彼此的車蓋相依而下傾。形容偶然相遇卻如老朋友一般。
12、過望:出乎意料之外。
13、書教:這裡指書啟、諭告之類的官場應用文章。
14、質:這裡指體式。
15、文理:指文章的結構、脈絡。
16、文:文彩。
17、行:這裡指傳播。
18、辭:指語言。
19、夫:語首助詞。
20、疑若:懷疑。
21、妙:奧妙。
22、景:同“影”。
23、是物。此物,指所求得事物的奧妙。
24、蓋:大概是。
25、大可勝用:用不完。
26、揚雄:字子云,西漢著名學者。好:喜歡。
27、文:遮掩,粉飾。說:內容。
28、正言:直截了當地說。
29、雕蟲篆刻:雕琢字句的意思,比喻小技。蟲:蟲書,筆劃如蟲形的一種字體。刻:刻符,刻在信符上的一種字體。這是秦代八種字體中的兩種。
30、《太玄》、《法言》:均為揚雄所著。
31、類:這一類(雕蟲篆刻的東西)。
32、獨:只是。
33、音節:指辭賦的用韻、講求聲調等。
34、經:揚雄仿《易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自以為是“經”書了。
35、《離騷經》:漢王逸注《楚辭》,尊《離騷》為經,稱《九章》、《九歌》為傳。
36、風、雅:代指《詩經》。再變:風雅中一些抒寫憂怨之情的詩,漢人稱為“變風”、“變雅”見《毛詩序》。蘇軾以《離騷》比附風雅,故云“再變”。
37、賈(jiǎ)誼:西漢著名的政論家、辭賦家,著有《新書》。
38、升堂有餘:入門、升堂、入室,道德學問修養由淺入深的三種境界。升堂,喻學問已達相當的深度。升堂有餘,就是已達到“入室”的極深造詣階段。《論語·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39、以賦鄙之:揚雄因為賈誼曾作過賦,所以輕視他。
40、司馬相如: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同科:科,品類;同科,等類齊觀。
41、陋:識見低下。比:類。
42、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文忠是他的謚號。
43、愧悚(sǒng):慚愧和恐懼。
44、須:需要。惠力:佛寺名。法雨堂:當為惠力寺中的一個堂名。謝民師曾求蘇軾給惠力寺題寫“法雨堂”的匾額。
45、局迫:狹窄。
46、如教:照囑託辦。
47、方:將來。臨江:今江西省清江縣。
48、或:也許。
49、念親:思念父母。
50、峽山寺:即廣慶寺,在廣東省清遠縣,因山對峙江中,故得此名。
51、少留:稍稍停留。
52、愈遠:(離開您)愈加遠了。
53、以時:隨時。自愛:保重自己。
蘇軾啟:近來分別後,多次承蒙你寫信問候我,詳知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剛直、待人不周到,所學不合時宜、能力見識低下,因而遭貶多年,不敢再自居於達官貴人的行列。自從渡海北還,見到平生的親戚故舊,不知為什麼都象隔世人那樣生疏,何況與你沒有一天的交往,而怎麼敢希求彼此結為朋友呢?幾次蒙你親來我處,交談間情意親切如同舊友一樣,欣幸已極使人出乎意料,這簡直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
你給我看的信和詩賦雜文,我閱讀得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動著的雲和流動著的水一樣,本來沒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應該流動時就流動,不能不停止時就停止,文章條理自如,姿態多變而不受拘束。孔子說:“語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傳也不能流傳很遠。”又說:“文辭以能表達出意思即可。”那麼文辭僅僅在於表達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講究文采了,完全不是這樣。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風捉住影那樣困難,能使所寫的事物在心裡徹底明白,大概在千萬人中未必能找到一個,更何況在口說時和手寫時也能表達得很明白呢!做到這樣才可說是文辭能表達出意思。既然文辭能將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達,那也一定是富於文採的。揚雄好用艱深的語言,掩飾本來是很淺近的道理,如果直說出來,是人人都懂得的。這種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說的是雕蟲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屬於這一類。楊雄唯獨後悔作賦,是為什麼呢?他一生講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賦相比較只是在音節上略有改變,便稱為經,可以嗎?屈原作《離騷經》,是變風、變雅的發展,雖與日月競放光彩也是應該的,難道可以因其文體與賦相近似而說它是雕蟲小技嗎?如果賈誼能見到孔子,他的學行可以超過“升堂”而達到“入室”的境地:揚雄竟然因賈誼作過賦便鄙視他,甚至把他同司馬相如一樣看待。揚雄見識淺陋象這類的例子很多,這一點只可與明白事理的人談談,很難同一般人講清楚的,這裡因論述文章偶然說到這個問題。歐陽修說,好的文章如純金美玉,市上價錢是有規定的,不是人們靠口說就能定出它的貴賤。我的話很拉雜,對你哪能有益處,非常慚愧恐懼。
你要我為惠力寺法雨堂寫“法雨”兩字,我本不善於寫大字,勉強寫畢竟寫不好,加之船上地點狹窄不好寫,故未能照你的囑咐辦理。然而我正好要經過臨江,當往游惠力寺。或許惠力寺的僧人想讓我寫點什麼。一定寫上幾句題留院中,以安慰你思親的心意。今天到達峽山寺,稍作停留就離去。彼此相距越來越遠,千萬希望你隨時愛護自己的身體,其餘不一一細說。
文章寫於元符三年(1100)。當時謫居瓊州的蘇軾遇赦北還,九月底路過廣州。擔任廣州推官的謝民師多次攜帶詩文登門求教,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結下了情誼。蘇軾離開廣州后,兩人繼續書信往來,《答謝民師推官書》是答謝民師的第二封信。
全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從開頭至“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是依著一般書信的規格,開頭寒暄幾句,並從中流露出“坐廢累年”的感慨,同時也對謝民師的熱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別的高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發於客套寒暄,但卻又不僅僅流露於一般文人的那種故作姿態。作者在問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顯得真切誠摯。本來如“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這些話都屬於一般性的客套,但聯繫到蘇軾這個人,則就是出自內心肺腑了。蘇軾一生坎坷多難,遭際極不平常,晚年又被謫貶嶺南,歷盡艱辛。他雖然不失通達,但是一生磨難,也形成了他對命運的感慨。何況作者在這裡並不停留於這種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這裡緊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處身的環境,而且包含了內心深處的嘆息。既可與上相承,又復往下延伸,顯得貼切恰當,毫無斧鑿痕迹。接著又具體加以說明,“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這幾句話,聯繫上面,直涉自己與謝民師之間的關係,對於下面將要說的話,還起到一種烘托和對比的作用,這就使得“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這種本屬平常之理帶有一種不同尋常之情,樸實自然,卻又不落俗套。這一部分始於問候致意,結於友好相言,內容一致而又毫不重複,感情單一而又不顯呆板,何況其間一逆三折,已經曲盡變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轉折自然之妙,又具統一連貫之妙;既見思想感情的漸進發展,又見事項說明的環環相因。從這裡可以看到蘇軾為文巧奪天工的才情。
如果說蘇軾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幾句中已極盡承轉之妙的話,那麼在第二部分則是在自然的變化一致中充分表現了這一特色。實際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蘊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語言、結構承轉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但對於蘇軾來講,這些還僅僅屬於比較淺顯的形式方面的東西。東坡的自然還強調了能夠隨物賦形,能夠在寫作過程中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講的,不僅瞭然於心,同時要瞭然於口,瞭然於手,到達“辭達”的程度。這就要求一種更高的自然表達能力。
第二部分從“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到“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這一部分是整個文章的中心,作者暢談了自己對文章的見解。上半段敘議結合,旨在達理;下半段評說古人,力圖明事。作者先是從評論謝民師的文章作品入手,強調了“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可以說,這一命題正是作者對文章要求的一個根本法則,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內容的成分。作者以行雲流水為喻,生動而富於形象,大大增強了語言的表現力。雲與水不是靜止的,它們時刻都在運行之中;雲行水流,雖無一定的樣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規律。作者在《自評文》中對這一點另有過闡釋,“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這也就是說,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樣,因為事物本身是在不斷流動變化,所以導致了文章的寫作也要不斷變化,不能拘於一格。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文章顯得姿態橫生。作者根據這一命題,引發了以下的各種論述。對孔子的話“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及“辭達而已矣”的解釋,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擴展,其出發點亦無非是表達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這種表達方法又不限於靜態的描寫,而是予以創造性的發揮。作者雖在說理釋意,但並不滯留於夾角之中,所以從表面上看來,這裡講的文辭與達意的關係以及文辭表現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題,但實際上卻不然。作者恰巧是從自己的立意出發,但又絲毫不見拖泥帶水,也沒有遊離脫節,更看不到經意刻求的成分。而且這番對“辭達”內涵的發微之見,在最後“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處,又悄然回歸,如細細品味,就會感到其與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之說暗暗相合。這一段所表現出的自然,則主要在於作者對於客觀規律的準確把握以及對事物之間的各種關係的清晰認識。這體現了深入內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隨意揮灑,實際上卻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歸於一個基本命題,使之體現了統一的主旨。
緊接著的下半部分是蘇軾對具體作家的評說。以揚雄為例,指出“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這是以實例來說明“辭達”。揚雄的失誤主要在於沒有很好地掌握“辭達”這一要領,並不在於運用什麼形式,所以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雖從形式上加以變化,但由於沒有與內容相適應,因而,也不免為“雕蟲篆刻”之類。作為反證,蘇軾還羅列了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等作家,論其優劣,以明“辭達”的深刻內涵。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蘇軾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種把對客觀事物本質的充分把握與求得準確精當地表達相結合的“自然”。這一段話較多鋪張,但卻體現了作者的“行於所當行”的思想,雖然僅僅評論具體作家,但在意義上卻是一種與前面相銜接的必然。作者講“因論文偶及之耳”,實則是舉其典型加以說明。最後引用歐陽修的話:“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終於與前面相呼應,並且含意雙重,耐人尋味。
文章第三部分從“所須惠力法雨堂兩字”直到結束,又回涉謝民師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結,並報告自己的行程。這一部分筆墨簡潔,從整個書信的角度講,也是通篇結構的一個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於其間記敘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層次,則不失大家手筆。
縱觀全文,信的前、后兩段文字,是談與謝民師的友情,和對有關問題的答覆。中間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簡潔生動的語言,通過評論謝民師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對文章的見解。他指出寫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雲流水。與此相聯繫,又主張辭以達意為主,但又不能忽視文采。在蘇軾看來,“辭達”與有文采是完全統一的。要做到“辭達”,首先必須深切體物,對事物作深入的觀察和全面的認識,使之“瞭然於心”,然後要善於達意,用簡潔而準確的語言文字將它表達出來,使之“瞭然於口與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說:“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對雕琢,反對故作艱深,對揚雄提出了批評。蘇軾的這些見解是很有價值的,這也是他一生創作經驗的總結。這篇文藝書簡,要言不煩,善用比喻和具體事實並引用孔子的話來闡明自己觀點。全文筆勢流動,揮灑自如,很能體現蘇軾文章的特色。
明·陳獻章:“此書大抵論文。曰‘行雲流水,數語,此長公文字本色。至貶揚雄之《太玄》、《法言》為雕蟲,卻當。”
清·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貶揚以伸屈賈,議論千古。前半‘行雲流水’數言,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
清·劉熙載《藝概》卷一:“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