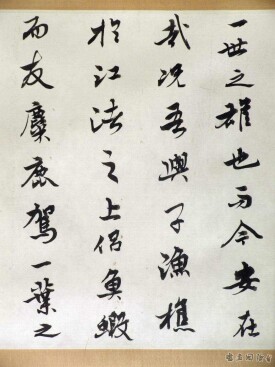散體賦
散體賦
興起於漢武帝之時,是一種綜合了詩、騷、散文等文體因素而被作家重新加工過的新型文體。散體賦的初具規模之作可上推至宋玉的《高唐賦》,枚乘的《七發》則是奠基之作,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則把散體賦的創作推向了成熟階段。
指漢代盛行的賦體作品,以主客問答的方式“鋪陳摛(chi)文,體物寫志”,雖散韻結合,但散文的意味較重,所以稱為散體賦。一般篇幅較長,規模宏大,所以又稱散體大賦。散體大賦是漢賦的主幹,所以散體大賦可以直接稱之為漢賦,一般來說,文學史上說的“漢賦”,都是指漢代散體大賦而言。
散體賦,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韻散結合,以體物為主,一般直書其事,鋪采摛文,排比鋪陳,多以問答體形式展開描寫,辭藻富麗,篇幅龐大。主要由諸子問答體、戰國縱橫遊說之文和楚辭演化而來。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宏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這段話充分肯定了賦的頌美作用,甚至將它們與《詩經》的《雅》、《頌》等而論之。它反映了東漢賦家對賦的重新定位。他們希望把賦納入國家的禮樂典章之中,使之成為文治教化之具。出於此種目的,東漢前期的賦家以極大的熱情頌揚朝廷的禮樂典章和文治教化之美,《兩都賦》就是從這一角度下筆的。這兩篇賦的創作和東漢初年關於建都問題的爭論有關。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曾遭到一些朝野人士的反對,到了永平年間,仍有《兩都賦》中所說的“西都耆老”盛稱西都的繁盛而鄙陋東都洛陽。《兩都賦》即針對這一現象而作。但班固在賦中並沒有就西都和東都的優劣展開評議,而是通過賦中的描寫“以極眾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在《西都賦》中,他先讓西都賓極力誇飾西都的宏偉富麗,這正是所謂“眾人之眩曜”的東西。《東都賦》一開頭就針對這個靶子進行批評,然後表示要告訴對方“建武之理,永平之事。”關於建武之理,主要寫光武中興,認為光武帝的勛業和行為,可比於伏羲、黃帝、湯、武、殷中宗、周成王以及西高祖和文、武二帝。而賦中讚揚的重點,則是永平之事。而永平之事,又主要寫其禮樂教化: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感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賦中對東漢的頌美是毫不掩飾的,尤其是對作者生活的永平時期,其讚頌更是無以復加。但這種讚頌既不是以東漢的繁榮富強去壓倒西漢,也不是停留在對帝王功業的謳歌,而是集中在東漢的德治之美和禮樂教化之隆,所謂“折之以今之法度”的法度,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依據,宣揚王道德治和禮義教化的思想。與這種思想傾向相適應,賦的風格也是雍容典雅的,賦的結尾又特意安排幾首四言詩,把這種頌美傾向和典雅風格推向了極致。
東漢前期還有一批賦家也表現出同樣的創作傾向。傅毅作有《洛都賦》和《七激》,崔駰作有《反都賦》,李尤有《函谷關賦》、《辟雍賦》、《東觀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等,也都重在描寫禮制之隆、教化之美和四夷賓服之盛況,以讚美東漢的中興和德治。
東漢中期,散體賦的創作出現多元化傾向,其中有娛樂之作,也有頌美和諷諫。張衡的(78—139)《二京賦》是又一次諷諫的嘗試。《後漢書·張衡傳》說:“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賦中假設憑虛公子和安處先生的問答。《西京賦》中先讓憑虛公子誇耀長安及西漢的豪侈富強,批評東漢“獨儉嗇以齷齪”,這些話等於為《東京賦》中的議論樹立了一個靶子。《東京賦》即針對上述觀點展開議論,尖銳地指出崇尚奢侈,“剿民以婾樂,”的危害。《二京賦》的鋪陳描寫規模更大,特別是更為廣泛地描寫了漢代的城市生活、風俗民情,其中對各種雜技百戲的描寫是研究漢代表演藝術的珍貴史料。賦中的議論也更多,更具針對性。但賦的基本體式仍是模仿前人,終不能改變勸百諷一的特點。
漢大賦的缺點是一味對客觀對象進行鋪陳描寫,而很少表現作者的內心世界和主觀感受;一律採用主客問答和層層排比,也略嫌呆板少變;賦中又往往愛用奇詞僻句,容易給人嚼蠟之感。但儘管如此,漢大賦在文學史上仍佔有重要地位。作為兩漢文學的代表,他們描寫了中華民族大發展時期的社會生活,反映了當時人們在各個領域開拓進取的業績,歌頌了國家的強盛和統一,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漢大賦中描寫了疆土的遼闊、山川的富饒、都市的繁華、宮苑的壯麗、以及田獵、歌舞、音樂、雜技、車馬、服飾等豐富多彩的對象,擴大了古代文學的題材領域。在表現技巧和語言運用方面,他們也為後人提供了經驗。特別是漢大賦主要是作為一種供人愉悅的藝術品而創作的,非常講究形式美,這對古代文學觀念的形成,對於文學脫離學術走向獨立,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