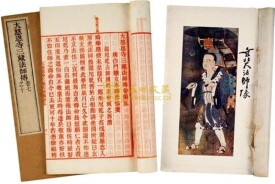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記錄玄奘生平事迹的書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亦稱《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三藏法師傳》、《慈恩傳》等。10卷。唐慧立本、彥悰箋,記玄奘生平事迹。因玄奘長期居住大慈恩寺,時人尊之為慈恩寺三藏法師。原5卷,垂拱四年(688)彥悰箋為10卷。前5卷記玄奘出家及到印度求法經過,大致依據《大唐西域記》 ;后5卷記回國后譯經情況,敘述受到太宗、高宗的禮遇和社會的尊崇等,尤以所上表啟為最多。其所記古代西域、印度及唐初以長安為中心的文化宗教情況,是極為寶貴的歷史資料。但書中玄奘的生年,沒有明白標出,為其不足處。此傳古代有回鶻文譯本,現存寫本殘卷,1930年出土於新疆。近現代以來,先後有法語、英語和日語譯本等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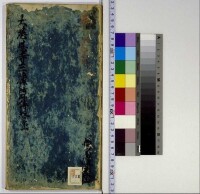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日本京都大學藏本
版本:1983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以支那內學院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影印《高麗藏》本和南宋《磧砂藏》本,但日本影印本之長處仍未能吸取,標點亦有失當處,轉不如影印本及內學院本之具學術價值。
本傳內容,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五卷述奘師出生、出家學歷、西遊行程及各地參學經過,后五卷述奘師回國以後和宮廷來往關係,譯經事業以至最後在玉華宮示寂等。各卷敘事起訖,大體如次:
第一卷記述奘師出生、出家、受戒、各地參學,發心前往印度求法,貞觀三年(629)由長安出發,過玉門關外五烽,度莫賀延磧,經伊吾,西行到達高昌的情形。
第二卷記述奘師從高昌西行,至阿耆尼等國,越蔥嶺到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過千泉、笯赤建等國,度大雪山過梵衍那、迦畢試國進入印度,經北印度濫波、那揭羅喝,健陀羅、烏仗迦那、呾叉始羅、迦濕彌羅諸國。又西南行經中印度波理夜呾羅、秣兔羅諸國,到達羯若鞠闍國的情形。
第四卷記述從伊爛拏缽伐多國順恆河南岸東行,經中印度瞻波等國。又東南行經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等國到羯[飠+夌]伽國,再西北行過中印度憍薩羅國,又東南行經南印度案達羅等國到達西印度伐臘毗國。又西北行經西印度阿難陀補羅等國,最後經北印度缽伐多羅國,折還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又東印度迦摩縷波國王慕師德義,遣使來請的情形。
第五卷記述奘師在那爛陀寺欲歸祖國,因應東印度鳩摩羅王請赴迦摩縷波國,又應戒日王請赴羯朱嗢祇羅國,赴曲女城大會弘宣大乘,赴缽羅耶迦國無遮大施會,從此辭戒日王東還,經中、北印度憍賞彌等國,度雪山,出蔥嶺經烏鍛等國到達於闐。在於闐向朝廷表奏還國,乃至到達漕上的情形。
第六卷記述奘師於貞觀十九年(645)正月入長安,謁太宗於洛陽,還長安弘福寺組識譯場,創譯《菩薩藏》等四經,並表進新譯經論及《大唐西域記》,蒙太宗制《大唐三藏聖教序》等情形。
第七卷記述東宮制“述聖記”,奘師居弘法院譯經以及大慈恩寺建成,另造翻經院,迎請奘師為寺上座,專務翻譯,乃至前後講譯造像請營經塔,並答中印度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書等情形。
第九卷記述顯慶元年表謝大慈恩寺碑成,又謝冷病中蒙賜醫藥,請定佛、道名位次第及廢僧尼依俗科罪。顯慶二年繼在洛陽積翠宮翻譯,表陳翻譯次第,又請入少林寺翻譯未許等情形。
第十卷記述顯慶三年從洛陽還長安居西明寺,四年遷住玉華宮,五年春創譯《大般若經》,到龍朔三年(663)冬全部譯成,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圓寂於玉華宮等情形。卷末附慧立的論贊。
作者問題
流行之說,認為現在傳世的十卷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前五卷為慧立所撰,后五卷為彥悰補作。如孫毓棠、謝方點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前言》說: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逝世后, 慧立為了表彰其師功業,便將玄奘的取經事迹寫成書,即本書的前五卷。初稿完成後, 慧立慮有遺缺,便藏之於地穴,秘不示人。到慧立臨終時,方命門徒取出,公之於世。到武則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玄奘的另一個弟子彥悰又將這五卷重加整理,另又自撰五卷(即本書後五卷),合成十卷,署名“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這就是現在的正文十卷。
按此說乃誤讀彥悰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所致。為便於分析,現先詳引其序說如下:
……(玄奘)法師懸弭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觽登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棲神之宅。故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履嶮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鷲山猴沼,仰勝跡以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蠧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振彼后之權豪。偃異學之高輶,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象,並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佑以元亨;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祀,達於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瞾(照)令宣譯。人百(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游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修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雲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按:此乃避唐太宗“世”字諱而用“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啟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鯁,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己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慚退,沈吟久之。執紙操翰,汍瀾腷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庶后之覽者,無或嗤焉。
據此序文的“……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可知此《傳》是記載玄奘一生的事迹功德,如果原稿五卷只述玄奘往印度的取經事迹,而不及其回國后在慈恩寺等寺院譯經傳教的功業,則何以能稱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呢?慧立之“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修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在其親身參予玄奘回國后的譯經傳教的事業之際。因此,不可想象其為玄奘撰傳,只記其得之耳聞的往印度的取經事迹,而不述其目睹的回國后的譯經傳教的事業。然後又說什麼“慮遺諸美”,這似乎就是明知不應“遺諸美”而故意遺美了。其實,古書多有經後人整理加插箋注而由一卷變兩卷之例。如《論語》原本為十卷,經後人加註為今本二十卷。《孟子》原本為七卷,經後人趙岐加註為十四卷。彥悰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由五卷變成十卷,其法亦是按照上述的箋注傳統,將一卷分變為二卷,再在各卷內加插箋述,不可能是另補加作五卷,而署名“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正如其《序》自稱:“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箋”或作”分”)為十卷。”所謂“參”“糅”和“錯綜本文”,就是在各卷本文加插箋述以及將各卷本文錯綜分柝之意。顯然非指可以截然分為前五卷純為慧立所撰,后五卷獨為彥悰補作的情形。又按今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格式,除其《序》於首行標明“沙門釋彥悰述”之外,乃於各卷首行標明“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這是具體表明由卷一至卷十皆為“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
再從各卷的首尾皆相連的結構看,也不可能把前後五卷分成兩人的作品。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五卷結尾記玄奘自西域回國將到長安云:
……(玄奘)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於闐使人及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宮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而其第六卷開頭接記玄奘自漕上被迎入長安云: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齎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眘、長安縣令李干佑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花幡等,擬送經像於弘福寺。人皆欣踴,各競莊嚴。……
顯然,這兩卷的連接說明其同出於慧立一人之手筆。慧立不可能寫到第五卷的結尾就這般收筆完書,留待彥悰如此從第六卷開頭接著補寫下去。
導致誤解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自第六捲起才有加插彥悰箋述之文,但這並不能作為第六卷以後各卷皆為彥悰續作之證,因為第八、九卷皆無加插彥悰箋述。下面就略析各卷加插彥悰箋述之文。第六卷開頭一直記事至如下一段話才加插彥悰箋述:
……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門。數十裡間,都人仕子內外官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門,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煙雲贊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毘,彌勒初升覩史,龍神供養,天眾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眾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鬱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彥悰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升覩史,龍神供養,天眾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慚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
這就是此卷之記述全文始終仍為慧立之本而彥悰只在其中間加插幾句“箋述”的具體例證。又如第七卷中間加插的彥悰箋述曰:
釋彥悰箋述曰:“自二 聖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
也是如此。至第十卷之末,則是在長篇的“釋慧立論曰”及稍短的“贊曰”之後,再加一段“釋彥悰箋述曰”為全書之結束。故筆者認為,依全書的體例格式,理論上凡前面不加“釋彥悰箋述曰”的句段,皆非彥悰之箋而為慧立的本文。當然,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因為在慧立的原五卷本於地穴挖出散佚到重新搜集,轉交彥悰作箋的底本,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以及很多人的轉手分合,其間應有被人有意或無意加工篡改的可能。至於彥悰的插箋理應是各卷皆有加插,何以目前只見第六、七、十卷有加插幾句“箋述”,而其它各卷皆無,這也有可能是彥悰或其它人有意或無意地把其它各卷的“釋彥悰箋述曰”標記語刪除了,使得彥悰箋文與慧立本文混合為一,無從分別看出了。
部分內容的可信性存疑
如前文所引現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本之序文所述,此傳的撰述隱現的曲折過程頗有奇怪可疑之點,向為研究者忽略。故應進一步提請大家注意研究討論。
首先,筆者認為其所謂“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之說就是一大奇怪可疑之點。當有比“慮遺諸美”更嚴重的顧慮或恐懼,或即此稿的內容公開會在其涉及的有關僧俗人士中引起很大的人事爭議糾紛,對作者慧立不利,才是使得其不但不敢在完稿之初即公諸世上,而且非要將該傳稿“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的原因。而在慧立行將逝世之際,此稿的內容所涉及的有關僧俗人士亦大都已故,不但事情的真偽問題已因當事人之死而無對證,已有的論爭是非得失勝負已因當事人之死而不會再爭論下去。因而其有意在身後才將一直秘藏的代表其一家私見暗撰的傳稿交由弟子傳世,顯然是有意迴避當事人及知情者對此傳稿的檢驗和論爭的。故其所述之事理為未經當時的有關公眾檢驗而缺少信史應有的公信力。特別是該傳目前的第八卷涉及慧立、明璿等僧人與呂才、柳宣、李淳風等世俗官僚就因明展開的一場大辯論,其經過及是非得失勝負的結果之記述,皆可謂缺少信史應有的公信力的一家之言,甚至有可能是後人加工改寫之文,值得懷疑之點不少。因為後來[宋]贊寧撰的《宋高僧傳?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便以有關慧立一家之言的資料,而傳其在“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並且稱因其致書批評呂才而使呂停止攻擊僧人的因明學說有誤,還進一步篡改今慧立原傳文之說,把支持呂才繼續論爭的柳宣都說成是受慧立影響而歸信並贊慧立云:
……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鼷鼠見釜灶之堪陟,乃言昆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眾云:“其外御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到了[元]釋念常撰的《佛祖歴代通載》卷十二進一步將以上引文有關栁宣之事改為:“栁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然而,慧立如果真的已戰勝了道儒兩家的論敵而能使之歸信,自己已成為“釋門之季路”,就不必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暗藏到臨終才讓它曝光面世。這決非如子路般的勇者英雄所為。即使是今傳世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也有很多是後人加工亂寫而不合史實的之點。
例如,卷八所記為“起永徽六年夏五月(公元655年6月10日)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三月(元656年4月29日)”的人事,而稱其首名論敵呂才為“尚葯奉御呂才”,此為一大不可信之點。因為據《舊唐書》卷七十九《呂才傳》載:“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敎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録》。”可知呂才在“永徽初”之前已官居“太常丞”。又同書卷二十八《音樂志》一載:“(顯慶)六年二月,太常丞呂才造琴歌白雪等曲。”由此至少可知由“永徽初”之前至(顯慶)六年二月這段時間呂才之官職為太常丞,再據《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一載:“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等為“從第五品下階舊正六品上,《開元令》改”,而“尚葯奉御”是位於其上的“正第五品下階”,且從來未見有其它唐朝史料提及呂才曾任“尚葯奉御”。
又如,同卷載顯慶元年春正月“壬辰(公元656年2月27日)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挍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挍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撿挍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挍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今查《舊唐書?高宗紀》載:“(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來濟為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河東縣男。”又載:“七年春正月辛未(公元656年2月6日)廢皇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公元656年2月7日)大赦,改元為顯慶,文武九品已上及五品已下子為父後者,賜勲官一轉,大酺三日。甲子(公元656年3月30日),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燕國公于志寧兼太子太傅,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為太子賓客。”“三月辛巳(4月16日),皇后祀先蠶於北郊。丙戌(4月21日),戸部侍郎杜正倫為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此可證上引顯慶元年壬辰(公元656年2月27日)之勅涉及的來濟、于志寧、杜正倫及李義府等人的職銜皆有微誤。由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至顯慶元年時來濟為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河東縣男,而非在此稍前的“中書令兼撿挍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于志寧在656年2月27日並非太子太傅,他要到3月30日才開始“兼太子太傅”。杜正倫為戸部侍郎而非“中書侍郎”。因此,有關記事及敕令,應是後來的加工編輯者對史料的研究不夠精細而留下的“馬腳。例如“中書令兼撿挍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之說,當取自《舊唐書?來濟傳》或與之相同的其它史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叚。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可見其“封南陽縣男”在五年,而改為“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河東縣男”則在“六年夏五月癸未”。又《舊唐書·李義府傳》載:“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為侯。”可見李義府在“兼太子右庶子”時,即同時“進爵為侯”,故應將“廣平縣開國男”改為“廣平縣開國侯”。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限於時間和篇幅,容后再另文詳細舉證。
中華書局點校本
中華書局再版推出的孫毓堂、謝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點校本是關於玄奘傳記研究的重要新成果,但是我們肯定其成果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該點校本存在著一些錯誤。現提出幾點商榷如下:
(1)“單開遠適,羅浮、圖澄”之誤點
該點校本卷八云: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恆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談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
按:其中“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標點明顯錯誤。單開人名也,梁代慧皎的《高僧傳。神異》上記載:“單道開,姓孟,敦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筆者認為,上文的“單開”即單道開之名省掉“道”字,實是一人也。而“圖澄”即“佛圖澄”之名省掉“佛”字,“羅浮”則非人名而是廣東的一座名山之名。據《高僧傳》記載:“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侄相殺,鄴都大亂。……后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由此可見,單道開是和佛圖澄同時代而稍前的一個和尚,因才能卓著而名聲遠揚。後來,逃避戰亂入羅浮山,並最終卒於此地。而且“圭角”為一單詞,不可點作“圭、角”。如《辭源》釋云:“圭的稜角,猶言鋒鋩。……又稱人沉著有涵養為不見圭角或不露圭角。”因此,該句的正確標點句讀應為:“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
(2)“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等句之失校誤點
該點校本卷八又云:
……既屬呂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約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
按:其中“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約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此應按《大正藏》第五十冊《史傳部》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點作: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因為“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與上句的“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皆以七字為句逗,順暢成章,若照誤點則亂套不通。又“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亦應按《大正藏》補字並點作“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於金鍮耳。”如此方為對稱而意順。
(3)“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之誤點
該點校本卷十云:
至二十三日,設齋嚫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豎菩提像骨已,因從寺眾及翻經大德並門徒等乞歡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人云:“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無彌勒、如來所居內眾,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華滿空。
(4)“朕與先王游大國”之失校
該點校本卷一云:
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游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岱、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眾。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
按:自秦始皇創立“朕”的稱號以來,只有中國這一中心的合法政權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才能使用並被認可,而周邊的藩屬國家的首領充其量只能稱王。故該段的“朕與先王游大國”句此應按《大正藏》改作“泰與先王游大國”。此處的“泰”乃為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的自稱也,此段之前有文云:“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可證其時大唐的周邊諸小國王皆不敢或不能以屬於唐朝天子專用的自稱“朕”來自稱的,即使有小國王敢妄自尊大而自稱“朕”,唐朝之人如玄奘等高僧也不會將此記入自己的論著而不加批評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