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彝
晚清外交家、翻譯家、遊記作家。
張德彝(1847-1918),原名張德明,字俊峰。滿族,漢軍鑲黃旗人。晚清外交家、翻譯家、遊記作家。祖籍盛京鐵嶺(今遼寧鐵嶺河西蔡牛鄉張家莊),清初編入漢軍鑲黃旗。他一生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二十七個年頭。每次出國,他都寫下詳細的日記,依次成輯《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約二百萬字。其中《航海述奇》和《四述奇》曾有人傳抄印行,其餘均未發表過。張德彝去世后,他的後人恐先人手稿遭受損失,一九五一年將手稿送交人民政府保管,存放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內。
民國七年(1918),在北京病逝,享年71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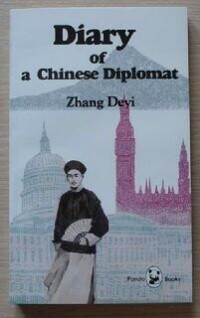
張德彝相關圖書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中外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張德彝十九歲時被清政府委派參加了中國第一次出國旅遊團,去歐洲觀光。他隨團遊歷了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漢堡、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等十個國家,飽覽了世界風情。在閉關自守的清王朝之外,竟有如此文明開化的另一天地!這活生生的現實使他大開眼界,本來這次出國清政府目的是為了了解洋人內情“探其利弊”,但是張德彝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對泰西(歐洲)新奇文化的觀察上,其中對戲劇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回國后,他寫出《航海述奇》,詳細記載了他的觀察見聞,許多戲劇活動的記載形象記述了歐洲戲劇活動盛況。他是我國第一個介紹歐美戲劇的人。
此後,張德彝又多次出國週遊世界。1868年他隨使團當翻譯,中國第一次派外交使團訪問歐美;1870年又隨使團任隨員再度赴法,是中國第一次派出外交專使到西歐國家辦交涉;1876年隨公使作譯官駐英國,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外國派公使;1887年任隨員又去法國;1896年任參贊到日本;1902年受賞二品官銜,出任英國大使;1906年功告回國。辛亥革命以後,於1918年病故於北京,享年72歲。張德彝於1904年代表清政府在英國倫敦簽訂《保工章程》,沒有給英國人任何在華特權。
他首譯電報、自行車、螺絲等至今仍被中國人沿用的科技名詞;首次向中國同胞介紹蒸汽機、升降機、縫紉機、收割機、管道煤氣、標點符號,乃至巧克力……
唐人街最早叫“大唐街”。1673年,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1872年。那一年志剛在《初使泰西記》中有:“金山為各國貿易總匯之區,中國廣東人來此貿易者,不下數萬。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國人呼之為‘唐人街’。建立會館六處。”1887年,王詠霓在《歸國日記》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為太平洋貿易總匯之區,華人來此者六七萬人,租屋設肆,洋人呼為唐人街。六會館之名曰三邑,曰陽和。”王詠霓的這句話與志剛的差不多。在這之前,王可能看過《初使泰西記》,因此,他在這裡沿用了志剛的“唐人街”。“唐人街”是粵人華僑自創的名稱。
1875年,張德彝在《歐美環遊記》中就稱唐人街為“唐人城”。張通英語,英語稱唐人街為Chinatown。其實,在這以前,張德彝更為直接,他將Chinatown直譯為“中國城”,如《航海述奇》(1866年):“抵安南國,即越南交趾國……再西北距四十餘里,有‘中國城’,因有數千華人在彼貿易,故名。”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張德彝時值十五歲,也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就在這一年,洋務派官員倡導下的“洋務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總理衙門”為了培養能夠辦理洋務的人才,決定創辦“京師同文館”,延請外國人來教中國人說外語,寫外文。創辦同文館的首要目的就是培養翻譯人員。
清政府在與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並不是到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才開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時的通事,主要是由於廣州一口對外貿易等活動,和澳門一隅同洋人接觸及傳教士的活動等關係,而自發的出現和形成的“通事”群。沒有誰有意識地培養他們。只有在北方因與沙俄交往較多,而俄語通事難覓,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設立過俄文館。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公使駐京了,與西方國家交涉事件開始增多,其中以英法為最多。因此,對於懂英法語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頗為迫切。以前雖有從買辦等渠道自發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這類人數量有限,質也不高,不能適應開放形勢和國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這類通事大多與洋人關係密切,清政府對他們表示不信任,事實上其中一些人也確實不能信賴。李鴻章到上海不久即發覺這些通事的劣跡而揭露說:
“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伙子弟,佻游閑,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通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塾,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他們知識不多,翻譯往往失實)“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慾,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他們甚至)“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
較早感到自己培養翻譯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與英法談判並簽訂《北京條約》的奕,他一則說“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再則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從僅僅為了消除“隔膜”,發展到“不受人欺矇”,自然是一個進步。處於上海交涉前沿地區的江蘇巡撫李鴻章,對自己培養翻譯人才的迫切感又超過奕,他表達這種心情說:
“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意,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達,亦難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活,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
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是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初設英文館,於1863年至1897年間先後增設法文、俄文、算學、化學、德文、天文、格致(時對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的統稱)、日文等館。學制分五年、八年兩種。八年制又分前館、后館。后館學有成效者升入前館,兼學算學、天文、化學、格物、醫學、機器製造、外國史地和萬國公法等科。
同文館創辦之初,教員擬從廣東、上海商人中專習英、法、米三國文字語言者挑選。於是清廷命廣東、上海各派二名識解外國(英、法、米)文字語言者,攜帶各國書籍到京作教習。朝廷發布詔令后,可惜粵、滬未能找出適當人選擔任教習。一八六二年,奕欣在英人威妥瑪的幫助下,請英籍教士包爾騰充任教習。學生來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為主,額定英、法、俄三館共三十名,結果也是事與願違,挑選不到合適的學生,只得先辦一個英文館,招生也擴大到了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八旗滿、蒙、漢閑散內,酌量錄取”。
雖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西交通頻繁,西風東漸日盛一日,但是保守的中國封建士大夫仍然嚴防“夷夏之別”。總是把外國罵做“蠻夷之邦”,把外語罵做“南蠻(央鳥)舌之音”,反對中國人學講外語。當時同文館成立之初,便遭到不少頑固守舊的官僚的攻訐。聲稱“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又雲“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將喪”,甚是聳人聽聞。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那些“正道人士”,希望自己子孫從科舉正途出生,是絕對不會把自家“佳子弟”送入同文館“拜異類為師”,做出這種“有辱斯文”的大逆不道之事。只有像張德彝這樣,出生寒門,又天資聰穎,好學不輟的人,才願意進入同文館學習。張德彝就是這樣被錄取了,成為了同文館第一屆十位學生之一。
為了獎勵入學,同文館規定,所有學生都有銀兩津貼。學生七品官者,每年給俸銀四十五兩,八品官者四十兩,九品官者三十二兩五錢。並根據學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三兩至十五兩不等。季考、歲考成績優異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張德彝就依靠同文館所發給的銀兩養家度日,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在館內完成學業。
同文館的學生畢業后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一八八九年,主管該館事務的曾紀澤對學生的水平作過一次統計:該屆一百多名學生中,學習優秀者約佔百分之二十;不堪造就、應予淘汰者十餘人,約佔百分之十。在這一時期,京師同文館培養了一批卓有成績的外語人才和二十八名高級外交官。張德彝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許多“第一”的紀錄:
中國近代第一所外國語學校——京師同文館的第一屆學生。
中國歷史上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外語翻譯人才。
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
更為世人稱道的是,他留下了二百多萬字的海外述奇,為封閉時期的中國國民開啟了一扇對外的啟蒙之窗,令人稱奇。一九一八年,張德彝病逝於北京,享年七十一歲。逝世時,有人送一副輓聯:"環遊東亞西歐,作宇宙大觀,如此壯行能有幾;著述連篇累續,闡古今奧秘,斯真名士不虛生"。
集郵活動在中國已開展100多年了,當初源自西方的“集郵”活動何時傳入封閉的大清帝國?誰又是中國第一個郵票收集的愛好者?由於歷史久遠,恐已難以考證了。但中國第一位用中文記述“集郵”活動的人是有據可查的,他就是中國外交官張德彝。張德彝(1847-1919),本名張德明,字在初,清漢軍鑲黃旗人。1862年,作為第一批學主之一進入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倉協的同文館學習,經三年於1865年畢業;1866年隨赫德等遊歷歐洲法、英、比、俄等10國;同年隨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任翻譯;同治九年至十一年(1870-1872年)隨崇厚出使法國;光緒二年(1876年)隨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大使郭篙燾到淪敦使館任翻譯,其間1878年至1879年,曾隨崇厚赴俄;1887年隨洪鈞至柏林使館任隨員;1891年曾充任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1896年隨羅豐祿出使英、意、比為使館參贊;1901年隨那桐到東京使館任參贊事;1902至1906年任出使英國大臣,其間專使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和瑞士等國。時大清皇帝,要求駐外使節將所見所聞寫成日記、定時向朝廷稟報。張德彝遵皇命,從1867年起,就陸續將海外見聞寫成《航海述奇》、《再述奇》、《八述奇》等約二百餘萬字的八種述奇。其中《再述奇爭》(又名“歐美環遊記”)之“英吉利遊記”一章“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六日己卯”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述英國的集郵情況:“聞英國二三年前,有種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張貼壁上,以多為貴,相習成風。女子有因無許多信票者而不得嫁者。據艾教習雲,有貧嫗英姓者,應得欠款銀一百二十兩,有百萬舊信票者不能得,以故眾人集得萬餘張送去。”時距英國1840年發行“黑便士”郵票已有28年,可見英人集郵活動已較廣泛開展,喜愛郵票程度也到如痴如醉。在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張德彝眼中,對集郵愛好如此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而稱之為“陋俗”;同時從側面反映國人對“集郵”的生疏;中國人對“郵票”也不識,稱之為“信票”。孰知時光流逝,物轉星移,歷史前進的潮流僅十年光景,大清光緒四年(1878年),中國也發行了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更為張德彝始料不及的是,當今中國集郵活動更是蓬勃發展,當初的“陋俗”已成為群眾性的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活動。儘管張德彝對“集郵”見解有偏異,也許由於他的“述奇”,為“集郵”活動傳入中國起到了介紹和傳播的作用,也使他成為中國第一位“集郵譯論家”,開創了中國集郵史的先河。附圖為張德彝像,選自使團官員合影。
張德彝——我國最早介紹歐美錢幣文化的鐵嶺人
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首次派旅遊團去歐洲觀光。旅遊團由四人組成,其中有一名19歲的鐵嶺人——張德彝。此時,他剛從北京同文館畢業,充當了旅遊團的翻譯。同冶七年(1868),張德彝再次出國。此行,他隨蒲安臣使團先經日本到美國,然後過大西洋到歐洲,到歐洲歷經英法兩國,后因故提前回國。張德彝這兩次出國,飽覽了異國風情。回國后,他將其見聞各寫成了一本遊記——《航海述奇》如《歐美環遊記》。書里第一次向我國介紹了有關外國的錢幣製造、錢幣形制和錢幣軼事。張德彝在歐美參觀了好幾處“鑄幣局”。他觀察入微,記錄真切。同治五年(1866)農曆三月二十八日,他同旅遊團一起到了法國巴黎造幣廠,目睹了造幣的生動情景:“入西面樓門,乃鑄錢處。銅片切錢,鑿花雕字,皆用火機,一時可得數千。金銀錢分兩不同,分毫不爽,洋錢質最純凈。”也許是偏愛,或是他第一次沒有觀察細緻,所以兩個月後,他再次參觀了這家造幣廠。這次和一名名叫德善的法國朋友同的,同德善至鑄錢同一觀,對機械部分作了補充記載:“其鼓鑄之火機,系以水氣衝激輪機,令進退於鐵管之中,以轉大輪。其大輪上置長軸無數,中系小輪百千,下連各種機器,彼此接以為條。大輪動別各機器相隨,快甚。所造之錢,分金、銀、銅三種,大小不一。”
同年四月,張德彝一行人到英國旅遊。他們在英國首都倫敦,參觀了該國的造幣技術。英國的造幣方法、機械、工藝,沒什麼特殊地方,只是廠房比較寬闊。它除了造鑄英國的錢幣外,還給香港、印度等處造大小銅、銀錢。
1868年農曆三月初八,張德彝一行人來到了合眾國(美國)的舊金山。他們特意參觀了該地的造幣廠,並對廠房、造幣的全過程作了較詳細地觀察。
張德彝是位有心人,不僅觀察外國人怎樣造幣,而且十分注意錢幣本身,對各國各種錢幣的幣製作了詳細
地了解和記錄。
他介紹法國當時的錢幣有“路易”、“笛佛朗”、“思安方”、“佛朗”、“對穌”、“桑地畝”。這是金、銀、銅幣,另外還有“銀錢票”名叫“巴比葉得邦格”。
俄國的幣制比較複雜、有古金錢、現行小金錢、大銀錢、小銀錢、大銅錢等,錢幣的重量各異、名稱也頗紛紜。
日本的錢幣新穎別緻,幣上印有花、線、字、蝴蝶,有的形狀為立方形、有的橢圓形。特別是有的很大,中有方孔。
張德彝對各國錢幣的記錄和介紹可謂十分詳盡。這裡他不僅介紹了其錢幣的種類、名稱、重量、質量、大小、形狀、面值,而且還介紹了其相互間的兌換關係。
張德彝在他的遊記中,還介紹了一些外國錢幣軼事,記錄了中國錢幣在國外的流傳情況。
在埃及,他鑽進了金字塔,見其塔中空空無物,但他爬出來的時候,看見許多“土人持綠瓷小人,碧銹銅錢出售,言皆自此陵下掘出者”。看來當時出售、倒賣出土文物——古錢幣是一種正當行為,埃及政府是不加干涉的。在美國,他發現中國古錢深受美國人喜愛。他應邀到美國正總理徐爾德家坐客,就發現這位要員曾收藏了許多中國古錢,中土古錢,如半兩、五銖、嘉佑、建興等暨大清‘同福臨東江’二十字之制錢,皆釘於紙版之上,放於玻璃罩內”。徐爾德堪稱是位“集幣專家”。
在法國,張德彝發現在鑄幣局用專樓舉辦了“各國錢幣展覽”。在眾多的古幣中,中國錢幣佔據著重要地位。對此,張德彝作了記載:
“法國錢局,東樓所集乃天下各國古今金銀銅錢。案上置大玻璃匣,每匣只盛一國錢。見有中國古錢,青銅錢、紅銅錢、鐵錢、錫錢,以及當十錢、當百錢、當千錢。其餘他國錢,文字皆難以辨識。”
張德彝關於外國錢幣文化的介紹,對我們研究錢幣歷史,了解錢幣文化交流都是很有幫助的。也許這些介紹,會給集幣愛好者增加新的知識,引起新的興趣。
著作《四述奇》
意外淘得《四述奇》顯見思鄉情
刻於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作為清初東北第一書院-----鐵嶺銀岡書院捐添經費修齋房碑,其碑陰刻:書院新添書籍其中有《出使英法比意四國日記三本》,這正是張德彝的旅歐述奇日記。
筆者藏有傳抄印行的《四述奇》,是張德明1876年隨公使作譯官時著述的。這套二函八冊由著易堂仿聚珍版,榮竹坪校閱,張德明好友常瑞,英煦作序及張德明自序,完整的旅歐遊曆日記。每卷名前提及“鐵嶺張德明”,表達了他對家鄉的懷念,“亦系不忘所籍也”(張德明後人張祖銘的“關於先祖的函述”)。

出使歐美的中國使團出發前在北京合影
作為鐵嶺人的張德彝無愧於十九世紀的旅遊家,作家,書法家,外交家,翻譯家稱號,他留下的許多歷史珍貴史料值得大家去研究,去學習。
同樣一個丁韙良,在與中國農民交流的時候,卻認識到中國社會底層的真實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滿手老繭的農夫聊天時,農夫問道:“你們洋人為何不滅掉清國呢?”丁反問道:“你覺得我們能滅得了嗎?”農夫說道:“當然了”,他邊說邊指著山下面的一根電線,“發明那電線的人就能推翻清國”。
晚清中國面臨的是一場源自先進科技的革命。頑固的士大夫們堅持認為中國雖然沒有發明電線電報,卻仍然是泱泱大國。
在直接走出國門、接觸到西方現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張德彝是一位比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張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歲時考入京師同文館,為該館培養出的第一批譯員之一,四年後,他便隨同中國近代第一個官方外派使團斌椿使團出訪。隨後40年,他雖然沒有擔任過駐外最高使節,但他始終從事外交和外事活動。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時他任通事(翻譯),環遊了歐美各國;同治九年,欽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專程赴法道歉,他任隨員。此間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這一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中國農民起義的偉大事件。光緒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國駐英使館譯官,光緒十三年任秘書。后曾一度回國,任光緒皇帝的英語教師;光緒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羅豐祿的參贊;光緒二十七年,以記銘道二品卿銜出英、意、比大臣,光緒三十五年任滿回國。他一生中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了27個春秋。1918年病逝於北京。張德彝陸續把他的見聞寫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叢書》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過去一直認為已遺佚,但最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獻中被發現。
張德彝從海外歸來后,被派去和同文館的另一校友沈鐸一起做光緒帝的英文老師。中國的皇帝也許是惟一要求兩位教授同時上一門課的人。為了對自己的老師表示尊重,光緒帝允許他們在王爺和大臣們跪見時仍然坐在自己身邊。可見張德彝回國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張德彝對此並不以為然,因為他對自己的同文館出身還是充滿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國,學習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過獎勵政策鼓勵八旗子弟學習英文。其獎勵條款是:每月發給“膏火銀”三兩,學習優秀者,另有獎金,三年學成后,視成績授予七、八、九品官職。但即使這樣既給錢又給官,在1862年6月京師同文館開館時,還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學生。
同文館的學生同時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京師的好事者作各種侮蔑、攻擊的言辭打擊這些入學的學生:所謂“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所謂“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所謂“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作為15歲的漢軍鑲黃旗子弟的張德彝,固然有勇氣面對這種局面,但是,畢竟沒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還是有遺憾的。
他逝世時,有人送一副輓聯——“環遊東亞西歐,作宇宙大觀,如此壯行能有幾;著述連篇累牘,闡古今奧秘,斯真名士不虛生”,當為對他的客觀正確的評價。而張德彝晚年卻並不為自己的經歷自豪。他教導他的子孫:“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余不學無術,未人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為要務。”
張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語言能力,其墓誌銘曰:“君雖習海外文字,或有諮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專好也。悲夫!”張德彝的自卑感來自晚清畸形的社會。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學問,固然出於美德,但更多的是社會的畸形環境。如此壓抑,的確可悲。
張德彝與他同時代的外交大臣們相比,可能因為沒有賦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對西方的觀察視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多來自他的記述,他的許多發現是中國人第一次對西方的細緻觀察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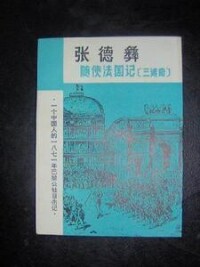
相關著作
第一個記載西方標點符號: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張德彝隨同美國公使蒲安臣帶領的“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在《再述奇》(或者《歐美環遊記》)中,他介紹了西洋標點:“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義足,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於句之前後記“”;另加註解,於句之前後記();又於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又過了將近40年,中國的現代漢語才正式採用西式標點符號。張德彝的文化觀察不可謂不敏銳。
第一個記載巴黎公社:張德彝寫作《隨使法國記》110年之後,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將其作為《走向世界叢書》的一種而出版。國人乃知有中國人經歷並記載了巴黎公社。張德彝曾於同治九年臘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為“天津教案”隨欽差大臣崇厚赴法賠禮道歉,正趕上巴黎公社暴動。24歲的張德彝在日記中,雖將巴黎公社視為“叛亂”,並命名之為“紅頭民政”,但對巴黎公社的勇士們,他仍然是稱讚有加:“申初,又由樓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叛勇不惟男子獷悍,即婦女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則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一空,奇珍半成灰燼。現擒女兵數百,迅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年輕的張德彝當然無法理解這場運動的世界性意義以及它在人類階級鬥爭歷史中的重大價值,但是,這種不同於中國農民起義的“叛亂”,想必一定對他產生了極大的衝擊。
第一個記載若干著名西洋工具、樂器和房屋名稱:自行車的名稱,即來自張德彝的記載。他在《歐美遊記》中描述過倫敦的自行車:“前後各一輪,一大一小,大者二寸(應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輪轉,足動首搖,其手自按機軸,而前推后曳,左右顧視,趣甚。”他也是第一個描述火車的中國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當時英法的火車:“頭等車廂分三間,每間左右各二門,門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藍綢小簾,自卷自舒,機關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鏡、帽架,有絲絡以便盛什物。前後兩木床,寬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絨洋呢。地鋪花氈,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燈於車頂,兩床抽出可並為一坑。”他也是第一個描述鋼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張德彝途經上海,去拜訪印刷家姜辟理,曾聽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張德彝描寫“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細小,差參錯落,頗舉可聽”。無疑姜氏彈的是一架鋼琴。他還首次記載了縫紉機(後來他在法國與縫紉機的發明者伊萊亞斯·豪見過面):《航海述奇》載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鎮壓過太平天國的英軍將領戈登家中作客,“見有鐵針架一座,俗名鐵裁縫”。張德彝描寫鐵裁縫說:“形似茶几,上下皆有關鍵,面上前垂一針,后一軸線。做女工時將布放於針下,腳踏關鍵,針線自能運轉,縫紉甚捷。”他還首次把美國白宮翻譯成“白房”。在《歐美環遊記》中他說:“朱溫遜(即約翰遜)少有大志,隱於縫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國安民之書,罔不精心功習,國人敬之。前任統領凌昆(即林肯)卒后,眾遂推彼登位,故國人呼為‘縫匠統領’。其府周圍三里,系漢白玉石建造,外繞花園。土人呼曰‘白房’,嘲語也,蓋國中呼廁為白房。”這還是頭次聽說,“白宮”一詞在當地民俗中居然有嘲弄的含義。
第一個進入金字塔參觀的中國人:金字塔與長城之間的最早的對話或者說直接聯繫,來自張德彝。他是有記載的第一個曾鑽進金字塔的中國人。拿破崙進入金字塔后,曾經因震驚而一言不發。埃及金字塔建築非凡,奧秘無窮。中國人知道它的直觀情況,是在清朝同治年間。探秘人張德彝(1847—1918),是一位鐵嶺人。1866年,張德彝在北京同文館畢業時,年方19歲,此間他曾隨觀光團出國進行了一次旅遊,一路上歷盡艱辛來到北非,見到了金字塔。張德彝首先考查了金字塔(即王陵)的外貌,記錄該王陵,一個大的,兩個小的,均呈“三尖形”。大型王陵“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疊起……正面一洞,高約八丈,上有埃及文一篇,字如鳥篆,風雨侵蝕,模糊不復辨識。”在墓前有“一大人頭,高約四丈,寬三丈許,耳目晰。”接著張德彝進一步考查了金字塔內部的情況。在土人的引導下,他好奇地鑽進了那座最大的金字塔。他是從破損的縫裂中進去的,進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縱橫累疊的大石頭,一片漆黑,只能秉燭前行。開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時雨顛撲”又“石震有聲”,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彎彎曲曲,“趨前失后,退後迷前”,走了好一陣方豁然開朗,原來進了墓室。其實裡邊並沒有什麼出奇的東西,只有“一石棺無蓋,形如馬槽,擊之鏗然,放於壁角”。張德彝等在墓中盤桓,往返達三小時之久。因過度疲勞,“出則一身冷汗矣”!張德彝回國后,將他親游金字塔的見聞寫了一本(航海述奇)的書。這篇遊記竟成了我國第一次關於金字塔的記載。據考,張德彝字在初氏,滿族,曾任清政府重要官員,出使國外。其祖籍為鐵嶺縣蔡牛鄉張家莊人。
第一個記載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張德彝所寫的著作中,曾兩次提到域外有一種叫“腎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國的見聞時寫道:“聞英、法國有售腎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據雲,宿妓時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間,雖雲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在《歐美環遊記·法郎西遊記》中,他記載再游法國時的見聞:“聞外國人有恐生子女為累者,乃買一種皮套或綢套,貫於陽具之上,雖極顛鳳倒鸞而一雛不卵。”他認識到避孕套的兩大功能:預防性病和計劃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對這種違背人倫的事進行了抨擊:“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張德彝對西方的觀察,最後仍然是中國的角度和立場。張德彝的遺憾,當然來自於他的教育背景。我們無法要求張德彝在將近150年前具有更加開放的視野。他在本質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在舊金山,張德彝的筆記就記錄了他同一個美國化了的華人發生摩擦的情況。這個華人已經來到美國七年,學習基督教。張德彝曾經就對他訓斥道:“你已經剪了你的辮子,你又怎樣有臉回到中國去呢?你已經改穿美國服裝了,我們不再把你看成一個中國人。你學基督教嗎?你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傳統。在你死後,你還有臉去見你的祖宗嗎?”
鴉片戰爭以後,新思想傳入,西洋標點也跟著進來了。第一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是清末同文館的學生張德彝。同文館是洋務運動中清政府為培養外語人才而設立的,張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學生中的一員。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駐華公使浦安臣帶領"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張德彝也成為隨團人員中的一名。張德彝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到了哪個國家,都喜歡把當地的風景、名物、風俗習慣都記錄下來,以"述奇"為名編成小冊子。在1868年-1869年期間,他完成了《再述奇》。這本書現在稱作《歐美環遊記》,其中有一段介紹西洋標點的,云:"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於句之前後記"";另加註解,於句之前後記();又於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
雖然張德彝不是在有意識地向國內知識界引入標點,甚至帶有反對的口氣,覺得這些標點繁瑣。但是卻在無心栽柳的過程中,為中國語言符號的發展帶來了新風。

巴黎公社革命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內,發現了張德彝七十八冊日記手稿本,除《七述奇》遺失外,都保存完好,並發現《三述奇》中有目擊巴黎公社革命的最大記載。這一意外的發現,引起了中國和法國史學界人士的注意。
張德彝在《隨使法國記(三述奇)》中,記述了凡爾賽軍隊攻入巴黎。從公社戰士的街壘戰,旺多姆圓柱被拆除等歷史性場面,不僅和正式記載相符,而且有許多生動具體的細節。如所記巴黎街壘:“各巷口多築土石牆,几案牆,又有木筐牆,系以荊柳編筐,內盛零碎什物,堆壘成台,炮子雖入,含而不出”。又如他寫到凡爾賽軍隊被俘戰士瘋狂鎮壓:“皆黑布蒙頭,以槍斃之”。而公社戰士視死如歸,英勇不屈。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元1871年6月2日)記:“由樓下解判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儘管張德彝是當時東方古老封建國家官員,並不同情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革命,但他卻留下了這些凜凜如生的記述,成為珍貴的史料。
如此一個人物,民國以後居然長期寂寂無聞!若不是上世紀80年代中,著名出版家鍾叔河先生獨具匠心,策劃出版一套“走向世界叢書”,費盡工夫把他的部分著作以及零星事迹挖掘出來,張德彝真箇被歷史掩埋得死死實實了!
何以如此?鍾先生一語中的——張德彝作為職業外交官毫無建樹,他是一個庸才!在晚清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人們休想一瞥他的身影!當了5年“帝師”,未聞他給光緒留下過任何印象!怪不得鍾先生出言刻薄——張德彝全部作品的價值,恰如其書名,僅止於“述奇”而已。
逸筆草草,足可勾勒出斯人的思想風貌——
紐約一家女子小學誠邀張德彝前往演講,他給洋娃娃大談忠孝節義。
每當有人向他請教英語,他總是笑而不答。蓋因他以“舌人”自嘲,認為自己只懂英語,屬於不學無術者流。
直至走向共和,垂老的他仍以終生不曾參加過科舉考試為最大憾事,諄諄囑咐兒孫務必要讀“聖賢經書”。
張德彝逝世於“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值舉國為“巴黎和會”決議義憤填膺之際,這位年過七旬的資深外交官卻以“宣統十年”為年號,向時年13歲的廢帝溥儀敬呈臨終遺折,稱:“臣八旗世仆,一介庸愚……瞻望闕庭,不勝依戀之至!”
滯留凡爾賽當旁觀者
幾經輾轉,張德彝終於出了巴黎,並隨崇厚等人於3月30日來到凡爾賽,先後見到了法國政府首腦梯也爾、外長法弗爾等人,但是被巴黎公社起義搞得焦頭爛額的法國政府無暇顧及“天津教案”。因而使團又在凡爾賽滯留,直到6月初巴黎公社被鎮壓才返回巴黎。這樣,崇厚、張德彝等人作為旁觀者,再次從凡爾賽的角度觀察並記敘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相關情況。
張德彝到凡爾賽的頭一天晚上,就見旅館外“兵馬雲集”,原來是政府軍隊不願與革命軍作戰,政府不得不調動海軍來鎮壓革命。後來,政府軍與公社部隊不斷發生激烈的戰鬥,張德彝等人都有目睹。
4月3日,公社調集4萬國民自衛軍,分三路向凡爾賽進軍,政府軍出城迎戰。由於久攻巴黎不下,凡爾賽軍隊採取炮轟巴黎的戰術,張德彝目睹當時的情況是,巴黎城是“濃煙衝突,烈焰飛騰”,好像燒著了幾千間房屋一樣。
5月21日,凡爾賽軍隊對巴黎發動了總攻。上演了歷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23日,張德彝在凡爾賽第一次見到了被抓獲的公社人員兩萬多人。張德彝認為,這些人不過是受到脅迫的窮民,並無太大罪過,但想到他們不久就會受刑,心裡也不禁十分難過。28日,公社遭到鎮壓,29日,張德彝在凡爾賽目睹了“勝利之師”三四萬人的歸來。這些人面目黝黑,步履蹣跚,有的走著走著就躺在了地上。這支剛剛投降過普魯士,又拿起槍鎮壓本國起義者的軍隊,完全沒有勝利之師的模樣!
再回巴黎完成使命
5月28日,巴黎公社遭到鎮壓,大批起義人員被處死。6月初,張德彝隨崇厚再次進入巴黎。張德彝等人目睹了政府軍追捕、屠殺起義者場景,多次真實地記錄了公社社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氣概。張德彝剛到巴黎當天,就在大街上見到被俘公社人員兩千多人,這些人“有吸煙者,有唱曲者”,一點也沒有懼怕的意思。可見,張德彝對於慷慨就義的公社戰士,還是頗有幾分同情的。當時的中國,剛剛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清朝官員能有這樣的態度,十分難能可貴。
之後,張德彝等人在巴黎參加了兩個“善後”事宜。一個是參觀了被推倒的旺多姆圓柱。旺多姆圓柱原是拿破崙一世戰勝敵國時,用繳獲的銅炮改鑄而成的。5月6日,公社拆毀了這一象徵著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圓柱,並推倒了拿破崙的石像。
二是參加了凡爾賽當局為原巴黎大主教達爾布達瓦舉行的葬禮。4月初,公社為清除反革命的勢力,頒布關於人質的命令,捉獲並處死了達爾布達瓦主教。凡爾賽軍隊奪取巴黎后,6月上旬為他舉行葬禮,並邀請各國使節參加,中國使節也在被邀之列。
崇厚使團既然是為“天津教案”謝罪而來,此時又將此事向法國政府說明。但梯也爾政府一直未顧得上理會。直到當年12月,梯也爾才正式接見中國使團,接受國書,並相互致詞。經歷梯也爾的一番訓斥之後,崇厚一行也完成了他們赴法國的使命。
清人張德彝當時正在巴黎,目睹了巴黎社會的情況,是巴黎公社的見證人。
張德彝曾在京師同文館學習外語。1870年6月,因外國教堂“迷拐幼孩”,強佔民地,欺壓百姓,天津群眾怒不可遏,焚毀法、英、美等國教堂,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外國職官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國聯合抗議,清廷特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乞情致歉”,張德彝隨同前往,充當翻譯。
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義前夕,抵達法國波爾多的崇厚一行派張德彝到巴黎為中國使節尋找館舍,由於巴黎戒嚴,張德彝困頓巴黎,被迫成了巴黎公社的見證人。張德彝是清代遊歷最廣的人,他將遊歷15國的情況寫成遊記,其中第三部分遊記《三述奇》主要記載法國見聞。張德彝寫道,他初進巴黎,看到截然不同的情況,在國家危亡之際,政府官員還“遊玩看劇”,而工人正在迅速武裝起來,與政府賣國活動作鬥爭。當梯也爾下令政府軍鎮壓工人時,一些政府軍“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工人武裝擊敗政府軍,“槍斃官兵數十人”,以梯也爾為首的政府軍敗北,逃往凡爾賽。接著工人武裝進入巴黎市中心,“巴里(黎)無主也,叛勇(工人武裝)行令”。張德彝親自目睹工人武裝佔領市政廳和其他政府機關,政府軍及其官員紛紛逃走,工人階級主宰一切。但缺乏政治經驗的巴黎無產階級,沒有立即進攻反動巢穴凡爾賽,消滅反革命力量,過早忙於公社選舉,使反動勢力贏得喘息機會,與普魯士相勾結,一起圍剿巴黎公社。張德彝寫道:“四月初六(五月二十四日),炮聲不絕”,反動派攻佔巴黎,工人武裝頑強鬥爭到最後。張德彝看到大批工人倒在血泊中,但他們面對死亡,“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
張德站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稱巴黎工人為“叛勇”,這不足為怪。後來,張德彝曾被清政府任駐英、比、意公使;回國后,1891年,又任光緒帝的英語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