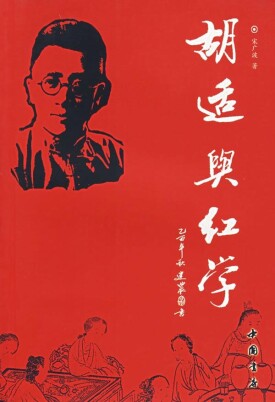新紅學
新紅學
新紅學是指五四運動以後胡適等學者進行的《紅樓夢》研究。新紅學是20世紀紅學史上影響最大、而命運又最多舛的一個紅學流派。“新紅學”這一稱謂,出自顧頡剛《紅樓夢辨·序》:“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
目錄
”新紅學的方法是科學方法,這是它區別於索隱紅學的最本質的特徵。1910年代,陳獨秀等高舉“賽先生”大旗,大力提倡科學精神;而《科學》雜誌以任鴻雋、楊杏佛、胡明復等為代表,也竭力宣傳“科學方法萬能”的觀點,主張科學方法適用於一切研究。《紅樓夢考證》是胡適在科學化運動大潮中,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的一種嘗試。胡適提出他的科學方法:“……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后即須改正的。”這種方法的哲學基礎是“實驗主義”(Pragmatism),它有兩個主要特徵:歷史的觀念,實驗的態度。後來,胡適又將其表述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今人席澤宗院士曾詳闡其科學性。
新紅學之“新”,不僅“新”在其研究方法,更“新”在其研究內容。胡適將紅學的考證內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他通過考證,將《紅樓夢》的著作權還給曹雪芹,並搜輯到大量作者及其家世的材料,使後人對曹雪芹這位“奇人”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而對“續書”的研究、脂硯齋的研究以及“探佚”等,都是由作者研究衍生出來的。因為不相信后40回是曹雪芹寫的,才有所謂“續書”說;要探究曹雪芹寫的后40回是什麼樣子,才有所謂“探佚學”。至於胡適對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則大體釐清了《紅樓夢》創作的年代。1954年批判胡適的時候,胡適總被指責沒有研究18世紀的階級鬥爭;孰不知,“18世紀”這個時間,正是胡適考證出來的。在版本研究方面,胡適將其劃分為脂本、程本兩大系統,又命名並初步研究他生前出現的戚本、甲戌本、庚辰本等本子。大體上,胡適研紅的前期,在作者方面貢獻最多,後期,在版本方面貢獻較多。
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都是迥異於索隱紅學的劃時代的貢獻(有研究者說,“新紅學的本質是實證與實錄合一”,這並未切中要害)。也主要是這個原因,學術史家總把新紅學視作現代學術的起點。這既是《紅樓夢》的光榮,更是新紅學的光榮。
新紅學有一個爭議極大的觀點:“自傳說”(最初的表述是“自敘”)。它是胡適根據曹雪芹的傳記材料與紅書所敘提出來的,是針對索隱家的“敘他”、“他傳”提出來的,是實證範疇的具體問題。沒有“他傳說”,就不會有“自敘說”;如同沒有索隱紅學就沒有“新紅學”一樣(新紅學本脫胎於對索隱紅學的批判與反動)。二者的研究方向根本相反:索隱的方向是“逆入”,新紅學則是“順流”。兩派都用的是“考證法”。但新紅學派側重於考證作者、時代、版本,而索隱則側重於考證小說情節;索隱從虛入手進行研究的,因此沒有根據,只好靠猜謎,只好靠附會,而新紅學則是從現有的材料入手,以事實為依據,處處尊重證據,相信證據,講求無徵不信。
由此可知,索隱與新紅學,簡直是“水火不容”。晚年的胡適,甚至拒絕批評索隱派的論文,他說:“方法不同,訓練不同,討論是無益的。”但有的研究者卻提出:《紅樓夢考證》既是“新紅學”的開端,也是“新索隱”的開山之祖,甚至把胡適與劉心武聯繫起來,說劉心武承襲了“新紅學”積弊;又說,新紅學“有反科學的一面”(而胡適卻反反覆復強調,要“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這實在令人費解。其實,新紅學與所謂新索隱,毫不搭界。最近,常產生這樣的感想:研究紅學史,須先從微觀研究入手,只有先把每一個重要人物及其著作研究透徹了,才能做成一部權威的紅學信史。拙作《胡適與紅學》,就是本人對“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所做的初步探討。
新紅學因反對索隱派而產生,這早已是公認的事實。但將其放在更廣闊的學術背景下加以考察,還有三大背景是為後人重視不夠的,即新文學運動、國語運動和整理國故。如果將新紅學的產生與胡適早在留學時期就倡導的白話文學運動和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中提出的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就會發現:由胡適來開創新紅學,這是多麼一件順理成章的事——那簡直是必然的。因此,有研究者根據胡適與汪孟鄒的通信而提出《紅樓夢考證》是“被逼出來的”說法,不能不說有點牽強。
無論是擁護新紅學的人,還是反對它的人,幾乎都不否認這樣一個論斷:作為新紅學的開山鼻祖,胡適是20世紀紅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人。1961年,胡適說,40年來新紅學的發展,只是作者、本子兩個問題的新資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過去了,這話似乎還沒有完全過時。就拿紅學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馮其庸二公來說,周老自然是公認的真正繼承胡適的“集大成者”,無論新紅學的優點還是缺失(如賈曹互證),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繼承下來了;馮公也是啊,馮先生在其整個紅學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貢獻最多,近年又多次強調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個方面多多用力——他們不都是在沿著胡適開創的路前行嗎?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難道《紅樓夢》研究就只能在作者、版本兩個圈圈裡打轉轉嗎?所以這樣說,並不是說這兩個領域都研究明白了,不需要研究了;事實是,有好多具體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我們的態度是:繼承胡適、發展胡適、超越胡適。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有更多的人從更多的角度來從事紅學研究,可惜迄今為止尚無突破性的成績出來。再上溯到上世紀50年代,俞平伯先生曾試圖超越新紅學的種種罅漏和時代局限性,力圖開闢《紅樓夢》研究的新境界。其實,無論是胡適、還是俞平伯,都有勇於修正錯誤的勇氣,這也是作為原創的“新紅學”的一種品質。胡適對曹雪芹卒年的不斷修訂,俞平伯對“自傳說”、對“《紅樓夢》文學造詣不高”等觀點的修訂,都體現了這一點。
新紅學的產生和輝煌,屬於20世紀。80多年來,它伴著風雨,一路走來,經歷了太多的艱辛和曲折。到了今天,在新的世紀,實在需要有一個像胡適開創新紅學那樣的人出來超越胡適了;雖然,這很難。
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開始了。紅學家們以五四運動為界線,將紅學分為新紅學和舊紅學。舊紅學主要派別評點派:中國文學史的評點派起源於明代中葉。金聖嘆批《水滸傳》、毛宗崗批《三國演義》、張竹坡批《西遊記》等,後來竟成了一個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題詞、讀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夾批、批註等。脂硯齋是最早學金聖嘆而對《石頭記》(《紅樓夢》)加以評點的評論家,他寫下大量評點式評語,因而使《石頭記》獲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一專有名稱。脂硯齋的批語隨《紅樓夢》抄本的正文保留下來。索隱派:索隱派又稱政治索隱派。所謂索隱即透過字面探索作者隱匿在書中的真人真事。索隱派在乾嘉時期經學考據風的影響下,形成一種學派。索隱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瑣的考證,從小說的情節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索隱派的開山鼻祖當推周春(1729-1815)。周春認為《紅樓夢》為“敘金陵張候家事也”,這種觀點對後世影響不大。索隱派對後世影響較大的觀點有“明珠家事說”(也稱納蘭性德家事說),“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亦稱福臨與小宛情事說),“排滿說”等。題詠派:題詠派著眼於書中人物之悲歡離合,從而寄其羨慕或感概之情。題詠派的詩詞、賦、贊,有的抒發“榮華易逝人生如夢”的人生觀,滲透著佛家的“色空”觀念和“夢幻”思想;有的抓住書中“風月繁華”和“愛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謂“繁華”之景和“香艷”之情,吐露出一種仰慕、一種思緒。王國維:舊紅學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評點派,也不是索隱派、題詠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國維。王國維是最早從哲學與美學的觀點來批評《紅樓夢》之藝術價值的紅學家。王國維首先建立了以哲學和美學雙重理論基礎的文學批評體系,其次他提出辯妄求真的考證精神,使紅學的研究能脫離舊紅學的猜謎式的附會。新紅學主要派別及思潮考證派:新紅學的主要人物是胡適。他在1921年寫了一篇《紅樓夢考證》;次年,又寫了《跋<紅樓夢考證>》。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胡適的‘考證’給《紅樓夢》研究開闢了新天地。胡適徹底抨擊了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說:“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所謂需要做考證的“兩個問題”,指的是作者和版本,這就是胡適為《紅樓夢》考證界定的對象和範圍。三、四十年代:上世紀30年代,紅學漸漸跳出了胡適的“考證”、“著者”、“本子”之類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闢蹊徑,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對《紅樓夢》時代背景、主題思想、藝術特點、人物形象加以探討。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轉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狀態分析之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是“一部對於《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在“紅學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對脂批給予重視”。 “批紅運動” :1954年開展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隨即展開了對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想的批判。在這場批判運動中,新老紅學的諸多觀點都受到了批判。1953年至1963年間,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是用馬列主義研究《紅樓夢》的時期,主要標誌是舉辦了“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紀念展覽會”。紅學現狀:1976年以後,紅學研究的內容愈來愈廣泛,分工愈來愈細,人們對紅學的概念亦進行了重新認識。周汝昌提出“現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是紅學中“四大支柱”。多數紅學家主張將紅學分為“曹學(外學)”和“紅學(內學)”。“曹學”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傳記、文物等:“紅學”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思想內容、人物創造、藝術成就、成書過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