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不收
明代防守軍中哨探或間諜的稱謂
明代遼東邊防守軍中的哨探或間諜的特有稱謂。明朝建后鑒於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不設府縣,專以都司領衛所,先後設立遼東都司和奴爾干都司。其中遼東都司的轄境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南至旅順口、北達開原,相當於遼寧省西部和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奴爾干都司的轄境西起斡難河、北至外興安嶺、東抵大海、南接圖們江、東北越海而有庫頁島其中所屬斡難河以東、嫩江以西、西拉木倫河以北、黑龍江上游兩岸地區建立的衛所,主要管理韃靼蒙古人嫩江以東遼河以北黑龍江中下游兩岸、松花江、烏蘇里江等的衛所,主要管理女真人的衛所。
明朝對奴爾干都司境內蒙古、女真的統治政策是:“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而由明朝任命為都司、衛所長官的蒙古、女真各部酋長,都是世襲的明朝地方官。他們負責管理本衛人民,遵守明朝的法令,守疆定邊,定期朝貢。
在和平時期通過朝貢和貿易的方式獲得生活必需品是當時蒙古、女真諸部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但是大規模和頻繁的朝貢給明朝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因此在正統年間及其以後的各代,明廷對東北蒙古、女真各部朝貢的人數、次數、日期等屢下令整頓和限制。但是這些限制措施卻引起了諸部首領的不滿和反對,在求增入貢不許以及邊官“出塞撲殺諸夷”的情況下,不僅兀良哈“時時出沒塞下”,就是女真諸部亦“數入塞殺掠”,從而激化了明廷與邊疆各族間的矛盾。
正統年間,“遼東邊備廢弛,胡虜數入為寇”,“建州等衛女真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為之困敝。”有鑒於此,明廷採納遼東都司畢恭的建議,修築遼東邊牆,以為防禦之舉。邊牆分為西牆與東牆兩部分,其中從正統七年開始陸續修建的遼西、遼河套一帶的邊牆,史稱“西牆”;從成化三年為防禦女真而修築的遼東一段邊牆,史稱“東牆”。
整個邊牆西北自長城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鎮北關,又自鎮北關起,到九連城江沿台堡止。其間以遼河之阻隔,形狀如凹字形。到萬曆元年(1573),“遼東全鎮修完城堡一百三十七座,鋪城九座,關廂四座,路台屯堡門角台圈煙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邊牆二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三丈九尺,路壕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一丈。”在邊牆沿線以內,距牆2—3公里,建立了守御邊牆的“營堡”,每一營堡屯駐著百十二名守軍,叫百戶所,其長官叫百戶。堡與堡之間相距8—15公里。時有“高牆垣,深溝壑,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之稱。每座“堡”城負責一段邊牆及其臨近的烽燧台防務事宜。
在“邊有牆、牆有關、關內有堡、堡內有兵”的防線中,一座座堡台構成遼東邊地的一處處邊防哨所,邊堡墩台駐軍則成為明東北邊防的一支重要的偵察防禦力量。其時,明朝為防禦“賊屢入寇”,曾指示遼東守邊官兵“夙夜盡心,以圖成功,遇賊近邊,出兵剿殺”。史料中關於遼東官兵在邊堡之間容易穿行的空地處伏擊入境者的記載屢見不鮮。總兵官曹義在時,為有效阻止邊外各族的“入寇”行為,還多次率官兵出邊巡哨,主動出擊。正所謂“今沿邊之守,有營堡墩台之建,有巡探按伏之防,有將領以總其權,有副將以分其任。調發者之有逰兵,分防者之有備御,嚴守之道亦可謂周且備矣。”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明朝的遼東防禦偵察系統是完備的。
這裡所謂的“巡探按伏”就是本文所關注的偵察隊伍——墩台哨兵。墩台哨兵又稱“墩夜”或“直撥、橫撥”。“墩”指墩軍,又稱“橫撥”,主要負責墩台及其附近地區的站崗放哨任務。“夜”又稱“哨夜”、“夜不收”、“直撥”,專指“能深入虜營哨探得實”者,即能夠深入敵境進行偵察活動的哨兵,因其行動遠離墩台邊堡,故又稱“遠哨夜不收”、哨探、間諜、哨撥夜探、撥夜等等。“墩夜”作為遼東邊防前線的士兵,或巡哨,或深入敵境偵察,是最先給對方構成威脅的敵人,處在最先與敵人發生衝突的境地,因而成為敵方最先要殺戮和擄掠的對象,這使他們成為最早的被“捉生”者。
明廷及遼東總兵官等對“墩夜”的地位和處境非常清楚,所謂“墩夜二項,了操傳報,其險苦艱難,比之別軍懸殊,若非加厚優給,何以責其用命?”;“沿邊夜不收及守墩軍士,無分寒暑,晝夜瞭望,比之守備,勤勞特甚。”因此多次出台優待這些士兵的政策,給“出哨夜不收”增加俸餉,對於被殺傷者厚加賞恤等,體現了“夜不收”等擔負偵察任務的兵丁在明遼東邊防前線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
實際上,“夜不收”之稱不僅反映了從事偵察任務的士兵的身份,很可能在當時遼東總兵之下已經建有“夜不收”的偵察兵兵種,從以下《遼東志》一段文字中出現“預定夜不收”和“存留夜不收”情形看,顯然另有一番深意:
“每歲冬,鎮守總兵官會同督理軍務都御史太監奉敕移文各路副參游擊守備備御提調守堡等官,遵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兵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沿燒野草盡絕,聽令安營吹號笛打鼓,聚官發放畢,夷人精銳至營外求見,發牌開門,鼓吹齊舉,通事引入拜見,量給酒肉令出。隨開營回兵入境。時兵馬各令附近屯堡休息,存留夜不收並標下官軍站立一營,圍夷人多寡,攜婦女老幼入關門投見,令通事譯傳,宣布朝廷恩威,地方厲害,量給卓面酒肉鹽米針布胭粉靴蠛之類。或有號稱大頭領及預有報事等項勞動者,亦賞牛羊段襖銀牌之類。賞畢,夷人出境,兵馬俱在邊宿歇,次日歸城。”
此外,《灤陽錄》卷一有“夜不收”條,有詩云:主寢僧房古塞秋,皇莊酒局報河流。駝羊百萬青青草,樂土無如夜不收。又有“未至建昌縣六十五里,站名夜不收,平川曠野,極目蒼然,牛馬駝羊成群散合,地甚膏沃,而無一畦,都是豐草,畜牧之利大於稼穡可知也。”
將上文與《灤陽錄》中“夜不收”的地名以及當地的生態環境聯繫起來分析,“夜不收”似乎在明朝邊境“燒荒”中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而以“夜不收”名地名,可知其時“夜不收”之盛名也。
從明代遼東地方遺留下來的檔案來看,明朝方面“哨探夜不收”的偵察活動最初主要是針對蒙古諸部的。因為“正統以來,瓦剌漸強,東並諸夷,西結諸衛,以撤我之藩籬,所以屢為邊患。”如萬曆九年三月初八日,《三萬衛經歷司為“竊賊”捕擄永寧堡哨夜事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的呈文》中稱:
“據守永寧堡衛鎮撫劉維藩呈稱,本月初三日辰時分,據本堡北方值了軍人周雲稟稱:了見沿邊空心樣台舉放炮火,左右鄰台一齊接舉,一面差夜不收楊彪等分投走報,一面帶領馬步官軍出堡迎敵,途遇本台值日甲軍孟堯稟稱:了見境外溝內突出掩伏竊賊約有十數余騎,撞遇預差出哨夜不收洪阻二、薛祥等二名……躲避不及,被賊擄去……具呈到職。據此,緣系竊賊捕擄哨夜事理,擬合呈報。”
又如萬曆九年四月,義州衛指揮使司“為境外哨探被擄事”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的呈文中稟:本月初七日大鎮堡夜不收於賢等六人分為兩撥出境哨探,遇“從北來達賊二十餘騎”,各役奔走不及,有三人被擄去等情。
明朝文獻記載中,多以蒙古為“達”、“虜”,以女真為“夷”。明中前期,以女真諸部、朵顏三衛為阻隔蒙古之藩籬,“建州、朵顏、野人女真、海西等衛,皆我迤東藩籬,赤斤蒙古、沙洲等衛,則我迤西藩籬。昔太宗欲征瓦剌,必先遣使迤東迤西,厚加賞賚,以結其心。故我師之出,瓦剌遠遁。”並因此標榜“向來夷漢一家”,以致“墩台俱廢,哨了不設。”
說明此前的“哨探夜不收”主要是征對蒙古諸部的,而在與女真諸部相鄰的邊牆地帶、以及針對女真的偵察活動並未引起明廷的重視。直到努爾哈赤公開與明廷對抗時,明與女真諸部尤其是建州女真之間的偵察防禦才提到了明廷的議事日程,此後,明之“哨探”的偵察對象便主要轉向了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女真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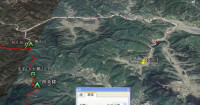
夜不收
萬曆四十六年(1618),遼東經略楊鎬在談到禦敵之術時,亦提出“偵探宜明”一條,“薊鎮舊有直撥、橫撥,直撥深入虜穴,察其情形;橫撥沿邊瞭望,接續飛報。自款貢日久,虜帳漸徙,直撥往齎米布,託處屬夷帳中,憑其口報。其橫撥又狃小利,或散而砍木采茵,多為夷所撲捉。”
這些材料說明,隨著遼東局勢的變化以及明與努爾哈赤衝突的不斷升級,明軍方開始加緊整頓偵察隊伍,加大了女真地區“夜不收”的派出數量。在隨後的滿文檔案中也開始有了關於不同時期明“哨探”深入后金國境內的記載。如:
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攻取清河之後,派八百人到沿邊收割糧食,臨行前努爾哈赤再三叮囑,為躲避敵人的襲擊,一定不要在同一地方避宿,“若在南山上住宿一夜,再往北山上住宿一夜。東邊山上住宿一夜,西邊山上住宿一夜”;並將八百人平分為二,分別往渾河南、北岸曬打糧食。但是這些人“違背了汗的誡諭,就在打糧場住宿。尼堪的哨探曾二三次前來窺探他們。九月初四日晨,尼堪出來了兵,襲擊了渾河南岸的嘉木湖村納林率領打糧食的四百人,被殺了七十人,其他三百三十人都逃了回來。”
這些記載說明,雙方統治集團在偵察與反偵察領域展開的較量和鬥爭,已經上升到白熱化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