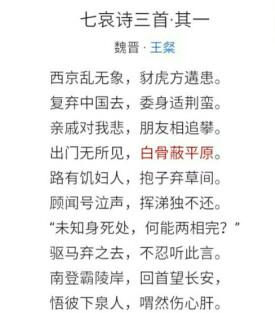七哀詩三首
漢末文學家王粲創作的五言古詩
《七哀詩三首》是漢末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càn)所創作的一組五言古詩。
其中第一首詩寫詩人初離長安在郊外所見難民棄子的慘狀,感嘆於盛世的難得。第二首詩寫詩人久客荊州,懷鄉思歸,日暮憑眺,獨夜不寐,觸處都生悲愁,表達了他的政治苦悶,以及寄居異地、懷念家鄉的寂寞憂傷之情;第三首詩寫邊地的荒涼和人民為戰爭所苦,深刻反映了漢末動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強烈傾訴了詩人對社會現狀的哀思。
這三首詩中,以第一首最廣為流傳,它真實地描繪出一幅悲慘的離亂的畫面。
七哀詩三首
其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
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其三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
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
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
登城望亭燧,翩翩飛戍旗。
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
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
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
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1.七哀詩:漢樂府中不見此題,可能為王粲自創。七哀,表示哀思之多。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文選》呂尚說:“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嘆而哀,鼻酸而哀也”。
3.無象:混亂得不成樣子。象,法度。
4.豺虎:指董卓部將李傕(jué)、郭汜(sì)等人。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五月,李、郭等人合圍長安,六月入城,燒殺擄掠,城中死者萬餘人。
5.遘(gòu)患:作亂。遘,通“構”,構成。
6.中國:京師。帝王所都為中,故古稱京師為中國,這裡指長安。
7.委身:託身。委,託付。
8.適:往。
10.追攀:攀車相送。依依不捨的情狀。
11.蔽:遮蔽,遮蓋。
12.棄:丟棄。
13.顧:回頭看。
14.號泣聲:指棄兒的啼哭聲。
15.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句是“飢婦人”的話,意思是:連自己也不知身死何處,又怎能兩相保全呢?完:全,保全。
16.驅馬棄之去:指詩人自己,因不忍看此慘象,連忙策馬走開。
17.霸陵:漢文帝的陵墓,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漢文帝是兩漢四百年中最負盛名的皇帝之一,這個時期的社會秩序比較穩定,經濟發展較快,連同其後的漢景帝時期被史家稱為“文景之治”。所以王粲在這裡引以對比現實,抒發感慨。
18.岸:高原,文帝陵因山起陵,建於原上。
19.悟:領悟。《下泉》,《詩經》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20.喟(kuì):嘆息。
21.滯淫:長久停留。
22.方舟泝大江:方舟,方形的小船。泝(sù),通“溯”:逆流而上。
23.岩阿(ē):到處都是岩石的山阿。阿,山丘。
24.增重陰:更黑暗。
25.裳袂(mèi):下衣裙和上衣袖子。袂,袖子。
26.攝:整理。
27.絲桐:指琴,古人削桐為琴,揀絲為弦,故稱。
28.羈旅:被羈絆而旅居在外,引申為長久寄居他鄉。
29.壯:盛,指憂思深重。
30.難任:難以承受。
31.更(gēng):經歷。
32.截:截取,引申為凍傷。
33.當遲:膽敢遲緩。
34.亭燧(suì):古代築在邊境上的烽火亭,用作偵伺和舉火報警。
35.翩翩飛戍旗:戍邊的旗子翩翩起飛。
36.行者:逃難的人。
37.反,同“返”,返回。
38.樂土:安樂的地方。見《詩經·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39.茲(zī):此,這裡。
40.蓼(liǎo)蟲:吃慣了蓼(一種有辣昧的草)的蟲子已經不感到蓼是辣的了,比喻人為了所好就會不辭辛苦。蓼:水蓼,植物名,味辛辣。
41.諮(zī):同“咨”。徵詢,商議。
其一
都城長安混亂無序,如狼似虎的董卓構成了這場禍亂。
離開了居住多年的中原地帶,託身來到南方的荊州避難。
親戚對我表示悲傷,朋友攀著我的車轅告別。
出門映人眼帘的,是白骨累累的大平原。
路邊有一個飢腸漉漉的婦女,正把親生的嬰兒放進草叢中丟棄。
她雖然回頭聽到了嬰兒的號哭.但還是揮淚毅然離去。
“我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死,我母子兩人都保全怎麼可能呢!”
我趕緊策馬離開此地,不忍心再聽到飢婦的哭訴。
向南邊走過漢文帝的陵墓,回頭眺望混亂中的長安城。
這時候我才理解了寫《下泉》詩的作者的心情,想到這裡不由自主地嘆息起來。
其二
荊州不是我的家鄉,卻長久無奈地在這裡滯留?
極目望去,大船在江心正溯流而上,天色漸晚更勾起我思鄉的情愁。
山坡上映著太陽的餘暉,溝岩下的陰影顯得更加灰暗。
奔跑的狐狸忙著趕回自己的洞穴,飛翔的鳥兒在鳥巢上盤旋。
大江上涌動的浪花轟然作響,猿猴在臨岸的山林長吟,
迅猛的江風掀起我的下衣和衣袖,秋天的露水打濕了我的衣襟。
夜深了我孤獨難眠,便又披衣起床拿起了桐琴。
桐琴象理解我的心思一樣,為我發出悲涼的鄉音。
在外寄人籬下什麼時候才是盡頭,心中充滿了難以排遣的憂愁。
其三
邊城的荒涼使人悲傷,過去我就曾經到過這個地方。
冰雪象刀一樣割裂皮膚。大風颳得就沒有停止的時候。
方圓百里不見人煙,草木茂盛卻沒有人來管理?
登上城樓遙望烽火台,只見滿城飄動的都是獵獵招展的戰旗。
行軍的人不準備再返回家園.出門時就已經與家人作了長別。
幾個孩子都已經被敵方俘虜了,我們為此已經哭了好長時間。
天下可供安居樂業的地方很多,何苦一直在這個地方呆下去呢?
這就象蓼草上的蟲子長期吃辣一樣,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請不要與我們再談離開邊城的事。
其一
此詩寫於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這年六月,董卓部將李催、郭汜在長安作亂,大肆燒殺劫掠,這時王粲逃往荊州,依靠劉表以避難。此詩是王粲初離長安往荊州時所作。當時他是十六歲。
其二
詩中詩人抒寫自己久客荊州思鄉懷歸的感情。內容和詩人著名的《登樓賦》相似。大約同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荊州時的作品。
其三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劉表病死,同年九月曹操大軍逼向荊州。王粲因勸說劉表之子劉琮歸降曹操有功,被曹操委任為丞相掾,並賜爵關內侯。王粲歸附曹操后,曾隨曹操南征北戰,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此詩就是寫邊地荒寒、人民深受戰爭之苦的詩作。
第一首詩中,“兩京”六句寫詩人離開長安的原因和辭別親友而執意去荊州的情景。“西京亂無象,豺虎相遘患。”勾勒了當時長安兵亂的情景和不得不離開的形勢。“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王粲原住洛陽,因董卓兵亂遷居長安,這時又因兵亂離長安,所以說“復棄”。詩人從洛陽西遷長安,往事極其殘忍凄慘。事隔兩年,又在大亂中離開長安,情景更加可悲。“復棄”二字表現了詩人無限的哀思和回顧。“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詩人與親友離別,他們悲傷,他們追著、拉著,依依不捨。著墨不多,卻把當時悲痛的離別場面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這裡用了互文的修辭手法,既是說親戚,也是說朋友,“相追攀”,即“對我悲”,既是說朋友,也是說親戚。
“出門”以下八句寫詩人出長安城后目睹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是當時中原地區遭受戰禍洗劫后的慘酷景象的真實寫照。出門所見是白骨蔽野,目不忍睹,這是豺虎遘患的罪證。據史籍記載,當時吏民死於戰亂者萬餘人,事後兩二三年,關中全境“無復人跡”。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寫:“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如果說“白骨蔽平原”是典型環境,那麼接下六句寫婦人棄子則是典型事件,作者極力烘托這一悲劇,一是有力地揭露了慘苦莫比的現實,更是為後面的抒情張本,活生生地再現了戰亂年代下層人民的痛苦和絕望。而這一節也頗為後人激賞和模仿。它是一種典型化的手法。吳淇說:“單舉婦人棄子而言者,蓋當亂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於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這種“舉重帶輕”的手法對後世極有啟發,杜甫《無家別》、《垂老別》,深受其影響。
最後六句寫詩人因“所見”而感慨不已。”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飢婦棄子使詩人目不忍睹,更是不堪其言,只能驅馬離去。“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詩人登上霸陵高地,回首悵望長安。霸陵是西漢文帝劉恆的陵墓,在長安東郊,是長安通往荊州的必經之路。從旅程說,到了霸陵,離開長安較遠,真的要和長安告別了。一股沉痛而依戀之情湧上心頭。文帝是西漢的中興君主,詩人到了霸陵時免不了要思念“文景之治”。然而,對照長安眼前的慘狀,像文帝那樣的賢明君主在哪裡呢?“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詩人感慨地說,現在我才深深地懂得了那《詩經·曹風·下泉》的作者對明王賢伯的思念了。哪裡能得到賢明君主以興太平呢?只有傷心哀嘆,肝腸摧裂。情感深沉熾烈哀怨傷悲。
詩人在詩中描繪了一幄悲慘的亂離圖,表現了漢末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
在第二首詩中“荊蠻”四句寫詩人久客荊州的苦悶和日暮乘船泛江時所引起的思鄉之情。起句自問,噴射出強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荊州的怨憤。為銷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銷愁愁更愁。江上日落餘輝,並船逆流而上,引起詩人思鄉懷歸的無限憂愁。“愁”字虛籠全篇,詩篇始終處於這悲愁的氛圍之中。
“山岡”以下八句寫日暮時的自然景色,抒發詩人思歸的凄苦之情。詩人攝下了落日西沉時大自然姿態的倏忽變化:山脊之上猶存夕陽餘輝,山谷本來就很陰暗,天將晚則更顯得陰暗幽深。起兩句寫了山色秀拔,給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將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種凄清氣氛。“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這兩句取《楚辭·哀郢》“鳥飛還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時刻,狐狸歸穴,鳥下窠巢。狐狸和飛鳥尚且思歸自己的穴巢,何況於人。“流波激情響,猴猿臨岸吟。”湍急的江流聲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邊凄厲嘶叫,氣氛越發凄涼。“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風吹動著衣袖,陰涼的露水沾濕衣裳。詩句點明秋季。秋風蕭瑟迅猛,白露陰寒濕衣,氣氛更為陰冷。以上八句詩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涼的景色,來映襯自己內心思鄉念歸的悲凄。情動於中而發於景,景見真情而感人。對仗優美,音韻和諧,節奏感強烈,讀來十分流暢。這樣的例子古詩里固然少見,在建安詩里也是極少的。它已經突破了漢詩古樸渾厚的風格,下開兩晉南朝風氣了。
“獨夜”以下六句,由寫景轉入集中抒情,寫詩人夜不能眠憂思難忍的情狀。“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羈旅之客難以返歸,愁思不絕,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攝衣起撫琴”,暗示著一種煩憂的過程。接下兩句,詩人以擬人手法賦物以人的情感,藉以襯托、強化思歸感傷之情。琴也通曉人的心情,為詩人的不幸而哀鳴。這“悲音”體現了詩人無處寄託又無從宣洩的哀愁。通過物之情表現人之情,這是傳統詩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寫手法。最後兩句悲憤低沉,哀怨不絕。寄居他鄉永無盡頭,沉重憂傷難以承擔。這悲憤的結句同扣篇首詩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飾愁思深重的離人形象,令人黯然神傷。
王粲久留荊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時此地,他憂多、愁多、憤懣多。這首詩抒發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詩人政治理想不能實現、個人抱負無從施展的憂憤心情的流瀉。詩中具有相當強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增添了抒寫思歸之情的濃郁效果。
在第三首詩中“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起句一開始詩人就為使人心悲的邊城慨然長嘆,充滿了辛酸凄愴。詩篇開門見山點明題意,這在古詩和古樂府中是幾乎看不到的。“悲”字是這首詩的詩眼,統攝全詩,也是此詩主意所在。接著,詩人申述了邊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寫邊地嚴寒、人稀、荒蕪。“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樣割著人的肌膚,大風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是冰、雪、風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慄。“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這設問,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寫戰爭給邊地人民帶來的痛苦。登城遠望烽火台,只見邊防駐軍的戰旗在朔風中紛紛飄揚、搖曳、戒備森嚴,氣氛緊張。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頭,不思返歸。留下的人,多被敵軍俘虜,沒完沒了地哭泣。可見邊地人民遭受敵軍蹂躪之慘,苦難之深。從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虜,這是造成“百里不見人”的主要原因。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停的殘酷戰爭,使邊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後四句寫詩人的憤激之情和悵然感嘆。“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這一反詰句流露了詩人強烈的哀怨情緒,表現了詩人對邊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關切。“蓼蟲不知辛,去來忽與諮。”蓼蟲喜歡吃苦辣的東西,因此說“不知辛”。這兩句是說,那些像蓼蟲一樣長期吃苦而不知什麼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談遷徙的事是沒有用的。言外之意,戰爭使人民習慣了,麻木了。這裡凝聚了詩人無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詩人對此無能為力的惆悵哀嘆的情緒。
王粲的《七哀詩》雖以哀痛感傷為主要基調,但哀痛而不消沉,感傷而不失望,在哀痛感傷中包含著希望。他希望出現治世,希望舒展才幹,希望息兵止戈,這都體現了廣大人民的情緒和願望。
清代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仲宣《七哀》,首篇起六句,點題交待耳,而敘事高邁,沈雄闊大,氣象體勢,騫舉清惻。“出門”以下,又以中道所見言之,情詞酸楚,直書所見,至不忍聞,《小雅》傷亂,同此慘酷。“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轉換振起,沉痛悲涼,寄哀終古。
清代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六)》:“出門,以下,正雲‘亂無象’。兵亂之後,其可哀之事,寫不勝寫,但用‘無所見,三字括之,則城郭人民之蕭條,卻已寫盡。復於中單舉婦人棄子而言之者,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於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
清代張玉谷《古詩賞析(卷九)》:“出門”十句,敘在途飢荒之景,然臚陳不盡,獨就婦人棄子一事,備極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顧,塞路死亡,不言自顯。作詩解此舉重該輕之法,庶幾用筆玲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