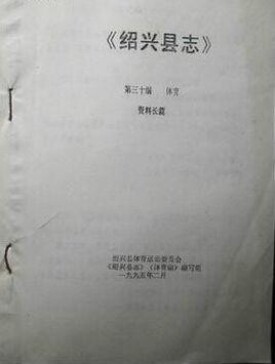紹興縣誌
1981年修志的紹興縣史書籍
記錄紹興縣歷史事件以及發展進程的書籍,1981年開始修志。
《紹興縣誌》的出版,可能已是浙江省第一屆社會主義時期新方誌中市、縣誌的關門之志。本屆修志始自1981年,迄今已歷十餘載,在此期間,市、地、縣誌書先後大量出版,緣何紹興縣誌書出版處在最後?這是一個耐人思考的問題,其實是一項深思熟慮的高明之舉。紹興縣修志,黨政領導格外重視,部門全力支持,調集精兵強將,組成合理的修志班子,同時,而且異乎尋常地努力,修志的客觀條件,經費、用房、設備等也都得到充分保證。他們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洞悉責任之重,修志之難,不滿足修成一部一般之志,強化質量意識,決心下大力氣,編出一部非同一般的,無愧於文化名城,無愧于越中父老,無愧於偉大時代的志中佳作,文化精品。
志書的生命在於志書的質量。縱觀修志歷史,前事可鑒。精心編纂的宋《嘉泰會稽志》、《寶慶續會稽志》,被稱為“志中雙傑”,歷代評價甚高:“詳略得中,紀敘典核,而鑒裁精當,亦地誌中之極有體要者”;“不漏不支,敘次有法”、“條理縝密”等,僅管迄今已歷八百年左右,仍然為人稱道。相反,有的志書,雖然成書較快,卻因“繁簡無法”、“筆力萎弱”,差謬甚多而被人擱置,似有若無。可見修志之道,事倍才能功倍,並無捷徑可通。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本屆修志首先出版者的開創之功,不能低估這些志書對本屆修志的巨大推動作用和借鑒功能。但是修志畢竟不是競賽場上的角逐,不能以時間來確定質量,安排名次。固然,后出的志書其質量也未必註定優於前面出版的志書。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善於學習,總結經驗,不斷創新,有所發展,取他人之長,補己之不足,還要人十之,己百之,加倍努力,才能攀登新的高峰。老天不負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讀了《紹興縣誌》我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后出版的《紹興縣誌》從三個方面下了大力氣:其一,收集、整理、印行紹興著名的舊志,以及其他大量相關的書籍、資料;其二,認真吸取歷代修志和本屆修志的經驗和教訓,使認識來一個升華和飛躍;其三,從紹興縣的實際出發,認真調查、研究,不斷聽取各方專家、行家的意見和建議,多謀善斷,精心編纂。為此,《紹興縣誌》起點高,基礎實,不斷完善,精益求精,終於大器晚成。其中有許多值得重視的地方,現略舉其要:
第一,不同凡響的“凡例”。本屆修志一般來說比較忽視對“凡例”的制定。其實“凡例”不可低估,體現了一部志書的指導思想、編纂原則、具體規定以及對一些矛盾問題的解決辦法。本屆修志之初,理論準備欠缺,實踐經驗不足,難以制定出比較完備的“凡例”。因此,不少志書的凡例,只是大同小異的簡單幾條,有的甚至相互套用。紹興縣修志同行深感制定“凡例”的重要。一部志書的發凡起例,既是修志的經驗升華,又是編纂全書的指導,其間大有學問在。為此,制定“凡例”四十條,值得同行和讀者的重視。
第二,深入挖掘資料,全志尚詳。資料是志書的基礎,志書的價值在於是否有全面、系統、翔實的資料,尤其可貴的是能夠核實、訂正人們忽視的一些差錯和佔有珍貴的獨家資料。當今,對本屆新志書的評議,比較共同的是,“志書有用,但又不夠用”。鑒於此,《紹興縣誌》在資料工作上狠下功夫,花了許多時間大量收錄、精心選擇古今各類資料,為全書打下了厚實的基礎。諸如“建置”,從秦王政二十五年開始,歷記漢、三國、晉、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變化,給人以完整、系統的認識。對“區域”的記述,細到歷記各個不同階段的具體變化。在“土地”編中,詳記紹興的土地開發,包括“撩荒墾殖”、“圍湖造田”、“圍塗造田”等;“土地制度”中,關於“私有制”,詳記自秦之後,直至民國,歷代私有制的具體狀況及其變化。既有翔實的資料,又有豐富的知識,這是他志所少見的。
第三,從實際出發,著力顯示紹興固有的特色。地方志要重視地方特色和時代特點,已成為方誌界的共識,許多志書都做到了這一點。《紹興縣誌》對紹興地方特色的記述,不滿足於立篇、設章、列目,不滿於一般記述,點到為止,而是引用大量資料,認真研究,加以分析深化。紹興為百越之首,越中山水,社會經濟,風土人物,方言民俗等都極具特色,《紹興縣誌》對不少有特色的內容,緊緊抓住,充分展開,詳細記述。不少章節類似專記,十分翔實、耐讀。如紹興是著名江南水鄉,“紹興之發展史,實為治江治水之歷史”,為此,水利設專編詳記。其中對鑒湖的記述尤詳,包括鑒湖開發的歷史、功能、歷代關於鑒湖的爭議以及歷代對鑒湖圍墾的情況等等。在“文物”中突出文化遺址、越窯遺址、陵寢墓冢、古代建築等,反映了紹興作為文化之邦的特色。在“黨派團體”中,記述著名的“光復會”,豐富了民國史的內容。在“人口”中,記述了流動人口和老齡人口等種種新情況、新問題,反映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變化。對一些極具特色的項目,如紹興師爺、墮民等均立專章,詳記其由來、變化、狀況以及種種爭議,並選輯了大量原始資料,供讀者查閱。
第四,志史結合,彰明因果。史和志既有密切的關聯,又有一定的區別。在一部志書中如何擺脫常規,處理好史體和志體的關係,這是一代新志值得研究的課題。《紹興縣誌》從實際出發,在志書中適當採用史體,作了可貴的也是成功的嘗試。如在卷首中設“史略”附“大事年表”,簡明扼要地記述紹興的悠久歷史,從新石器時代,舜、禹遺跡,越國基地等直至當今,脈絡清晰。同時詳列歷史大事年表,具體記錄重大歷史事件,給人以完整、系統、翔實的歷史過程的認識。這樣的設計比一般志書的“大事記”更加系統、厚實。各編的編前章前均設有無題小序,文風統一,內容簡明扼要,真正起到畫龍點睛,提綱挈領之效。在整個編目設計上,不僅注意歸屬得當,排列有序,而且力圖揭示因果,以顯示志書的深度。
第五,言必有據,引文注意註明出處。一部志書是由大量資料編纂而成。常見的不少志書,由於種種原因,較少註明資料來源和出處,因此使有的學者不敢輕易引用,也使人難以深入核查志書以及有關資料,以便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為此,《紹興縣誌》對大量引文認真校核,並註明出處。如“大事年表”和志書中應用的許多資料均一一註明資料來源,這是一件十分細緻的工作。當然,要事事註明出處,勢必增加大量篇幅,這是難以做到的。
第六,認真編好索引。工具書以及學術著作做出索引,以便於讀者查閱、使用,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當今國際所通行的。浙江出版的不少志書已編有索引,受到讀者歡迎。但一般來說索引編纂較為簡單,這是美中不足。《紹興縣誌》編纂者有感於斯,花了極大的功夫編出了比較詳細的索引,並與《叢錄》合列為一卷,這是很值得稱道的。
第七,注意記述事物發展的具體過程,細節生動,文風優美。當代已經出版的有些志書,敘事比較簡單,缺乏過程,因此,可讀性不強。《紹興縣誌》比較注意記述典型事例,通過記實,體現事物發展本身的曲折性、生動性。行文注意概括、簡潔,優美、生動,可讀、耐讀。其中有些章節使我愛不釋手,一讀再讀,這是其他志書所比較少見的。此外還可以列舉一些,鑒於篇幅,這裡不一一細說。
《紹興縣誌》的成功證明“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專家修志”的基本格局是十分正確的。而且三者相聯,缺一不可。紹興縣幾屆黨政領導都十分重視修志,早已將此項工作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之中,經常關心,提出要求,並創造優越的修志條件。修志部門的人員結構合理,相互補充,尤為可貴的是有一批具有相當水平,又鐵心修志的修志人員。在這裡“求實、創新、協作、奉獻”的修志行業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現。為此,歷經八年之久,一部高質量、高水平志書的問世,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凡例
史略
大事年表
第一冊 地域 社會
第二冊 經濟 政治
第三冊 文化 人物
第四冊 叢錄 索引
紹興縣大事年表
記事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迄1998年3月。採用編年體,酌用本末體。所錄史事,力求反映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並撮敘要點,註明出處。因史籍浩繁,一事有多處記載,則只選用經史子集和歷史文獻之有權威者,一般襲用舊籍文句。對某些純屬地方史事,遂引用舊志。中華民國之後,則多用檔案、報刊資料。如此之類,均為便於檢索、瀏覽,粗知縣事發展之要略。
新石器時代
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
“河姆渡文化”,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第三、四層距今約7000~6000年之新石器時代文化,稱“河姆渡文化”。
1973年在浙江餘姚縣河姆渡村發現。這個文化遺址中最大一個碳14數據為6955±120年。歷史考古學家認為這裡可能是于越先人之活動地區,距于越中心(紹興)東約69公里。(《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
約公元前3300~前2300年
“良渚文化”在農業、紡織、治水、制陶等方面有很高成就。這個文化類型中碳14測得有代表性數據為5260±135年(錢三漾)和4330±145年(嘉興雀暮橋)。可以認為是于越先人文化,距紹興西北約100餘公里。(《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
約公元前3000年
馬鞍仙人山文化遺址,1985年在紹興馬鞍山寺橋村仙人山發掘之“仙人山文化遺址”,面積約8000平方米,試掘110平方米,文化內涵與鳳凰墩遺址相同,早期屬“良渚文化”,晚期為“馬橋文化”,上限約5000年。距城區北18公里。(《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年))
約公元前2500年
紹興馬鞍鳳凰墩文化遺址,1983年發現、1984年發掘之紹興馬鞍山寺橋村鳳凰墩文化遺址,分佈面積約6000平方米,發掘面積400平方米,經編號出土文物有120多件,主要為石器、玉器和陶器等。
文化層大致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相類又獨具紹興文化特徵。距今約4500年,證明于越先人已在這些孤丘上生活。(《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年))
傳說時代
約公元前22世紀前後
姚丘,“在上虞縣西四十里,一名桃丘,俗傳舜所生處”。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
帝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五帝本紀》、《史記·五帝本紀》引《會稽舊記》、《嘉泰會稽志·拾遺》、《史記·夏本紀》)
約公元前22世紀至前21世紀前後
“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會稽之名始此)。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今紹興存有禹冢。
“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
“舜崩,禪位命禹”。“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越絕書·記地傳》、《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20世紀前後
禹崩,“以天下授益(舜子),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史記·夏本紀》、《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夏朝 于越
約公元前20世紀至前19世紀
“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餘。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才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餘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于越之稱始此。(《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商周 于越
約公元前17~前16世紀間
陶里壺瓶山文化遺址,1984年發現,1991年初步發掘之紹興陶里壺瓶山文化遺址,分佈範圍約20000平方米,發掘335平方米,出土石器、玉器和夾砂紅陶器等。屬商周時期,距城區北15公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報告)
周成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11世紀)
“于越來賓”。是為于越有歷史記載之始。(今本《竹書紀年》)
周穆王三十七年(約公元前10世紀)
春秋 于越
約公元前12~前10世紀
袍谷古文化遺址,1981、1986年在紹興袍谷里谷社村兩次發掘之袍谷古文化遺址,分佈範圍約10000平方米,發掘面積150平方米,出土文物150多件,主要為陶器、石器、玉器和網墜、板瓦等。上限為春秋戰國時期及以前,下限接近西漢。(《考古》1989年第9期《浙江紹興袍谷遺址發掘簡報》)
周定王六年(前601)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左傳·宣公八年》)
周景王元年(前544)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余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弒吳子余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引《春秋左氏傳》)
周景王七年(前538)
春,“靈王會兵於申,僇(辱)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史記·楚世家》)
周景王八年(前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