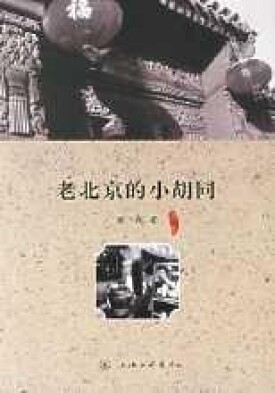老北京的小衚衕
1999年蕭乾創作的書籍
《老北京的小衚衕》是由蕭乾編著,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發行的書籍。
《老北京的小衚衕》由北京海納博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攜新世界出版社於2014年11月再版發行,並由蕭乾夫人文潔若親自審定、親筆作序。
蕭乾(..~..)著、翻譯,北京。“北京”北京——汁味北京腔。北京合院、北京胡、北京糖葫蘆、北京驢滾、北京土,煙,覽遺。
蕭乾(-),蕭秉乾,蒙古族,作家,文學翻譯家。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家和出色的翻譯家。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中文系后,主編《大公報·文藝》。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英文版《人民中國》和《文藝報》副總編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是第五、六屆政協委員,第七屆政協常委。著譯有小說、散文集三十餘種。1999年2月11日因心肌梗塞及腎衰竭在上海醫院逝世,享年89歲。
北京胡(選市七級二語課)北京胡。未爸爸管,北城角早。漂泊,思鄉,北京角落。識始。
還是位老姑姑告訴我說,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衚衕出生的。七十年代從“五七”幹校回北京,讀完美國黑人寫的那本《根》,我也去尋過一次根。大約三歲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們家好像是坐西朝東,門前有一排垂楊柳。當然,樣子全變了。九十年代一位攝影記者非要拍我念過中學的崇實(今北京二十一中),順便把我拉到羊管衚衕,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張。
其實,我開始懂事是在褡褳坑。十歲上,我母親死在菊兒衚衕。我曾在小說《落日》中描寫過她的死,又在《俘虜》中寫過菊兒衚衕旁邊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夢。
母親去世后,我寄養在堂兄家裡。當時我半工半讀:織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畢業(1927年冬),因學運被變相開除,遠走廣東潮汕。1929年雖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學,但那時過的是校園生活了。我這輩子只有頭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衚衕里。那以後,我就走南闖北了。可是不論我走到哪裡,在夢境里,我的靈魂總在那幾條小衚衕轉悠。
啊,衚衕里從早到晚是一闋動人的交響樂。大清早就是一陣接一陣的叫賣聲。挑子兩頭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黃瓜”,碧綠的葉子上還滴著水珠。過一會兒,賣“江米小棗年糕”的車子推過來了。然後是叮叮噹噹的“鋦盆鋦碗的”。最動人心弦的是街頭理髮師手裡那把鐵玩藝兒,嗞啦一聲就把空氣盪出漾漾花紋。
我最喜歡聽夜晚的叫賣聲。顧客對象大概都是燈下斗紙牌的少爺小姐。夜晚叫賣的特點是徐緩,拖尾,而且當中必有段間歇——有時還挺長。像“硬面——餑餑”,中間好像還有休止符。比較乾脆的是賣熏魚的或者“算靈卦”的。最喜歡拉長,而且加顫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爺——太(哎)太——有那剩菜——剩飯 ——賞我點吃吧。”
那時我是個窮孩子,可窮孩子也有買得起的玩具。兩幾個錢就能買支轉個不停的小風車。去隆福寺買幾個模子,黃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餑餑。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風箏的世界。闊孩子放沙雁,窮孩子也能有秫秸糊個屁股簾兒。反正也能飛起,襯著藍色的天空,大搖大擺。小心坎可樂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還常鑽到東直門的蘆葦塘里去捉蛤蟆,要麼就在墳堆旁邊逮蛐蛐——還有油葫蘆。蛐蛐會咬架,油葫蘆個頭大,但不咬。它叫起來可優雅啦。當然,金鐘更好聽,卻難得能抓到一隻。這些,我都是養在泥罐子里,每天給一兩顆毛豆,一點水就成了。
北京還有一種死胡同,有點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見不到陽光。北京衚衕里的平房,多麼破,也不缺乏陽光。
衚衕可以說是一種中古民用建築。我在倫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見到過類似的衚衕。倫敦英格蘭銀行旁邊就有一條窄窄的“針鼻巷”。很像北京的衚衕。在美洲新大陸就見不到。他們捨得加固,可真捨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現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兩次過獅城,很有東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認不得了。幸而他們還保留了一條“牛車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裡吃碗排骨茶。邊吃邊想著老北京的豆漿油炸果。
但願北京能少拆幾條、多留幾條衚衕。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
第一段(1—4):總寫作者與北京衚衕的關係——在此出生,成長,認識世界。
第二段(5—10):具體回憶兒時生活過的北京衚衕的風土人情,
第三段(11—13):別處的衚衕和北京的對比,突出北京衚衕的獨特魅力,突出作者對北京衚衕的懷念。
書名 老北京的小衚衕
作者 蕭乾

老北京的小衚衕
定價 35.00
出版時間 2014.11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和翻譯家
富有傳奇色彩的二戰記者
現代文學史上最有影響的大師之一
作品多次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蕭乾夫人文潔若親自審定、親筆作序
一部“老北京”深情敘說老北京前世今生的作品
——巴金
他(蕭乾)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在文學創作上,他是個多面手,他會創作,會翻譯,會評論,會報導……像他這樣的,什麼都來一手的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上,是罕見的。
——冰心
他(蕭乾)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他的為人,他的創作態度呢,我認為只有一個“鄉下人”,才能那麼生氣勃勃勇敢結實。我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
——沈從文
蕭乾(1910.1.27~1999.2.11),原名蕭秉乾,蒙古族。世界聞名的記者,卓有成就的翻譯家、作家,原中央文史館館長,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訪歐美及東南亞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寫出了三百多萬字的回憶錄、散文、特寫、隨筆及譯作。主要著譯作有《籬下集》《夢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冊》《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蕭乾是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地道的北京人。本書可以說是“老北京”說老北京——原汁原味的北京腔。衚衕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它記下了歷史的變遷、時代的風貌,並蘊含著濃郁的文化氣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風情博物館,烙下了人們各種社會生活的印記。書中,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衚衕、北京的糖葫蘆、北京的驢打滾、北京的風土人情,如煙往事,一覽無遺。文字生動細膩,真切感人,文風嚴謹,讀之令人沉迷。
輯一衚衕浮世繪
籬下03
落日12
一隻受傷了的獵犬19
矮檐24
栗子36
皈依44
郵票57
曇66
鵬程77
輯二衚衕里的紅塵
參商91
蠶104
道旁112
俘虜124
雨夕132
印子車的命運137
鄧山東144
花子與老黃152
小蔣162
輯三衚衕心語
往事三瞥171
北京城雜憶178
東車站197
一個北京人的呼籲199
老北京的小衚衕208
東直門211
一本褪色的相冊214
小黑的友情249
終身大事251
我與蕭乾的文學姻緣
文潔若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筆名寫了三篇小說和隨筆,從東京寄給《國聞周報》。不但 都發表了,還收到編輯寫來的熱情洋溢的鼓勵信,這件事無疑對我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後來聽姐姐說,《大公報·文藝》是年輕的作家兼記者蕭乾主持的,《國聞周報》文藝欄也由他兼管,說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寫的。念高中時,又讀蕭乾的長篇小說《夢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聽到蕭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經由清華外文系畢業,在出版社工作兩年半了。一天,編輯部主任突然跑進我們的辦公室來說:“蕭乾調到文學出版社來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電影劇本,暫時不來上班。如果有什麼稿子想請他加工,可以通過秘書送到他家裡。”
一
我提請蕭乾加工蘇聯小說《百萬富翁》的中譯文。此書當時社會上已有了三個譯本,這是第四個了。譯文生硬,在校對過程中,不斷發現不通順的句子,校樣改到第五次還不能付梓。雖不是我發的稿,我卻主動承擔了在校樣上逐字校訂的任務。
五十年代初,很多蘇聯作品都是像這樣根據英譯本轉譯的。改完后,仍不滿意,因為原來是直譯的,佶屈聱牙,儘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譯文“信達”,以我那時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後,校樣改回來了,我琢磨了許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經蕭乾校訂后,做到了融會貫通,甩掉了翻譯腔,頗像創作了。這麼一來,這最後一個譯本,才真正做到了後來居上,超過了前三個譯本。
按照制度,校樣得退給校對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譯文以及蕭乾的改動都抄下來,研究該怎樣校訂和潤色稿件。後來聽說蕭乾終於上班了,就在我們的樓下辦公。
蕭乾的答覆是,這個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見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譯,完全可以這麼譯。但譯者願意那麼譯,也不能說他譯錯了。這不是黑白錯,屬於可改可不改的問題,既然是別人譯的,以不改為宜。在認識蕭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歲時能考上競爭性很強的清華大學,在校期間成績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崗位后,對編輯工作也能勝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這個年齡已做出多少成績來鞭策自己。
編輯工作的質量和數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覺。一個織布女工在機器前偷懶,馬上會出廢品,一個編輯加工稿件時馬虎一點兒,毛病就不容易看出來。
二
倘若說,和蕭乾結婚以前,我已經以工作認真努力獲得好評的話,在他的影響下,文字也逐漸變得灑脫一些了,好幾位有名望的譯者都對我加工過的稿子表示滿意。
蕭乾說,倘若他有心搞翻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間,有的是機會,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聽聽音樂,休息休息,不願意再熬夜搞翻譯了。
我們結婚後,他在我的帶動下接連譯了三本書:《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和《好兵帥克》。《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印了八十萬部,一九八○年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英漢對照本,其他兩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稱讚《好兵帥克》的譯筆,說文字幽默俏皮,表達了原著的風韻。
三
他反對死譯或硬譯,認為譯文學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愴的,譯出后引不出同樣的感情,再忠實也是不忠實。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開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這漫長的二十二年,對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困難重重,談不上什麼成績。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繼續留在出版社工作,儘管多次搬家,總比流浪到外地要強多了。
蕭乾的最大志願還是搞創作,沒有條件從事創作時才搞翻譯。一九六一年春天,我聽到一個可靠消息,說要把他從農場調回來翻譯菲爾丁的《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便作為一條特大喜訊寫信告訴他。他的反應之冷淡,使我大吃一驚。他在回信中寫道:“我對翻譯這部小說,興趣不大。”
他是最早調回來的一個,後來從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夠搞翻譯,算是最可羨慕的人。
四
一次,香港《文藝》雜誌約我寫一篇遠藤周作訪問記。我事先把幾家圖書館所藏的二十幾本遠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問題,按照電話里約定的那樣只採訪了一小時,便寫出一篇三千字的訪問記《早春東瀛訪遠藤》,編輯部一字未改地予以發表了。
我們二人最喜歡用的詞是“teamwork”(合作),每逢我們一方有了緊急任務,就共同協作完成它。老三桐兒還沒正式學英文就聽懂了這個詞。他小時看見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說:“我長大了,當什麼也不當編輯,太苦啦!”他確實沒有當編輯,然而如今在美國費城,還是經常作畫到深夜。
我有時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長在這麼個環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賭博、吸毒,他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有時兩三點鐘才睡,蕭乾則習慣早睡早起,我幾乎剛躺下,他已起床到書房去寫作了。
(文潔若,翻譯家,作家,蕭乾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