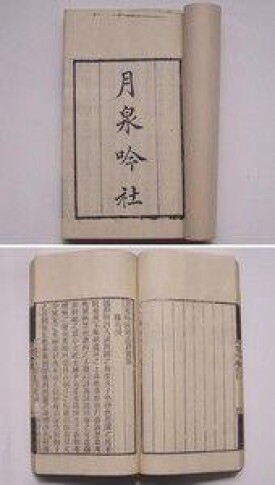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是元初宋遺民創立的人數最多、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遺民詩社,其作品《月泉吟社詩》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社總集。宋末浙江浦人吳渭曾官義烏令,入元隱居吳溪,創此社,請遺民詩人方鳳、謝翱、吳思齊等主持。詩作語句和平溫厚,沒有警拔之詞,卻多隱含追懷宋室之意,內容借歌頌田園風光來抒發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表明詩人自己不仕元朝的情操,具有深遠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詩社獨特的征詩活動,對後世的文人結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南宋末年,宋王朝經過長期的苟且偏安,已是風雨飄搖了。蒙古族鐵騎的長驅直入,使得南宋政權徹底覆滅,改朝換代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此時,宋末士子才深刻認識到他們失去的不只是一個趙宋王朝,而是作為天下文明象徵的整個華夏民族及其傳統文化。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一部分人選擇了投筆從戎,投入到實際的抗元鬥爭中去,更多的則是歸隱田園,藉助山水湖泊來抒發自己的憤懣之情,到大自然中尋求心靈的慰藉和獲取面對生活的勇氣。
雖然元朝統治者憑藉武力實施了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但在思想文化方面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因此,這些故宋遺民才得以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有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選擇了詩歌這一最便於抒情言志的文學樣式,藉以宣洩其抑鬱悲憤之情,從互相唱和的過程中,獲得堅守志節的力量。月泉吟社即在此背景下成立。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原宋義烏令浦江吳渭,入元不仕,退隱吳溪,延致方鳳、吳思齊、謝翱,共同創立了月泉吟社。這幾位月泉吟社的主事者在地方都頗具聲望。吳渭(生卒年不詳)字清翁,號潛齋;吳思齊(1238--1302),字子善,號全歸子,永康人,宋末曾任嘉興縣承;方鳳(1241-1321),字韶卿,亦浦江人,宋末任容州文學。宋亡后,三人皆矢志不仕元朝,退居田園。至於謝翱(1249--1295)則是抗元名士,字皋羽,號啼發子,福建福安人,曾為文天祥咨議參軍,后避地浙東,寫了著名的《登西台拗哭記》,悼念文天祥。
月泉吟社系得名於浦江名泉——月泉。據薛應旗《浙江通志》云:‘.其泉視月盈虛為消長”,故稱之月泉。因景緻優美,成為文人騷客聚會之所。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六日,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限五、七言四韻律詩,征詩四方,於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在短短的三個月間,共得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作者遍布浙、蘇、閩、桂、贛各省。方鳳等人評隙甲乙,選出二百八十名,於三月三日揭榜,依名次贈予獎賞,並將得名作品編集付梓月泉吟社成立和征詩宗旨。
《月泉吟社詩》為元初人數最多、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遺民詩社-“月泉吟社”所創作的作品,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社總集”。其作者大都為故宋遺民,由於處於特殊的時代,他們的詩歌創作不敢直言心聲,只能以隱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結。他們借歌頌田園風光以抒發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通過對忠臣義士的追慕和對現實的關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為元廷的官爵利祿所誘惑的孤介情操,表現自己隱逸抗節的志向,從而使文本內容具有深遠的思想價值和審美意韻。
吳渭(具體生卒年不詳),字清翁,號潛齋,浦江(今屬浙江)人,自幼穎異篤學,人品俊逸,博覽群書。宋末為義烏令“,國亡退食吳溪,慕陶靖節,自號曰潛齋”,延請宋遺民方鳳、謝翱、吳思齊,創立月泉吟社,相與酬唱品評。元至元間“,以春日田園命題,取靖節‘田園將蕪,胡不歸’之意”。應徵詩有2735卷,評選出280人,編成《月泉吟社詩》。
謝翱(1249~1295),字皋羽,自號日希發子,長溪(今福建霞浦)人,后徙浦城(今屬福建)。“父鑰性至孝,居母喪,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南宋度宗咸淳年間應進士舉,不第。1276年(元恭宗德右二年),文天祥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曾在嚴子陵釣台之西台哭祭文天祥。1295年(元成宗元貞元年),卒於杭州,享年47歲。著有《日希發集》《西台慟哭記》《天地間集》等。謝翱的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一生“為人倜儻,有大節”。
方鳳(1240~1321),一名景山,字韶卿,號岩南,浦江(今屬浙江)人。“鳳有異才,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后以恩授容州教授,因宋亡未赴,浪遊江南。歸鄉,名其齋為存雅堂,學者稱存雅先生。1321年(至治元年)卒,享年82歲。其遺詩有門人柳貫選刊為9卷,已佚。清初,同邑張燧在各種書中收錄殘剩詩文,編為《存雅堂遺稿》13卷,於1654年(順治十一年)刊刻。“鳳善詩歌,通毛鄭二家言”,宋末文弊,方鳳曾對學者說,“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
吳思齊(1238~1301),字子善,括蒼(今浙江麗水西)人。由蔭入仕,監臨安新城稅。調嘉興縣丞,攝縣事。后入鎮江幕府,因忤逆賈似道,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后辭官寓桐廬,自號全歸子。元大德五年卒,年六十四。流傳下的詩文不多,有《擬古》《題鹿苑寺壁間記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吳思齊性直愨,“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禾責、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
對故國的懷念
在古代,由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已形成了人們的思維定勢。而每當改朝換代之際,士人又總面臨著自身出路的抉擇,尤其是外族統治之朝,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南宋王朝的覆亡,對詩人們來說,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朝代更替,科舉的廢止對他們人生道路所造成的衝擊之大更是無法形容,然這又是他們必須面對而又不願面對的嚴峻現實。因而,懷念故國不仕新朝就成了他們詩歌的主要題材內容。如羅公福的詩: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
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葯旋澆。
放犢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
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遊魂入夢招。
詩歌首聯追敘自己棄官歸隱的行跡,開宗明義表示了自己寧老死林壑也不乞祿於當朝統治者的態度,從東風、林壑等景物之中可體味其脫離樊籠、復返自然的感受;中間兩聯正面描述田園生活,通過好雨、寒泉、秧、葯、犢、鶯、雲、柳等意象,展現出一種生意盎然的春日秀麗風光;尾聯化用謝靈運“池堂生春草”之意,以“生新草”這一具體事物來體現整個自然界一片萬象更新、蓬勃滋長的生機。然細讀就會發現,“生新草”是“見說”,以顯示這一片生機與自己的感情是有隔閡的;又用“入夢”二字,更見這一片生機對自己來說是恍恍惚惚而遊離於現實之外的。詩人正是通過這樣的敘寫,來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即含蓄委婉表達出自己對故國的深深思念和不願與新朝合作的心態。同時也使整個南宋遺民群體那種寧願老死林壑也不肯邁進蒙元“市朝”的共同心聲得到了完整巧妙的表述。
詩人們這種憑弔興亡、懷念古國之情,在卷中頻頻出現。如“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語流鶯”(王進之),亦同此意。而如“吳下風流今莫續,杜鵑啼處草離離”(栗里),則簡直是《詩經·黍離》之同調。詩人們借今昔之變傳達盛衰之悲,從而使得作品不僅具有幽邃深刻的歷史底蘊,而且把人類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強烈悲劇色彩展現得沉痛而又深刻,作品由此獲得思接千古、情系古今的恢弘氣勢和言近旨遠的藝術張力。誠如一位學者所言:“宋遺民詩不僅是宋詩的魯殿靈光,而且在整個中國遺民詩史上也是一塊里程碑。”
對忠臣義士的追慕
由於月泉吟社的成員大都是故宋遺民,他們十分重視名節,甚至把事二姓、仕異族,看成是像“女更二夫”一樣的不道德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視名節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所以對歷史上的氣節之士就自然流露出了無限的追慕之情。如詩人們對歷史上最早的兩位遺民伯夷、叔齊採薇而食和陶淵明之不事劉宋的的抗節行為,幾乎都懷有深深的追慕之情,以藉此勉勵自己堅守節操。如方賞的詩:
繞畦晴綠弄潺湲,倚仗東風卻黯然。
往夢更誰憐秀麥,閑愁空自托啼鵑。
犁鋤相踵地力盡,花柳無私春色偏。
白髮老農猶健在,一蓑牛背聽鳴泉。
詩歌描寫了春日田園的自然風光,頷聯首句是統攝全詩的軸心,用箕子感“麥秀”而傷殷亡的典故,表達了作者為田園春景所感,而懷念故朝的情思。由此間接透露了詩人“黯然”之由,“愁心”所在。春日欣欣向榮的原野風光,敷染了作者主觀的悲思,使全詩始終籠罩在沉鬱凝滯的氛圍中。可見在這貌似飄逸的詩句中,實是作者通過對忠誠義士的追慕來顯現強烈的亡國之痛和世事滄桑之感。再如“九山人”的詩:
軒裳一夢斷塵寰,桑柘陰陰靜掩關。
種秫已非彭澤縣,採薇何必首陽山?
因憐社鼓剛催老,轉覺儒冠不負閑。
君看浣花堂上燕,芹泥雖好亦知還。
對異族統治者的控訴
由於蒙元統治者從馬上得天下,本屬一個游牧兼狩獵的落後民族,“自春徂冬,旦旦逐獵”和長期逐水草而居的流動生活,使他們養成了慣於賓士殺掠的特有習性,文化素質十分低下。消滅南宋政權之後,官員需要大量激增,權臣更是趁機賣官鬻爵,只要賄以財貨,皆可署江南之官。故“南方郡縣官屬,指缺願去者,半為販繒屠狗之流、貪污狼藉之輩”。他們唯以促辦錢穀為才,搜刮割剝為務,“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而根本不顧江南人民的死活。雖然本次詩歌的主題是歌頌田園風光,但蒙元官吏的殘酷壓榨和無情剝削,在詩人們的筆下還是不由自主的要反映出來如感興吟的作品:
兒結蓑衣婦浣紗,暖風疏雨趲桑麻。
椎鼓踏歌朝祭社,賣薪挑柴晚回家。
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榷茶。
這首詩的前三聯描繪了一幅春日田園農家圖,忙忙碌碌的身影中,沒有一人是空閑的;365天中,每日都得為生計而勞作。自認為文化人的他們,社會地位從原來“四民之首”的座上賓一下子成了社會最底層的勞力者,生活上的艱難、鬱結在心中的悲憤可想而知。尾聯直言主旨,從側面揭露了政府官吏來鄉村收茶、鹽等租稅時的強盜行徑,以及鬧得全村雞犬不寧的實況。其他如戴東老“去年官賦今年罷,寂甚門前犬吠聲。”姜仲澤“鼎貴安知此中意,徒能學犬吠村莊”等句也均含蓄地揭示了士人們即使隱居在田園,照樣要承受蒙元統治者的沉重賦稅和剝削,日子過得並不安寧。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月泉吟社的詩人們在經歷了國破家亡之痛,遭到了異族政權的無情摧殘后,產生了躁動不安、悲哀無奈的共同心境。他們感到別無選擇,只得人人唱起隱逸之歌,於是隱逸便成了詩人們詩歌的主旋律。因為他們深知,儘管世代更迭,但寧靜和諧的自然風物是千古不變的,田園作為相對僻遠寧靜的“樂土”,才真正是他們自我躲避的角落和心靈的最佳歸宿,是一個重要的精神家園。也只有在這兒,他們才得以在精神上暫時獲得一份怡然自得的樂趣。如山南隱逸:
獨犬寥寥晝護門,是間也自有桃源。
梅藏竹掩無多路,人語雞聲又一村。
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
我來拾得春風句,分付沙鷗莫浪言。
詩歌開篇言旨,把偏遠寂寞的鄉村生活和傳說中的人間仙境挑花源相媲美,中間兩聯對仗工整,用了梅、竹、枯藤、野水等植物,配合著人和動物的聲音及屋角和田頭等地點,構成一幅繽紛且充滿生意的春日田園畫卷。也間接地呈現了平實的田家生活。誠如安定書隱所寫:“世數有遷革,田園無古今”,這當是身處宋元之際的士人們共有的認識。
對高尚情操的讚美
自先秦以來,中國的士人群體心態主要表現為一種經世致用的入世精神、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意識和匡時救俗的社會責任感。特別是到了南宋末年,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他們這種關注民族命運的積極入世精神更被空前地激發出來。而國家的覆滅、民族的屈辱以及士人地位淪喪所帶來的人格的扭曲、自尊的貶損,又使他們陷入了空前的羞辱、悲憤和人生價值嚴重失落的困惑之中。在這無可奈何的窘況下,詩人們只能帶著破碎的心靈踅入“獨善”之途,以表現出與統治者的距離和自己的孤介情操。如桑拓區詩云:
粟爵瓜官懶覬覦,生涯雲水與煙腴。
晚風一笛麥秧隴,春雨半鋤桑拓區。
可是樊遲宜請學,肯教陶亮嘆將蕪。
斜陽芳草關情處,更把新詩吊石湖。
詩歌首聯就表明自己對於元廷所施祿餌的不屑之情,無論是芝麻小官還是封侯拜將,自己仍將一如既往地,只願在雲水茫茫炊煙裊裊的田園間度過餘生;頷聯藉助“晚風”、“春雨”、“麥秧、“桑拓”等自然意象展現生機四射的田園風光;頸聯借用《論語》中孔子的學生樊遲請學及陶淵明歸去來賦典故,表示自己不會上當變節;尾聯言旨,借歌頌田園風光表明自己隱逸志向。
《月泉吟社詩》是以詩歌大聯唱的形式反映數千遺民進行的集體抗節活動,在中國古代詩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這本詩集最可貴的意義在於它以特殊的方式,即無視異族入侵的降臨而繼續吟詠田園風光,實際上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反抗———或說拒絕,來反映當時遺民詩人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這一點,數百年來一直起著激勵民族鬥志的積極作用。而且,詩人們還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上繼詩、騷、陶、杜,使南宋後期的衰頹詩風為之一變,為宋代詩壇寫下了光輝的最後一頁。正如張兵在總結宋末元初遺民詩歌創作時所言:“抒故國宗社之憂憤,歌黍離麥秀之悲音,慷慨沉鬱,憂深思遠,不僅表現了堅貞的民族氣節,而且有力地改變了宋季四靈江湖詩人氣局荒靡、纖碎淺弱的詩風,對有元一代詩歌創作影響甚巨。”總之,“月泉吟社”及其創作除了對元代詩壇頗具影響外,在後世遺民詩人中也被奉為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