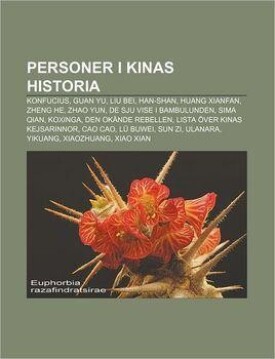黃氏三重證據法
黃氏三重證據法
在古史研究上,黃現璠是最早突破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建立“三重證據法”的學者之一。所謂“黃氏三重證據法”,是指黃現璠將歷史文獻、考古史料、口述歷史三者結合起來的治史法,這在黃現璠對民族史和壯學研究的大量論著中斑斑可考,尤以自著《廣西僮族簡史》和遺著《壯族通史》表現突出。

“黃氏三重證據法”創立者-黃老教授
三重證據法是建立在二重證據法基礎上運用三重或多重證據研究歷史的考據方法。在近代之前,傳統史家常常只是運用文獻記載作為唯一的研究歷史的證據材料。近代學者打破傳統,推陳出新了二重證據法。如王國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陳寅恪說:“一日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日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日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二重證據法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考古學和考據學的重大革新,現代許多學術大家,在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實踐中,都自覺運用二重證據法,當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國學者仍將二重證據法奉為古史研究的圭臬。但也有一部分學者,已突破二重證據法而創新地運用“三重證據法”作為研究歷史的證據法。一些學者談到的三重證據法的“三”不是基數詞,而是約數,指“多”的意思。事實上仔細推敲,目前歷史學界看到的似乎只有“三重證據法”成果,很難再找出第四重證據。如果不講學術的嚴肅性、嚴謹性而硬要穿梭附會強詞奪理,那又另當別論了。
所謂治史證據中的“文獻史料”,即王國維和陳寅恪所說的“紙上之材料”或“紙上之遺文”,過去學者大多理解為“文獻史料”(包括古典文獻和歷史文獻),事實上,“紙上之材料”或“紙上之遺文”還應包括人類學和民族學調查所得的古籍、古文書等“文字史料”。而王氏、陳氏所言“地下之新材料”或“地下之實物”,即指考古史料,它包括有字的考古史料(甲骨文、金文、木簡等)和沒字的考古史料(出土的無字實物),人類學和民族學調查所得的“實物史料”(古代遺物)同樣屬“考古史料”一類。如此一來,表面上看區別於“文獻史料”和“考古史料”的人類學和民族學調查所得的“調查史料”,實際上它包括的調查所得“紙上之遺文”、“遺傳實物”和“口述史料”中前兩項應該歸為“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的範疇,很難作為區別於“文獻史料”和“考古史料”之外的“一重證據史料”,唯有當中的“口述史料”與眾不同,獨立於“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之外,可視為“二重證據法”之外的另“一重證據”。換言之,在“二重證據”上加上“口述史料”,“三重證據法”於焉成立。一些學者將歷史學研究中藉助或引入人類學、民族學的史料而不加具體分析視其為“一重證據”史料,更有荒唐者,將引用“國外史料”(即在國外發現的有關中國歷史、文化、民族、風俗的“文獻史料”和“考古史料”)當作“二重證據”之外的“一重證據”,這是思慮極淺和牽強附會的誤識,真學者向不以為然的。
在從事民俗學或民族學的研究過程中,黃現璠逐步認識到學界盛行的二重證據法並不能在史料上充分說明民俗學或民族學研究中遇到的許多新問題,即歷史留下的文獻或近代流行的考古地下遺物挖掘史料依然有限,不足以解決一些新學術研究領域的新問題。於是,黃現璠開始了他的“行萬里路”的田野學術考察,期望於學術實踐中有所突破,最終收集到大量調查史料(包括“紙上之遺文”的“文獻史料”、民間遺留之“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從中他敏銳地意識到“口述史料”可以作為獨立於“文獻史料”和“考古史料”之外的“一重證據史料”,用以說明少數民族史中的一些難解問題,從而自覺地加以了運用,由此形成了“黃氏三重證據法”。由此可見,問題意識是“黃氏三重證據法”形成的前提條件,而廣泛收集“口述史料”,則是“黃氏三重證據法”形成的根本條件。
在古史研究上,黃現璠是最早突破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建立“三重證據法”的學者之一。所謂“黃氏三重證據法”,是指黃現璠將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結合起來的治史法,由黃現璠創始,故得名。
黃氏收集“口述史料”簡歷
作為一門學科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致力於“對過去事件的參與者和目擊者等當事人的採訪,目的在於重建歷史。它是一種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紀歷史的研究方法。”現代口述歷史的方法被廣泛地運用於各種學術領域,特別是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領域。中國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學者皆從各自的學科角度出發,對口述歷史有著不同的理解、表達和實踐。特別是我國有56個民族,它們當中有許多少數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歷史上難以留下文字材料,民族文化大多遺留在自己的民族記憶里,保留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中。為了保存這些民族的文化精髓,口述歷史或口述史料無疑是“還原”這些民族歷史的最佳方法。
黃現璠一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和史學、民族學研究,中年後尤重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工作和近現代史研究。他在組織領導的多次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工作中以及一些有關近現代史的研究課題中,曾對眾多人物進行過採訪,收集到大量口述歷史資料,這從他遺存家中的九冊《少數民族調查筆記資料》和數十冊《人物採訪筆記》中可見一斑。黃現璠生前訪談過的人物,既有中國現代史上國共兩黨上層人物龍雲、黃紹竑、陳銘樞、羅章龍、張雲逸、韋國清、謝扶民、謝鶴籌、黃松堅、黃舉平、覃應機、甘苦、吳西、黃一平、陸秀軒、黃榮、趙世同等,又有國內外著名學者梁啟超、章太炎、威廉·施密特(1868~1954,奧地利“維也納學派”領袖)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等人,還有眾多普通老百姓和鄉村農民,採訪人物涉及面之廣,可說在中國現代學術界屈指可數。
1943年8月,黃現璠帶領中山大學學生組成“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帶團深入到廣西義寧、龍勝、三江等縣考察;1945年4月,黃現璠帶領廣西大學學生,組成“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他率團赴貴州榕江縣大有鄉一帶考察壯族、侗族、苗族、水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生活,重點是調查當地苗民教育、文化、生活、習俗和婚姻狀況;1945年9月,黃現璠帶領學生張壽祺(後任中山大學教授)到融縣附近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作學術考察。以上三次考察分別調查了黔桂邊區少數民族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狀況,共歷時近一年之久。他與“蜷伏於荒山長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數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飽腹,夜無卧具,不分晝夜地採訪當事人和知情者。他於三次學術調查過程中前後採訪的當地邊民達30多人之眾,十分艱辛地收集到大量古文獻史料和“口述歷史”資料(即口述史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1年6月,黃現璠參加了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即第一分團,團長費孝通)工作,任副團長,與費孝通、陳岸等人一道率團深入到區內各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兼調查。黃現璠到東蘭縣韋拔群烈士的家鄉武篆區東里鄉慰問時,曾親自登門慰問和採訪了韋拔群的妹妹韋武月、韋武丁和弟媳黃美倫。由於在對這些革命人物的採訪過程中,黃現璠深為老革命者韋武月、韋武丁和黃美倫等人所談的她們與韋拔群一道當年鬧革命的事迹感動,加上同為壯族人,採訪上無語言障礙。為此,黃現璠萌芽出了撰寫韋拔群評傳的念頭。從此之後,黃現璠借著經常與韋拔群烈士生前的領導張雲逸大將以及生前部下韋國清、謝扶民、謝鶴籌、黃松堅、黃舉平、覃應機、黃一平、陸秀軒、黃榮、趙世同、牙美元、韋國英、廖熙英等人在一起開會的機會,多次採訪或專訪了這些革命前輩人物,收集到大量第一手“口述史料”,並運用這些人物採訪資料所得到的口述史料和其他人撰述的一些回憶文章,陸續寫出了《右江蘇維埃政權之建立》初稿一卷和《韋拔群評傳》初稿三卷。《韋拔群評傳》現已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於2008年9月出版,全書90餘萬字。正如韋拔群的好學生、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務委員會原主任黃榮(韋拔群生前的農講所學生)於《韋拔群評傳》“代序一”中所言:“為了收集韋拔群同志的革命事迹,黃現璠教授曾多次到我家做客訪談,我不斷鼓勵他早日完成。”可謂從一側面道出了黃現璠為撰著《韋拔群評傳》而廣泛進行人物採訪的實態。《韋拔群評傳》中即收錄了許多親身參加過右江革命運動的老革命前輩親歷、親見、親聞的“口述歷史”。
1956年10月,身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的黃現璠,負責調查組的全面學術調查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調查。他帶隊在深入區內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展開調查的過程中,採訪的人物更是繁多,收集到大量珍貴文獻和口述史料。
1978年7月,年近80歲高齡的黃現璠拄著拐杖,帶領助手赴龍州、憑祥、寧明、崇左等縣收集紅八軍革命史料;1979年11月,黃現璠又帶領助手赴廣西百色、田陽、田東、巴馬等縣調查“百色起義”和收集韋拔群烈士的史料。正如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的覃應機說:黃現璠教授晚年“以八十歲的老邁之軀,拄著拐杖,領著他的學生和助手,到本區的百色、靖西、寧明等地,還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進行綜合考察並搜集資料。”黃現璠生前的學生兼助手周作明教授回憶說:“恩師在80高齡的年紀,還經常拖著年邁的身驅外出做社會調查,在1978年7月11日至8月5日,竟有近一個月穿行在寧明、崇左、龍州、憑祥等縣市的群山峻岭和大街小巷之中。在考察中,每到一處,恩師都親訪民宅,探究遺址,總是那樣地樂此不疲。”文中所言“親訪民宅”便是登門採訪人物,收集口述史料。這從黃現璠當時的助手何英德研究員的回憶文章中同樣可資佐證:“一九七八年夏天,我與周作明同志一路陪他(指黃現璠——筆者按)到龍州調查紅八軍起義,還到憑祥、寧明、崇左等地……當時黃老已是八十高齡,仍頂著烈日奔波於江河、鄉村之間,逢人必問,無論是老幼,真是‘不恥下問’。”文中所言“逢人必問”、“不恥下問”,正是黃現璠為收集口述史料而進行人物採訪時的一貫作風和特點,同時亦為他中、後期學術生涯中能收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的法寶。
在“黃氏三重證據法”形成的前提條件和根本條件具備的基礎上必需躬身實踐,將收集到的大量“口述史料”去偽存真後用於著述和學說中,“黃氏三重證據法”始能成立。因此,實踐運用又是“黃氏三重證據法”成立的必要條件。“三要件”一應俱全,“黃氏三重證據法”於焉成立。“黃現璠史學”的實踐性為“黃氏三重證據法”的這一必要條件的成立無疑提供了基礎。黃現璠將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結合起來治史從而形成的“黃氏三重證據法”的實踐運用,在對民族史和壯學研究的大量論著中斑斑可考,尤以自著《廣西僮族簡史》和遺著《壯族通史》表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