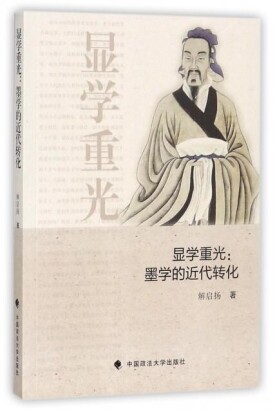顯學
文化流派
顯學,是指一時在社會上處於熱點的、顯赫一時的學科、學說,學派。韓非子著有《顯學》。《顯學》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這是指韓非子所處時代的情況。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顯學。“顯學”之名最早見於《韓非子》,指盛行於世且影響較大的學術派別。顯學更接近於現在的科學物理研究,被稱為實踐學派。儒家學派、黃老學派、墨家學說與楊朱學派組成了中國較早的顯學學說學術。
孔子—儒學,墨翟—墨學,儒學與墨學並稱“顯學”。
顯學強調存在就是現實,對於顯學研究的成就根源於對發展變化和諧治理制衡的理解。顯學根於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提供治理管理的意見與建議,而忽視了對自身是否完善的探索而使得自身容易發生主觀的錯誤,帶來新的錯誤。當然顯學的不足可以通過玄學來豐富。對於中華文化的深厚也只有揚長避短確定診斷髮揮正確的部分,適時改變完善服務於對現實發展需要的實踐。遵循宇宙發展創建的規律,無論曾經存在還是現存在,都應該得到發展;顯學無疑應該成為未來創建的重要內容。
《莊子·駢拇》云:“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棰辭(棰辭二字據王叔岷說補),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韓非子·六反》:“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由此可知,楊朱學派當積極參與了戰國時期關於堅白同異的論辯。可惜的是,楊朱學派在這方面的見解和貢獻已無法考知了。
古希臘哲學是極富純理論探索精神的。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哲學是“自由的學術”,“為其自身而存在的學術”,換言之,“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而中國古代哲學大多是“致用”的學術。先秦哲學中最富於“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理論色彩的學術問題,大概就是堅白同異之辯了。楊朱學派“游心”于堅白同異之辯,韓非斷其“不可以為官職之令”,甚至連避世的莊子學派也批評楊朱學派“敝跬譽無用之言”,則楊朱學派之富於純理論精神實在已無可懷疑了。
《莊子·天下篇》的“百家之學”,《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呂氏春秋·不二篇》的“天下十豪”,《韓非子·顯學篇》的儒墨,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中的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劉勰《文心雕龍》的諸子。
“顯學”之意始見於《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顯學”之名后見於《韓非子》,指盛行於世而影響較大的學術派別,然而韓非舉儒墨為顯學是為了要秦王廢除批判兩家指出兩家之害,而同樣影響巨大的道法則沒有列舉,私心頗大。
玄學又稱新道家,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它是中國哲學脈絡中很重要的一塊,產生於東漢三國、昌盛於魏晉。是中國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與世俗所謂玄學、玄虛實有不同。“玄”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揚雄也講玄,他在《太玄?玄摛》說:“玄者,幽摛萬類,不見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說:“玄,謂之深者也。”玄學即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魏晉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之為“三玄”,而《老子》、《莊子》則被視為“玄宗”。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含義也因歷史沿革而不斷演進變化,要了解真實,可以查閱相關資料,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中有相關記載,胡化凱老師的《科學思想史》課程也有相關的講述。
“玄學”重要學術特徵是:以天地人為研究對象,以天文地理、數學、物理、農業水利、動植物生長規律、音樂、律歷、養生等知識為研究手段,去最終探索天地人的和平發展運作及其內在生態系統規律的一門系統性學問知識。中國歷史上的“玄學”具有“基礎性”學問的特點,它的學術研究資源來自於人類社會的所有領域,但是,它一般又不涉及具體的政治、經濟、倫理和科學技術等問題,而是著力去研究這些知識背後和本質性的同一運作規律,所以,“玄學”的學術成果往往不能夠直接運用於世,卻又是中國古代社會各種知識的基礎。
按照哲社部吳靜波老師的觀點,“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即可將“玄學”,等同於“元學”,“元”就是“meta”,這樣就便於理解了。事實上,很多研究者將玄學等同於哲學看待,而一些江湖術士認為玄學就是算命之學。
韓非子·顯學第五十 原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斗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途,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副痤則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楊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名思想家,字子居,衛國人,生平已不可考。在當時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現。他的行蹤多在魯、宋、梁一帶。據《莊子》記載,他曾經見過老子。其活動的年代,比墨子稍後,而又早於孟子。有雲他是老子弟子,或為道家別支。其學說在當時相當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散見於《孟子》、《列子》及《淮南子》中。
《孟子.滕文公》篇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可知春秋之世,楊朱之學與墨學齊驅,並屬顯學。楊子之學,曾風靡宇內,然卻如曇花一現,後繼無人。實則楊朱歿后,老莊之徒興,其一方既能踵楊子之餘緒,又能發其所未發,自是楊朱之名,遂為莊子所掩。
楊朱曾經和老子會面,所以他曾受老子思想的影響。後來有感於動亂的環境,困惱于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於是揚棄老子學說中的部份內容,朝著“養生”、“存性”的方向不斷深化,發展成以“為我”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楊朱的思想在戰國初年一度風行,與儒、墨兩家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勢。
楊朱的思想概略,可從以下四方面見之:
首先,從其中心要旨而論,楊朱學說實在是以“我”作為自然的中心。他認為人的生命,往往由於外界的蒙蔽、組織所拘束,因而無法明察生命的真象,使個人失去主體性。於是楊朱主張探求內在自我安身立命的境界,以擺脫社會的束縛,偏向於個人人性的追求。他認為只有重視人類本有的自然性,人才會快樂,才能“全生(性)保真”。
其次,在政治方面,楊朱既然反對社會的束縛,所以在政治上也反對強權獨佔的霸道,主張“天下為公”,要“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另外,他認為一切外在的道德刑法,皆不可妨害一個人的自由。政府只是象徵式的,不可對個人過份約束。由此可見楊朱的政治觀是放任自由的。
第三,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楊朱極力主張個人的“為我”主義。他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說社會是由各個“我”所組成,如果人我不相損、不相侵、不相給,那麼天下便無竊位奪權之人,便無化公為私之輩,這樣社會便能太平。
第四,在對生命的態度上,楊朱既重說“全性保真”,因而重視“貴生”、“樂生”。他認為人生短促,故在生時必須享盡人生之天性,所以要適欲。發揚了老子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與養生等思想。重生、貴生的思想,在當時及近代被認為是否定儒家禮教的束縛,又摒絕了墨家的禁慾;承認命從而否定墨家的非命。《楊朱篇》非儒、墨、《力命篇》非墨。